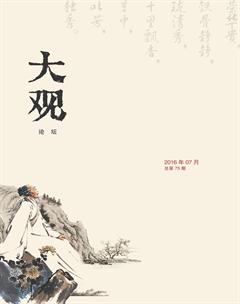紀錄片創作中的紀實性、真實性和觀賞性(下)
李燕
摘要:以美學角度為出發點,用藝術的表現手法來說明問題和展現客觀真實,以此讓紀錄片更具備觀賞性。“觀賞性”能夠讓“真實性”更加具有說服力和魅力,是紀錄片能夠打動人心與受眾共鳴的關鍵因素。但是紀錄片終究是真實的影像藝術,這就要求“觀賞性”與“真實性”能夠在一定的程度上達成和諧統一。
關鍵詞:紀錄片;紀實性;真實性;觀賞性
一、紀錄片中真實性與觀賞性的關系
(一)現實存在與主觀思考的關系
紀錄片無論在題材選擇、前期拍攝、后期制作等任何一個環節都離不開創作者的主觀意識。創作者的這種主觀行為是一種藝術再創造的過程,無論任何的藝術形式都不能避免的,并使紀錄片有了主觀的方向,是影片的創作者對客觀事物的感知和表達。而主題和情感都是建立在客觀真實的基礎上,影像本身的真實是受眾建立真實感的基礎和關鍵。紀錄片的真實感是來自影像本身內容的真實,在此條件下創作者可以將一切能動性的思考盡可能的用在創作的過程中,這樣才可以提升紀錄片的藝術價值和觀賞性。
(二)客觀紀錄與主觀表現的關系
紀錄片作為一種傳播形式,雖然在電影發展史中,并沒有占據電影工業的主導地位,但是紀錄片電影以其自身獨特的方式展現出其它類形電影不具備的特點和性質。不斷的追求真相是紀錄片的本質屬性和目的,所以在紀錄片創作中真實的重要性是不可撼動的,同樣真實性也占據紀錄片的“首把交椅”。
紀錄片的本質就是建立在客觀真實素材上的主觀表意,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影片創作者必須要用心去觀察現實世界和思考生活。心如花,默默開放,在紀錄片的創作中必須用心才能看見,靈魂是任何主體存在的前提基礎[1]。紀錄片不是新聞報道,而是經過影片創作者的獨立思考、選擇與后期制作才誕生的影視藝術類型,正是如此,創作者的主觀思考才能成為影片的靈魂。事物存在,這是肯定的,如何去拍攝,從哪種角度去記錄,這就是主觀表現內容中的思考。紀錄片的表現來自對客觀真實事物的記錄,這一過程一定要以紀實主義的原則為宗旨,主觀表現是客觀記錄的能動性體現,應此主觀表現必須是有根據的,也是一定要具備客觀性的表現,客觀性保證了紀錄片的真實度。所以,再現客觀真實并不是紀錄片的唯一目的,然而,錄實僅僅只是一種表現形式而已,通過紀錄片的視聽表現方式來傳達創作者的思想感情并以此去打動觀眾的情感,這才是紀錄片最終的目的。利用影視語言與觀眾達成共鳴,這就是優秀紀錄片的成功之處。
真、善、美是要經過觀眾的閱讀才能被理解的。紀錄片僅僅只是創作者表達內心思考的外在體現,真正實現美好事物的理想才是影片創作者的終極目標,同樣紀錄片的創作亦是如此,所以,客觀再現與主觀表現的融合的度正是影片真實性的體現。
二、紀錄片創作觀念
(一)用真實奠定基礎
在紀錄片創作中,導演不應該去主觀的安排事件的發展,也就是說不能夠用“演出” 等行為進行創作,使紀錄片失去了客觀真實的面貌。“演出”是指對已經發生的事件由演員 重新扮演或是演繹,直截了當地說就是運 用影視表現手法重現歷史事件,以此方式 對表述內容的強調。而這恰恰是與紀錄片 的宗旨不相統一。在影視語言中的再現有兩種方式,一 是影片中的人物按照曾經的經歷再次還 原,就像影片《北方的納努克》中導演弗 拉哈迪就讓人物去還原納努克上一代長輩們的生活方式。
另外還有一種再現的方式,就是 演員來扮演,創作者們還會通過美工、化 妝師、布景等一系列的方式來達到需要的 藝術效果,導演還會告訴每位演員應該怎樣去表演、去演講等等。筆者認為,這完全是虛假的方式,僅僅是套著“情景再現”的外衣 進行著“表演”。這是從本質拆卸了影片的真實性,紀錄片的前提是客觀真實而絕非是 表演,更不是按照導演的意圖進行的一系列的演出行為。所以說紀錄片更是要以真實作 為前提基礎,也就是真實的影像基礎也是紀錄片的根基,所有創作者的表意一定建立在影像 素材真實的基礎上。
(二)用藝術展現真實
安德烈·巴贊的攝影影像本體論、電影美學理論、是紀實主義理論的源頭。在這種美學觀念的指引下,天然不經打磨的物品是其追求的目標,這種觀念強調的是一種以自然的方式 完成的作品,所以大多獨立影片都取材自真實的生活而非由導演安排和再現生活。在自然的 形態下,有很多有待我們去發現的美。忠誠的客觀紀實是紀實主義一貫所堅持的手段,毫不 粉飾的再現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紀實影片的作品可以通過攝影機的客觀性最大程度上的展現 真實,因為攝影機的本質是“照相錄實”和“真實再現性”。在客觀真實的前提下,獨立紀 錄片創作者具有和故事電影導演同樣的對藝術手法的運用權。真理才是紀錄片導演的最終追求和目的紀實美學一直是紀錄片創作必須堅持的美學原則。紀實美學是紀錄片發展理論源泉,在 其作用下,誕生了法國的真實電影、美國的直接電影、中國的新紀錄片運動等紀錄片創作的 派別。中國以往的紀錄片受蘇聯模式的影像,長期注重其宣教的功能,忽略了紀錄片真正 的特性,即真實性。20世紀80年代后,國外優秀的紀錄片進入中國,在八、九十年代, 中國紀錄片創作出現了空前的繁榮,如《藏北人家》、《望長城》、《流浪北京》、《沙 與海》等。《沙與海》導演康健寧在拍攝上慣用畫意的構圖方式,使影片以 一種寫意的方式展現平凡的生活。這些在當時優秀的作品讓中國紀錄片看到了一股更加真實的力量,很多紀錄片導演揭竿而起。實際上這股力量就是紀錄片惟一生存的命脈,在這里必須說明的是優秀的紀錄片并非是純粹的記錄客觀,藝術的表現己是紀錄片發展的趨勢。在紀錄片創作的觀念上要明確這點,這樣影片才能夠更加富有生命。也可以說在創作時更應該考慮到意境氛圍的營造,有了“意”的加入會顯得更有韻味。
(三)用真情代替宣教
很多紀錄片創作者在一定意義上都是在教條著某種主流的聲音,主流聲音之后才是自身 的思考。紀錄片利用豐富的表現方式可以講述過去的歷史、正在發生的現在和人們都在預知的未來,紀錄片本身具有“紀實”和“創作”的性質,同時也授予了紀錄片更大的作用與使命。這必定是一種有利于文明社會媒體傳播方式,在任何地方,紀錄片都可以視為社會價值觀的綜合體現。
中國早期的紀錄片與新聞片沒有什么明顯的差別,表面上來看差別就是紀錄片的時間長于新聞報道,內容也比新聞更加豐富。所以,一直以來紀錄片成為了反映社會各種事態的工具。在中國從紀錄片這種影視藝術類型衍生了新的一種影片類型——“電視專題片”,這種畫面加解說詞是標準的格里爾遜模式,帶有強烈的教說意圖。這種類型紀錄片,不管是理念還是主題的選擇上,各各方面都突出了教化性,就像似一場演講,這種教說式的創作思想—直影響著我國紀錄片的創作。新紀實主義的紀錄片所拍攝的內容是展現真實客觀的人、物、事與其所在的時間和空間, 這絕不是說紀錄片就是對生活得復原,而是需要在創作中秉承紀實 美學的觀念。《音樂人生》這部紀錄片主要講述了一位音樂癡狂者,影片記錄了主人翁從兒童到少年的生活、思想和對待音樂的態度,在90分鐘的影片濃縮了這 位音樂少年7年的生活。影片沒有解說詞,少有采訪,記錄式的影像講述了這位少年的真實生活,對音樂的執 著與家人、朋友之間的關系,影片導演借助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表達了真實性與真實性中所 蘊藏的感性,為受眾所接受·作為一種影視藝術的門類,不能只靠“以理服人”,更應該“以 情動人”,紀錄片必須具備情感的表達,這樣才能夠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所以,用真情 來創作,就是要融入真實的感受、真實的思想,以此來打動觀眾的內心,而不是教化式向觀 眾表達創作者思想。
當下的紀錄片中存在兩個極端,第一個極端的體現是過于強調客觀而忽視了藝術創造,使紀錄片缺乏觀賞性;第二個極端是全部用虛構的影像畫面來詮釋真實,這使得影片失去了其真實的屬性,導致影片功能性的消失。所以,紀錄片必須強調以真實作為影片的生命。紀實主義的美學原則是紀錄片創作需要堅持的,而真實的前提是影像本體內容的真實性,在此基礎上任何藝術表現手法都應該為紀錄片創作所服務,以此提升其藝術價值和觀賞性。
總之,影片素材本體內容的真實是紀錄片真實的核心部分,也是紀錄片導演在創作中必需始終堅持的美學原則。不但是對的客觀真實保證,又是強調真實基礎上的主觀表意,從而在深層意義上保證了客觀真實與藝術創作的和諧統一。
三、結語
本文分析了紀錄片中的表現技法與“真實性” “觀賞性”之間的關系,以及兩者之間的平衡點。得出了紀錄片創作過程是客觀記錄與藝術再現的結合,應該具備“真實性”與“觀賞性”相統一的特點。具體結論如下:
(一)紀錄片中視聽語言的呈現
紀錄片視聽的表現要求真實自然,主要是為了體現真實的場景與影片氛圍,是聲音 與畫面相互說明對方,互為補充,是建立在主觀能動性下的聲畫統一,讓真實看上去更加真 實,也是“真實性”與“觀賞性”和諧統一的體現。
(二)紀錄片中“真實性”與“觀賞性”的關系
紀錄片中影像本體的“真實性”奠定了影片的根本屬性,受眾觀影的心里底線是真 實,所以在創作中應該以聲音、畫面、時間、空間等客觀真實的前提為基礎,是在其基礎上 的藝術再現和主觀表意。“觀賞性”需要在紀實美學的規范下,與構成真實客觀本體內容 充分結合,不僅是為了營造影片的藝術氣質,更重要的是完成真實性的藝術回歸,從而拉近 影片與觀眾的關系,使真實更加真實,用藝術的表現手法讓受眾更加信服熒幕上的影像畫面。
(三)紀錄片的創作觀念
創作觀念上仍然是以真實為基礎、用藝術展現真實、用真情代替宣教,通過藝術的手法 將真實的拍攝融入情感進行創作,能夠打動觀眾,與之產生共鳴。在這個層次面上塑造的本 質真實才更加生動,更能夠揭示現實中的真實,體現了紀錄片存在的意義。
綜上所述,紀錄片僅僅表現客觀真實的生活還是不夠的,優秀的紀錄片應該在客觀真實的前提下進行藝術的升華,通過藝術表現手法為觀眾找到最佳觀看角度。同時具備質疑的批判精神是紀錄片創作者應擁有的基本素質,去觀察,去發現、去討論,不斷的去琢磨這個現實存在的世界,揭示出現實的普遍意義和永恒價值。
【注釋】
[1]呂新雨.“底層”的政治、倫理與美學[J].電影藝術,2012(05):8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