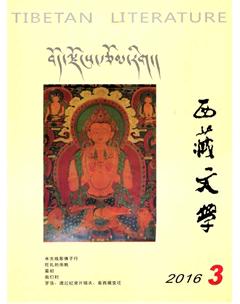小說二題
蘇子
她們的故事
磨房里偌大的石磙碾壓著石槽中炒熟的青稞,石磨發出低沉的轟隆聲,磨盤上方吊著的羊皮囊下端小口里,有節奏地漏出青稞,緩緩地喂進石磨中間的小孔,新鮮糌粑的香味溢滿小小的磨房。
外面傳來一個青年高亢的聲音:阿若曲珍,糌粑磨完了嗎?姑娘突然低下頭,紅著臉回應:快完了。青年走進磨房動作麻利地幫忙掃石槽中的糌粑面,不時深情地注視著姑娘。姑娘把頭上的圍巾往臉上拉了拉,整個臉幾乎遮住了,只露出兩只水汪汪的眼睛,躲閃著青年的目光。
糌粑磨完了。青年把藏袍的兩只袖筒往腰上打了個結,舉起裝滿糌粑的皮口袋往肩上輕輕一扛,低著頭出了磨房。姑娘隨后跟了出去。兩人一前一后沿著小路走去,上了一道山梁便到了女孩家。青年把糌粑往地上一放,一邊擦著汗一邊隨手接過女孩端過來的酥油茶,一口氣喝完。
那以后,青年時不時來到姑娘家,每次來懷里都揣一些核桃、蘋果、奶餅、酥油等討好姑娘。然后,拼命地幫姑娘做家務。姑娘身前身后打著幫手,不時被青年的幽默風趣逗得咯咯笑。
又一個春暖花開的時節,姑娘和青年成了一家人,并且有了第一個孩子,一個和媽媽一樣水靈漂亮的女孩。他們請活佛賜了個名,叫德吉措姆。于是,青年更辛苦地外出勞作、遠牧,姑娘在家帶孩子、操持家務。后來,又有了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年齡間隔都不大。女人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嬌美羞澀的姑娘,面容憔悴布滿褶子,也不再梳妝打扮,比實際年齡看上去蒼老許多。青年也不再腰板筆直,精力充沛。勞作回來的他一邊嘴里哼著“啊熱熱。”一邊疲憊地躺下,聽著滿屋子孩子們的哭鬧聲,無奈地閉上眼睛。
男人依然深愛著女人,女人也依然心痛男人。可生活的壓力使他們沒有了從前的浪漫和激情,只有默默地堅守著簡單的日子。盼望孩子們早些長大,多幾個勞力。
傍晚,一家七口圍坐在火塘邊,滿屋是煙霧,嗆得人直流眼淚。茶壺里熬著濃濃的茶,女人在一個石板上倒了些蕎面糊糊,不一會兒煎成了一張餅,剛一取下來就被孩子們搶著瓜分了,然后又眼巴巴地盯著石板,等待下一張餅。男人抱過最小的孩子,吼著幾個大的:別急,有的是吃的。女人沒有任何抱怨繼續烙著餅。等孩子們和丈夫都吃飽了,女人最后拿起一張餅,掰一塊蘸著碗里的酸奶,就著清茶吃了。最后,把裝酸奶的碗轉著舔得干干凈凈。
地里的麥子冒出了寸頭,山坡上一片淡淡的綠,田埂上的柳樹也發出了嫩芽。春天來了,他們要去給地里放水。幾個孩子大的背小的,一家人朝自己地里走去。老大、老二已經可以幫著干些活了。幾個小的就在地邊嬉戲玩耍。男人的背駝了不少,但依然強壯有力,邊勞動邊唱著山歌調子,幾個孩子也跟著哼哼。女人時不時招呼著老三看好弟妹。
這里一年就一季,地里的莊稼是他們全家一年的希望。歇息的時候男人說,再養幾只羊吧,兩個大的孩子該上學了,要交學費。女人應著:哦呀。可大姑娘說,讓弟弟上學吧,我在家幫阿爸阿媽干活,帶弟妹。男人說:不行,都去。不學文化不成。好歹認幾個字吧。
幾年過去了,孩子們都上了學。可老大小學沒上完就輟學了,倒成了家里的好幫手。雖說是姑娘,可干起活來像阿爸一樣利索,人也出落得越發漂亮。豐潤的瓜子臉,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烏黑的頭發,模樣活脫脫像年輕時的曲珍。村里的年輕人見了她總是找機會套近乎,可姑娘像阿媽一樣靦腆害羞,總是躲得遠遠的。
突然有一天,家里來了提親的。阿媽把女兒支了出去,阿爸阿媽和提親的人在屋里嘰嘰咕咕說了很久。又過了一段時間,幾個人來把女兒帶走了。那天姑娘哭得很厲害。曲珍躲在屋里不忍出來送行。可村里人都說姑娘命真好,有福氣嫁給在拉薩做生意的兩兄弟了。
幾年過去了,姑娘終于回來了,她手里牽著一個,背上背了一個,頭上盤著五彩絲線纏繞的辮子,身材更豐滿了。聽說嫁過去后,兩兄弟中的哥哥不愿同娶一個女人。于是,她便和弟弟結了婚。丈夫在外忙著做生意,她這次是專門回娘家探望父母。
老兩口又是泣又是笑,把女兒和孫兒們迎進了家門。曲珍已是滿頭白發,腰也彎了。不同的是衣服比過去穿得干凈講究,不再是蓬頭垢面,補丁蓋補丁。家里蓋了新房,養了好幾十頭牛和羊,老二和老三先后考上了外地的學校,最小的也在上初中了。日子比從前好了許多。
秋天來了。山寨滿目是深紅、金黃、墨綠交織,秋色斑斕,灌木樹叢在微風中搖曳。牛羊正是膘肥體壯季節。女兒沒住多少日子要回去了。曲珍兩口用牛毛編制的布袋為女兒裝了滿滿的核桃、蘋果干、奶渣、風干牛肉等。
曲珍有些渾濁的目光溫情地注視著女兒,強忍著淚水。女兒拉著阿媽一雙老繭粗糙的手,眼里滿是淚花。曲珍說:多回來看看,時間長了可能就見不著了。女兒哽咽著回答:哦呀。你和阿爸也要保重!
山梁上,阿爸阿媽摟著腰揮手,目送女兒遠去。女兒和前來接應的婆家親戚一道帶著兩個孩子,一步一回頭,難舍難分。
風中的阿媽曲珍哭了……
阿尼覺姆
烈日下,藏域一處偏僻的山鄉,通往山坳里的崎嶇小路上,旺堆扛著攝影機器,喘著粗氣獨自前行。他今天是專程去尋訪一個人,一個離開自己的故鄉幾十年,生死不明的孃孃。
阿尼覺姆是藏地康區對年長尼姑的俗稱。
旺堆的孃孃就是一位覺姆,其實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面。只是從他阿媽那里聽說過她的一些事。因工作的緣故,旺堆來到這里采訪時無意中得到了一些線索。聽當地人說,山坳里有一個來自遙遠康區的覺姆在那里修行了幾十年,也不知是否還在。旺堆心里一愣,早先在家時聽阿媽說過,她有個妹妹很小就隨朝佛的人去了西藏,從此沒有音訊。出于血緣親情和好奇心,旺堆決定前去打探一下。即使不是自己的孃孃,也算拜訪下這位修行的老者。
這天,旺堆起了個早,按照鄉人告知的方向朝著大山深處走去,山上沒有一棵樹,四周光禿禿的,腳下是紅色的巖石。高原熾熱的紫外線火辣辣的,把整個山脊烘烤得像一座火焰山,熱浪從地面反射上來,灼得旺堆滿臉通紅,一頭大汗。這一帶人煙稀少,荒蕪寂靜。偶爾有山鷹在頭頂懶懶地盤旋,幾聲單調的叫喚在空曠的山坳中回蕩,不由讓人有些寒噤。
旺堆不知道自己是否該堅持走下去。他有些猶豫,后悔沒有找一位當地向導。可心中的那份期待又讓他放不下腳步。他整理了一下掛在身上的包和相機,喝了口水壺里的水,擦了擦汗又繼續前行。幾個小時過去了,眼前依然是溝壑巖壁,不見路人。旺堆有些支持不住了,找了塊石頭坐下休息,眼見日已過午,他心里不由得有些焦急。山太大,溝太多,走岔一條溝就可能南轅北轍,徒勞無功。
旺堆定了定神,看了看太陽的方向,認準了一條道,又走了下去。就在旺堆已經筋疲力盡、有些失望的時候,前方山崖上有一個山洞,遠遠地能看見一縷淡淡的輕煙飄向空中。旺堆頓時興奮起來,認定那一定是他要尋找的目標。他加快步伐小跑起來,就在離山洞不遠的低洼處,有一個不大的泉眼,咕嚕咕嚕地往外冒著泉水,周圍長著一些綠色灌木植物,這讓旺堆激動不已,迫不及待地朝山洞奔去。他堅信有水就有生命,老人一定還活著。
旺堆來到洞前,往里探了探身子,按捺住激動的心情,輕輕地問道:“有人嗎?”里面沒回應。旺堆又大了點聲喊道:“有人嗎?”還是沒人回應。里面像是有人居住,有一些簡單的家什,地上三個石頭壘起的鍋灶下還燃著余火,一口被煙熏得黑乎乎的平底鍋里熬著茶。人應該不會走遠。旺堆出了洞口四處張望,又喊著:“有人嗎?”突然,背后傳來一個老者的聲音:“誰呀?”旺堆回過頭,只見一位覺姆模樣的老者從一面山坡上下來,腳步有些蹣跚,個子瘦高,身體看上去還硬朗,被高原陽光曬得發黑的臉上布瞞褶子,身上的袈裟已很破舊,脖子上掛了一串念珠,右手搖著一個又小又舊的轉經筒。沒等旺堆回話,老者就直接進了洞,邊走邊用手招呼旺堆進來喝茶。可能是長期與世隔絕隱居的緣故,老人口齒不大利索。
旺堆跟了進去,在火塘邊坐了下來。旺堆打量眼前的老人,盡可能想從這位老者身上找到一點想象中的痕跡,她的口音有些康巴語,但相貌和自己的母親不太像。最令旺堆感到不安的是,眼前的老人好像還有些神癲癲。老人根本不顧這位造訪的陌生人,自顧自地念著聽不大清的嘛尼,盤腿往地上一坐,就近取了一個木碗,倒上濃濃的清茶一口喝完。這才問旺堆:“你,拉薩來的?”旺堆:“是的。”老者:“我想去拉薩。”旺堆順勢問道:“嬤啦(對女性長者的尊呼),你的家鄉在哪里?”“家鄉?江那邊。”“哪個江?”“不知道。”說著,老人又站了起來,從角落里取出一個牛皮口袋,放在火塘邊,招呼旺堆吃糌粑。旺堆這才想起還沒吃午飯,就從包里取出一個鍋盔,掰了一半給老人,老人接過來眼里一下放出光來,高興地說:“好吃,阿姐做過。”旺堆追問:“姐姐叫什么名字?”“拉姆。”老人脫口而出。旺堆的心快要蹦出來了,他阿媽就叫拉姆!他蹭地從地上跳起來,又緊緊追問:“你還記得你阿爸阿媽的名嗎?還有你小時候住的地方是什么樣的?”老人看了看旺堆,呆木地搖了搖頭。旺堆提起來的心又沉了下去。
旺堆和老者就這樣無厘頭地交流著,旺堆盡可能啟發她的記憶,告訴她家鄉的一些特征,還有她當年離開家鄉時家人找她的情景。老人面無表情地聽著,嘴里不停地念誦著嘛尼,好像這一切與她無關。
眼看太陽已偏西,旺堆只好暫別老者,起身告辭。臨別時,老人突然說:“我要去拉薩。”旺堆試探著問:“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嗎?”老人馬上雙手合十說:“哦呀!哦呀!”就這樣,旺堆把一個并不認識,也不確定身份的老覺姆帶出了山洞,又把她帶到了拉薩。旺堆當時的想法就是了卻老人的一個心愿。
來到旺堆家里,當老人看到旺堆阿媽的照片時,老人瞪大眼睛指著照片說:“阿姐拉姆!”一切就這么巧合地確認了。從此,阿尼覺姆成為旺堆家的正式成員住了下來。旺堆把這個消息在第一時間用電報告訴了千里之外的阿媽。阿媽也是難掩激動的心情,希望不久的一天,她們姐妹倆能見上一面。
由于老人有些神癲,路途遙遠無法讓她一個人回去,旺堆因工作原因也一時難以脫身,就這樣幾年過去了。阿尼覺姆除了去布達拉宮和八廓街轉經,就是不停地給旺堆找麻煩。老人脾氣古怪,但心里有數。除了旺堆誰的話都聽不進,還常常發火。有一天,老人突然告訴旺堆,她想回老家。而且,越來越吵嚷著要回去。這讓旺堆很為難。阿媽去了很遠的姐姐那里,離開了老家。老屋只有一個年老的叔叔,也是孤寡老人。她回去了誰照顧誰?可人是他找回來的,他必須負責到底。為了再次了卻老人的心愿,他決定親自把孃孃送回老家。旺堆專門請了假一路輾轉,當車子行駛至與家鄉交界的金沙江大橋時,阿尼突然情緒激動起來,拍打著車窗叫喊著:“回家了!回家了!”
旺堆因工作在身不能久留,匆匆安頓好孃孃,又給老叔做了交代后告辭了。
回到家鄉的阿尼覺姆思維似乎清醒了些,但依舊時不時地在家里大吵大鬧,讓人不得安寧。
又過了些年,阿尼明顯老了,不再大吵大鬧。她生病了,病中的她喊著阿姐,她想見她的姐姐。老叔發去電文希望拉姆回去一趟。可那時交通極不方便,一時難以成行。碰巧的是,拉姆這時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打針吃藥終無濟于事,竟不省人事,瞳孔放大,醫生說為她準備后事吧。家人一時陷入悲痛。就在這時,傳來郵遞員急促的聲音:電報、電報!拆開電文只有幾個字:阿尼病故。家人心里一沉,難道是命中注定,冥冥中姐妹倆相約一同離開人世。
突然,這時病榻上的拉姆微微睜開了眼,還說她很渴,想喝水。守護在床前的家人悲喜交加,難道是回光返照?可拉姆看上去真的沒事了,之后竟然慢慢好了起來。當得知她的妹妹就在她病重不省人事的時候已經去世,拉姆恍然明白了什么,自言自語道,原來是她替我去了。她告訴家人,她做了一個夢,感覺匍匐在一個山洞里,越往里越窄小,她快爬不動時,忽然洞的前方有一燭光閃耀,一位白衣尊者朝她往外揮著手說:“你還不該來,回去吧。”她想轉身可洞太窄,只好退著往后爬行,慢慢出了山洞,眼前一亮看見了圍在床邊的家人。家人皆不可思議。
而阿尼覺姆總算是葉落歸根,魂歸故里,了卻了心愿。
責任編輯:次仁羅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