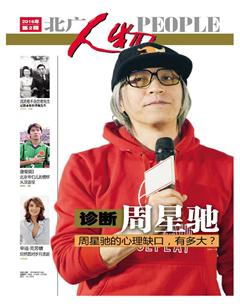怒吼過奧巴馬的醫生


她出現在戰火紛飛的各種難民營中,為了天災人禍中的人們,她咆哮過聯合國,怒吼過奧巴馬。廖滿嫦醫生的另一個身份是無國界醫生國際組織主席。2014年,廖滿嫦帶領著這個曾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組織奔走在蔓延著疾病恐慌的非洲大陸,并在聯合國呼吁各國迅速采取行動來遏制埃博拉疫情的發展,被外界稱為“埃博拉斗士”。
作為聲名赫赫的兒科急診醫生,她的身影并沒有太多出現在醫院里,人們總能在戰火紛飛的各種難民營中見到她。因為,她的另一個身份是“無國界醫生”國際組織主席。
她帶領著這個曾獲“諾貝爾和平獎”的組織,出現在任何需要醫療救助的國家,帶給苦難中的人們慰藉。為了天災人禍中的人們,她咆哮過聯合國,怒吼過奧巴馬。她說:“一位優秀的醫者,不僅要有高超精湛的醫術,更要有人文情懷。”她就是廖滿嫦,由美國《外交政策》雜志評出的2015年“全球百大思想者”之一。
人生還有夢想和遠方
廖滿嫦是移民二代,父母早年從廣東臺山移民加拿大魁北克,以經營餐館為生。雖然家境一般,但父母會不時接濟需要幫助的人。廖滿嫦記憶最深的,是母親幫助一個無錢付賬的中年男子。
那天餐館即將打烊,風寒料峭中進來一位中年男子,衣冠還算齊整但已明顯破舊。男子坐下后,猶豫很久才點了一份陽春面,然后很慢很慢一筷子一筷子地吃,邊吃邊不時用余光掃視店內。7歲的廖滿嫦正在吧臺上做作業,突然母親輕喚了她一聲,讓她出門告訴外出正在返回途中的父親進店后訂一份外賣,然后離開。廖滿嫦帶著疑惑照辦了,直到那名男子摸索著全身準備結賬時,她才明白母親的意思。“剛才來的那位先生替您付賬了,他家今天有喜事,想讓您也沾沾喜氣。”男子歡喜地走了,母親的話卻印在了廖滿嫦心里,“任何時候,人都需要有尊嚴。”
廖滿嫦喜歡醫學,常會讀一些有關戰地醫生的書。15歲那年,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的《鼠疫》走進她的人生。小說的主人公是個醫生,他盡其所能挽救生命。同事問醫生:“你為什么非要去?什么促使你這么奮不顧身?”醫生平靜地說:“我從未對死亡習以為常。”
這個故事成了廖滿嫦的人生坐標,“像一個對自己的約定,讓我也不要對死亡麻木。雖然這些事可能離我很遠,不會傷及我,但我有機會的時候,會努力挽救那些不應過早消逝的生命,為他們奮斗。”
于是,大學時廖滿嫦選擇了全球頂尖的麥吉爾大學醫學院,隨后又到紐約大學醫學院擔任兒童急癥科研究員,并在麥吉爾大學獲得衛生領導人員國際碩士學位。畢業后,她進入蒙特利爾大學擔任教職。
次年,廖滿嫦加入無國界醫生組織,前往非洲西北國家毛里塔尼亞,為其鄰國馬里的難民提供醫療護理。“4萬人中只有我一名醫生,每天超負荷運轉,睡覺就是奢侈品。”
夢想照進現實,廖滿嫦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樂與滿足。多年后,醫學院的同學故交們,或名利雙收,或成果斐然,唯有廖滿嫦常年行走在戰火中,灰頭土臉,甚至性命堪憂。問她是否曾后悔當初的選擇,她淡淡地笑了,“有句話現在很火,‘人生不只是茍且,還有詩和遠方。我想說的是‘人生不只是茍且,還有夢想和遠方。”
世界的覺醒慢一步
成為無國界醫生后,廖滿嫦經歷過海嘯的印尼,遭受地震和霍亂的海地,戰火紛飛沖突不斷的肯尼亞、剛果、阿富汗、達爾富爾……無數極度危險的國家和地區都留下了她忙碌的身影。這期間的艱難苦楚,無法用言語盡述。
在剛果和蘇丹,由于要時刻提防叛軍攻擊,廖滿嫦睡覺都穿著鞋,稍有風吹草動,跳起身就能往屋外跑。在也門,炸彈聲此起彼伏,遭遇的危險已無法用“最”來描述,流彈像節日里的煙火般,已是家常便飯。在索馬里和烏干達,沒日沒夜地連軸轉,一轉就是八九個月……廖滿嫦用醫術與仁心,拯救了大量無辜生命。
一線經歷讓廖滿嫦有了更多思考。漸漸地,她從一個只關注醫療技術研究的醫生向管理者轉身。加入無國界醫生3年后,她成了該組織巴黎辦事處項目經理,不僅服務于難民、病人,更積極為參與組織的工作者提供良好服務。
2013年6月,她當選無國界醫生國際組織主席,成為這個人道主義救援組織的最高管理者。
2014年3月,西非地區多個國家爆發埃博拉病毒,廖滿嫦馬上組織成員赴西非實施醫療救助。“在最艱難的九個月里,我們的成員平均連續工作四周才休息一天。多數成員失去了家人、朋友,還要活在暴露于病毒中的恐懼里。”
讓廖滿嫦覺得“很難很難的”,是在救治過程中,她和團隊感覺到埃博拉疫情兇猛異常,與此前其他疫情大不一樣,便反復向聯合國請求采取實際行動,阻止疫情發展擴散。然而這種前瞻意識并沒有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直到半年后,埃博拉病毒對國際安全構成威脅,而非僅對西非貧窮國家造成威脅之時,世界才開始覺醒。“那是我覺得最無力最艱難的時候。”
這一路走來,廖滿嫦經歷了太多危險,也還有更多危險之地等著她。僅2016年第一季度,她就前往中東,探訪巴勒斯坦、黎巴嫩和約旦的敘利亞難民營。雖然無國界醫生對于如何在沖突地區工作有著豐富經驗和部署,但是“如果悲劇發生也沒辦法,畢竟那是戰爭”,廖滿嫦輕描淡寫地面對生命危險。
各種挑戰都是殊榮
廖滿嫦不畏懼死亡,卻痛恨各種無端的“死亡綁架”——無國界醫生國際組織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與保護,不斷被戰火傷害。
2014年1月,有5名工作人員被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擄走,迫使無國界醫生不得不關閉在“伊斯蘭國”控制地區的醫療設施,大幅度縮減醫療救援人員。同年4月,中非共和國的醫院遭受襲擊,無國界醫生國際組織失去了4名員工。而在越來越危險的環境一利比亞、南蘇丹、索馬里等等,如何更好開展工作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醫院成為襲擊目標,病人成為目標,救護車成為目標……這些原本應受到最起碼尊重的僅存之地,不斷地被侵犯。”
2015年10月,由美國主導的駐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對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士市的一家醫院反復轟炸,造成42人喪生,其中有14名無國界醫生員工、24名病人以及4名病人家屬。
這是無國界醫生成立44年來最大的傷亡事件。廖滿嫦一次又一次提出抗議,要求美國展開獨立國際調查,查清事件經過,同責有關人員。一周后,美國總統奧巴馬終于正式電話道歉,并向遇難者家屬表示慰問。
廖滿嫦對此并不滿意,她執著地呼吁國際社會對此進一步調查,并給出解決方案。
廖滿嫦始終無法忘記那一幕。空襲后,她再次去了阿富汗,一位在空襲中肢體受損的同事質問她:“之前戰事緊張時,你說過昆都士醫療中心是安全的,你知道我們會被轟炸嗎?”殘破的身體、質問的語氣、盯著她的眼神,讓她至今難忘。
痛心的事還有其他。在人道救援圈子中,無國界醫生組織未必是受歡迎的。擁有財務自主權是該組織與眾不同的一個地方:其89%的資金來自個人和私人捐助者。這種因財務獨立而具有的靈活性,也招致了批評。“自給自足很重要,這才使你擁有迅速反應的能力。以埃博拉疫情來說,這意味著,在其他人還在開會討論時,我已抵達了疫區。”
在廖滿嫦看來,整個人道救援體系都出了問題。她一年內要趕赴許多國家,不停出差使她對現實有著深入的了解。她講了一個發生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故事:一個無家可歸的婦女,堅強地自力更生養活自己,被視為成功的援助案例,結果發現真相是她當了妓女。“我們的人道救援體系需要被修復,需要進行一次現實檢查,重新回到人道主義的宗旨上。”
董巖據《莫愁智慧女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