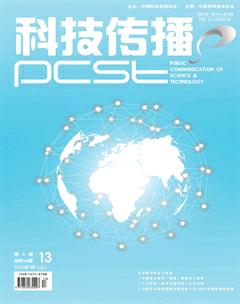中國當代電影的空間敘事分析
楊書源
摘 要 關于“游民”,學者王學泰有過這樣的定義:“脫離社會鐵序約束、庇護,游蕩于城鎮之間,沒有固定謀生手段,迫于生計,以出賣體力或腦力為主,都被視為游民,游民處在社會最底層。”本文選取《榴蓮飄飄》《姨媽的后現代生活》《老唐頭》3部影片中女主人公具有游民回歸色彩的敘事單元,對于影片中以游民的生活遷移的“大城市”與“故鄉”的空間敘事及其背后的“城鄉二元空間”的對立與沖突作為研究主題。
關鍵詞 城市空間;游民;城市經驗
中圖分類號 TU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6)166-0002-01
1 遷移中的城市空間
對于城市空間對于人類生活的景象表達作用,城市社會學家早有論述。按照吉登斯的說法:“所謂場所,不是簡單意義上的(place),而是活動的場景(setting)。”(安東尼·吉登斯,2002)而一個空間的物理組合和社會組織不僅僅構成社會群體的表達,也是社會群體的自畫像,揭示出社會利益結構的空間坐標。美國學者蘇賈指出過:作為一種社會產物,空間性既是社會行為和社會關系的預先假定,又是社會行為和社會關系的具體化。”(愛德華·W.蘇賈,2004)。從考察社會行為者的地位和社會關系的內涵來看,空間性本身還應該是一個媒介,一個在產生意義的媒介。意義的空間就是傳播的空間,而這個空間是生產性的(邵培仁,2006)。
涉及具體的城市空間,周巖在其研究中指出:電影中的城市,一類是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邊緣空間展現;另外一類是欠發達的邊緣城市、城鎮(周巖,2014)。大陸青年導演在涉及寫實題材之時,除了留意農村以外,更多的還是將視角投向轉型過程中的小城鎮。身處其中的人不少是社會的承擔者,他們被遺棄,生活無所依傍且終日彷徨(邱寶林,2010)。
本文選取《榴蓮飄飄》《姨媽的后現代生活》《老唐頭》3部風格迥異,但是均有對于“游民從大城市回歸東北家鄉”的敘事主線,均有對于回歸前后,城鄉二元空間的信息傳達。
3部影片中,女性主人公在城市生活的經歷中,一個在香港做3個月暗娼賺錢的東北戲劇年輕女演員,也就是香港人眼中的“北姑”,一個由于歷史原因在東北草草結婚生子卻又無比熱愛著都市生活的上海老知青,一個在北京從事性交易的城市外來“務工者”。他們共同困境是:雖渴望都市生活,但其在都市生活都受到了到阻滯,必須切斷城市的生活,回到其具有深厚生命根基故鄉。
2 “回歸”前后:市井空間表達
3部影片中的主人公城市生活經驗的起點,從影片的敘事結構來說,是從“大城市”經驗引入開始。
《榴蓮飄飄》導演陳果將市井底層生活敘事經驗運用入影片。以秦燕香港軌跡展開的敘事中,沒有出現與城市文明相關的光鮮事物,作為“都市象征”的高樓大廈也未出現。長達一兩分鐘的固定長鏡頭被大量使用,用于表現街角社會,街景大多是碎片化的,城市街景以及宅屋的取景,如以茶餐廳為例的一個場景內,鏡頭的機位的調度中,常常以秦燕在局促的空間之內的行動作為其手持拍攝鏡頭晃動的根據,這種鏡頭的晃動給觀眾帶來的不舒適感。在鏡頭與鏡頭的組接之間,產生了一種鏡頭外部節奏構成的局促感。比如阿芬的父親洗漱穿衣的中景,攝像機的取景框定范圍以房間的墻壁作為觀眾視域范圍,產生取景框邊沿和室內物理空間(如墻、門)重合的視覺效果。
在《姨媽的后現代生活》中,“碎片化”的都市空間敘事也同樣常見:騙子潘知常在一家小飯館里和姨媽故作風雅,鏡頭迅速搖到窗外的街景,各種市井中的小門面招牌鱗次櫛比,姨媽的頭邊借位招牌上“青春”二字,形成一種諷喻和潛在的危機。然而作為上海都市的“標志物”卻也總在以殘缺的方式出場:金茂大廈、東方明珠,時而會在家或者醫院的窗戶里露出一角。
對于“故鄉”,創作者往往用更加寬闊、靜態的景別來描述空間,相比于都市中的“運動鏡頭”或者是手持鏡頭,鏡頭內部的穩定性增強了。比如在《榴蓮飄飄》中由香港切換到“東北”牡丹江邊上的小城中,在雪地里,用塑料膜包裹著的寬闊的街道兩邊的殘雪以及稀少的人煙構成的運動長鏡頭,讓觀眾在長長的“香港都市經驗”之后,獲得了第一次視覺上的舒緩。在宴請親朋好友慶祝小燕歸來的飯館中黑壓壓的幾桌人吃飯、叫好構成了一個喧騰巨大“人情場面”還有居民樓、火車站候車室、新年的臨時公共戲臺等大量寬闊、具有多樣性的“公共空間”的全景拍攝,讓影片對于之前香港街道的敘事相比之下多了一種“生活感”。在香港的城市街道中,小燕將行走作為到達的生存式的工具。而在東北她生活的城市之中,而行走并不是唯一目的。小燕在香港私密性較強的“生存”經驗變成了公共性參與拓展的“生活體驗”。
創作者很多時候會有意創造一種兩種城市空間在敘事上的視覺對稱片段。在《榴蓮飄飄》中,小燕腰際處始終保留著的一條紅線在她初到香港和歸家以后到澡堂洗澡的兩次特寫的對稱、小燕在香港吃飯時的狼吞虎咽和在家中吃飯時的細嚼慢咽以及姨媽和寬寬在上海的醫院和東北居民樓內出現的兩輪城市夜空中魔幻的大滿月。以及唐彩鳳“歸家——離家”往返沿途之中望向窗外。創作者主觀營造的城市空間的對比營造了對于不同城市空間的張力與戲劇性的一種集中性表達。
3 主人公在自我言說中完成的城市空間表達
除了城市空間這一以非生命物為實體進行記敘的以外,作為城市空間中的行動者的主人公,其實其本身也作為城市空間的一種表達載體,呈現出對于作為“我”與“他者”的城市空間的自覺和想象。
在《榴蓮飄飄》的第一場中,運用到了維多利亞港和牡丹江水景的疊化,秦燕開始了用東北方言敘述:“我的家,就住在一條江上,小的時候,我每天都穿過這條江去上課,原來香港也有一條大海,每天人來人往的,都要到對岸去工作,一年四季都可以坐船或者坐車。”在影片的開頭,主人公就將“我”與“他者”在這個城市中的空間位置交代得非常清晰。而在其與“接客”的香港男人對話中,她卻再也沒有流露出像是獨白中那樣對于“東北人”的自我認同,她聲稱自己是湖南人,四川人,上海人,只在與同行的“北姑”聊天時,才會透露自己是“東北人”的身份。
在《姨媽的后現代生活》中,從鄰居老水和醫院護士的口中可以得知,姨媽給自己編造了一個“洛杉磯海外的親屬背景”用來掩蓋自己的核心家庭的根基在東北的事實。她經常通過與他人的對話實現一種“排他”的城市空間身份中對于自身的獨特性定位。在寬寬剛來到姨媽家中時,姨媽在樓道中對于這個樓道中居民的評價是:“整幢樓都是癟三,像我這樣的正經大學生是沒有幾個。”可看出姨媽雖然身處市井但是清高自我的。此外,姑媽在城市的日常會話之中,標準的普通話與上海話之間游刃有余的轉換,也正是姑媽一方面積尋求著在城市空間中的積極的群體認同。可以說“上海話”的使用,對于主人公來說,是在特定的城市地理空間定位中,對于自我“上海人”的積極定位。
在《老唐頭》中,唐彩鳳在回憶在北京的城市經歷時,是這樣評價自己這次的回歸的“這不是不行了,回家種田吧!”其實闡釋的是唐彩鳳對于都市經驗的慣性,對于東北的疏離與無奈。在紀錄片的最后,唐彩鳳化妝在美容院的特寫鏡頭以及畫眉時她的自述“真的,我太邪門了,到哪里都能碰到老大,都奔40歲的人還漂著呢。”等,其實無一不表現城市生存狀態。唐彩鳳在對于“自我”在不同地理空間中的認知中,她自覺到回故土之后的空間經驗對于她是根本性的,但是同時這種對于生活經驗的評價也是負面的。
回歸前后,人物對于“都市生活空間”的生活慣性,與人物形象的前后反差形成了更多的戲劇張力。在《榴蓮飄飄》中,回到東北老家的小燕由濃妝艷抹、短裙、黃發變成了棉衣、耳罩、短發的普通裝束。然而內心并非徹底回歸,影片尾聲,小燕在家鄉面膜店中問美容師“有沒有進口的面膜?”是對于都市經驗的追溯。姨媽在上海時鮮艷的穿衣風格以及整齊的黑頭發到了東北被一身破棉衣所代替,然而她在上海城市街道之中指責“外地人”不講公共衛生,勒令城管干涉的“潔癖”在東北的居民樓卻依舊存在,面對粗糙簡陋,“家”本能的清潔沖動。對于打掃這一生活細節的堅持,卻是對于城市生活空間在人物內心的追溯。
參考文獻
[1]李道新.“后九七”香港電影的時間體驗與歷史觀念[J].當代電影,2007(3):34-38.
[2]張浩.“九七”后香港電影中的大陸形象研究[D].重慶:西南大學,2013.
[3]邱寶林.新世紀中國青年導演電影話語建構圖景與傳播邏輯[D].上海:上海大學,2011.
[4]陳曉敏.香港電影中內地女性形象的變遷[J].電影文學,2010(2):25-26.
[5]周巖.現代轉型中的城市想象[D].杭州:浙江大學,2013.
[6]石川.族群認同與香港電影中的“北佬”形象[J].文藝研究,2011(11):2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