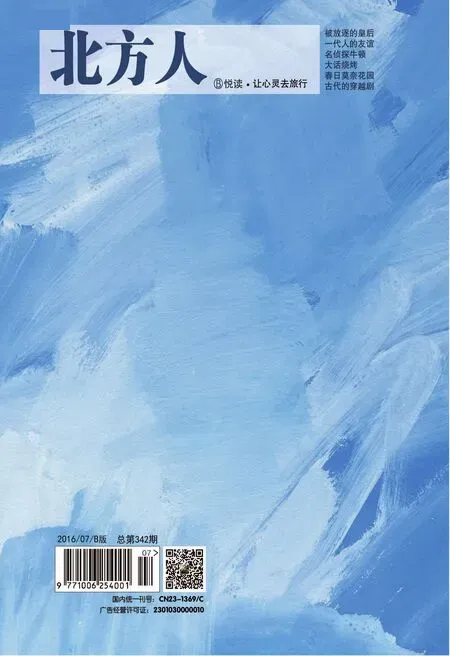精準醫療:你的疾病獨一無二
文/曹 玲
?
精準醫療:你的疾病獨一無二
文/曹玲

不遠的將來,基因分析師以及分析基因數據的軟件會變得熱門,遺傳學會日益進入醫療保健領域……你的病就像你的個性一樣,獨一無二,并且被單獨對待。
2015年年初,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5年國情咨文中談到了“人類基因組計劃”所取得的成果,并宣布了新的項目“精準醫療計劃”。
簡單來說,精準醫療就是先創建一個龐大的患者醫學數據信息庫,研究人員通過研究分析比對患者信息與數據庫里的信息,進一步了解疾病的根本原因,從而開發治療針對特定患者特定疾病基因突變的藥物,并確定哪些患者服用哪些藥物,以及預測可能出現的副作用。
2015年,全球精準醫療市場規模近600億美元。未來5年,年增速預計將超過15%,是醫藥行業整體增速的3倍—4倍,其中基因測序行業的增速將超過20%。
新的藥物
早在1860年就有醫生提出,舊有的藥物研發和使用是對人類資源的浪費。美國著名作家兼醫生奧利佛·溫德爾·霍姆斯認為,若將所有的藥物“沉入海底的話,對人類來說是一大福音,不過對魚兒們卻是詛咒”。
霍姆斯是在考察當年的醫療情況后提出的這一觀念,他發現很多人不僅服藥無效,反而深受藥品副作用之害,其深層的原因就是沒有實施個性化治療。
時至今日,精準醫療、個體基因組研究和蛋白質生物化學研究為精準用藥、少用藥和有效用藥提供了更深層次的科學解讀,提出了需要治療的總病例數(NNT)的概念。總病例數是一種對臨床藥物或其他治療效果的評價指標,指的是有多少人接受治療或預防性服藥才能確保其中一人有效或受益,NNT值越小越好。
經過大量的臨床調查,NNT顯示的藥物療效低得令人吃驚。例如,如果2000人每日服用阿司匹林堅持兩年以上,才能防止一起首次心臟病突發事件,即NNT為2000。同樣,當哮喘發作時有8個人使用類固醇藥物,才能避免一次入院,也即對一個人有效,NNT為8。如果鼻竇炎發作,15個人使用抗生素,只有1例會改善或治愈,NNT為15。人們感到奇怪,阿司匹林、類固醇藥物和抗生素是公認的防治心臟病、哮喘和鼻竇炎的有效藥物,為何它們的實際療效也如此之差?事實上,因為基因、環境和生活方式不同,很多人疾病痊愈未必是藥物的功勞,而是機體的自我修復所致。這也證明了霍姆斯的判斷,很多藥物是人類不需要的。
從NNT的角度看,在一般的臨床治療中NNT達到30就已相當不錯,低于10的比較少見。這也提示,藥物的研發和使用,如果不是針對每一個體,至少也需要針對小眾人群精準開展。
為什么同樣的藥物在不同人體內差異如此之大?人類基因組計劃使我們知道了個體之間的差異,人體的30億對堿基中包含0.1%的差異,即每個人的基因組中有300萬對堿基的差異。盡管比例很小,但藥物療效的個體差異正源于此。
在癌癥治療領域,精準醫療的重要性更為明顯。以靶向藥物易瑞沙為例,從整體上看它對肺癌的療效并不好,但在具有EGFR基因突變的肺癌病人中效果很好。易瑞沙非常昂貴,每個療程16萬元左右,一個療程為一個月,病人在進行治療之前必須檢測EGFR基因突變。
基因檢測還會提示不同人群服用某種藥物后的副作用大小。比如常用化療藥5-氟尿嘧啶(5-FU),有很少量的人使用后不僅無效還會產生嚴重副作用。5-FU可以阻斷細胞的分裂,通常口服或者靜脈給藥,對快速增殖的癌細胞很有效,同時也會殺死人體正常快速增殖的細胞,比如分布在口腔黏膜和消化道壁的細胞,長期高劑量使用5-FU可引起口腔潰瘍、腹瀉和其他腸道改變,還可能會導致脫發以及紅細胞、白細胞和血小板的減少。一般情況下醫生應用5-FU時非常謹慎,足量而不過量。
人體肝臟中有一種酶可以將5-FU降解為無活性物質后排出體外,如果父母將編碼這種肝臟酶的基因遺傳給我們,我們可能僅有一半能正常工作的酶。一半的正常酶量是遠遠不夠的,若接受正常劑量的 5-FU后將出現嚴重的毒性,大約有1%的人存在這種情況。
另外一種更罕見的情況是,如果父母基因編碼的酶都沒有活性,那么5-FU將持續存在于血液中,而且含量很高,用藥的后果不堪設想。幸運的是,這種情況非常罕見,發生率只有0.001%。如今研究人員已經發現了這個酶和編碼它的耐藥基因,如果能在使用5-FU前檢查一下病人是否存在異常的基因,可以判斷用藥的風險。事實上,目前并沒有普遍開展這種檢測,因為有需求的病人比例很小。但是如果不幸碰到,可能就是致命的。
所以,人們希望未來的藥物將針對每一個體或一小群人進行定制,實現真正的“對癥下藥”。
測序革命
精準醫療的發展離不開基因檢測技術的進步。
基因(DNA)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象征。它傳達出一種強大的理念,每個人都可以科學地還原成一份明確而具有決定性的編碼。
基因測序的歷史并不長。第一次人類基因組測序始于1990年,耗時13年,花費27億美元,回顧起來就像是眾人參與的一場混戰。2007年,克萊格·凡特博士的基因組研究花了4年時間,耗資1億美元。2009年,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斯蒂芬·夸克在一周內完成自己的基因組測序,花費不到5萬美元。
2009年,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也進行了自己的基因測序,并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我的基因,我自己》一文。
平克預測:“全基因組測序的價格將變得平易近人,人們必將開發出相應的軟件,持續不斷地提供個人醫療解讀。回顧往昔,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后的頭10年,可以被看作改變每日醫學實踐前的漫長熱身。我們已經領會到基因測序帶給我們的影響,它可以被用在癌癥治療,定義個人的基因藥物和人體的相互作用,以及闡明先天疾病上。”
他說的沒錯。基因測序越來越普遍,成本下降幅度甚至遠超摩爾定律。利用近期被稱為下一代測序平臺的DNA測序技術,美國著名測序公司Illumina的HiSeq測序平臺每年可對1.8萬個人類基因組進行測序,使得單個基因組測序的成本將下降至約1000美元。業內認為,這是一個大規模的測序過程,測序首先要到臨床,再從臨床到相關的研究。
美國的測序技術非常發達。位于東北部的馬薩諸塞州和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亞州聚集著大量的生物醫藥企業,它們中近一半的企業從事著與基因相關的工作,比如基因芯片檢測、基因測序等等。
隨著測序成本的飛速走低,以及測序技術平臺的效率逐步趨于完善,樂于接受測序服務的人群數量將會呈現對數式的大幅上升。當今,基因檢測在各種檢查和治療下變得更加有用,包括癌癥、智力發育遲緩、出生缺陷和原因不明的疾病。
數據解讀
精準醫療領域令人擔心的一個現狀是,許多醫生沒有資格做基因檢測,或者不能準確地傳達給病人結果。
美國波士頓兒童醫院的遺傳學家戴維·米勒遇到過這個問題。2014年秋天,一對夫妻帶著5歲的女兒找他看病。女孩協調性很差,并且明顯矮小,很容易感染疾病。之前的內科醫生已經讓她進行了基因檢測,以確定她的發育遲緩是否與已知的遺傳條件吻合。如果是的話,或許能找到某種療法。結果表明,女孩的22號染色體缺失了部分基因片段,這意味著她患有迪格奧爾格綜合征,即先天性無胸腺或發育不全,屬于原發性細胞免疫缺陷疾病。醫生給女孩父母的解釋非常可怕,迪格奧爾格綜合征常見癥狀包括學習和發育遲緩,心臟缺陷,精神疾病風險增加比如精神分裂癥,并且沒有已知的治療方法。當米勒重新核對檢測結果時發現,22號染色體上基因缺失的部位并不在導致迪格奧爾格綜合征的位置,可能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遺傳標記。女孩并沒有得綜合征,她的父母松了一口氣,再也沒有必要監視孩子的心臟和精神健康。
2015年初,匹茲堡大學馬吉婦科研究所遺傳生殖專家亞歷山大·拉伊科維奇發表文章,記錄了另一個錯誤判定迪格奧爾格綜合征的例子。與米勒的病人一樣,基因檢測能確定染色體缺失,但不能指出準確的位置。
美國醫學遺傳學家和遺傳咨詢師認為,這樣的判斷失誤很常見。有時候,這些錯誤會造成更大的傷害,而非只是引起病人和父母的焦慮。
還有一些業內人士指出,很多疾病和基因之間的關系并沒有人們想的那么確定。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人們認為少數基因變異是導致疾病的主要原因,但是對于糖尿病、心臟病和癌癥等普遍的疾病來說并非如此。目前,年齡、性別、體重和一些簡單的血液檢查能夠更好地預測2型糖尿病,對于高風險人群開出的預防措施依然是健康飲食、多運動。
有時候,人們發現高風險的遺傳變異能發揮多大作用,更取決于環境、文化和行為。例如,與肥胖相關的主要遺傳變異只和那些上世紀4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關系密切,極有可能是因為“二戰”后出現了低體力活動、高熱量攝入的生活方式。從這個角度來說,或許并不是每一種疾病都需要基因測序后再進行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