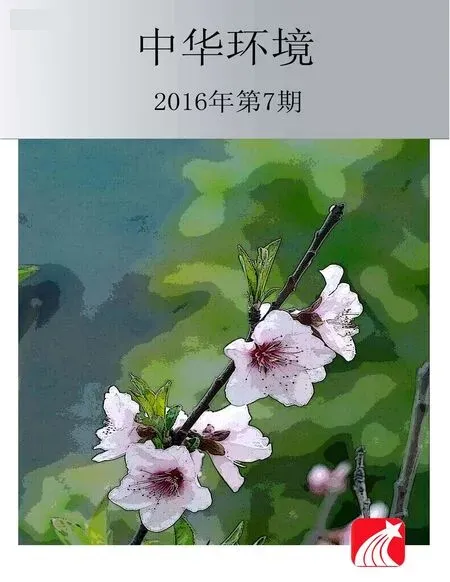常紀文:行路難,堅守更難
楊雪杰
常紀文:行路難,堅守更難
楊雪杰
2015年底,“2014—2015綠色中國年度人物”評選活動在北京拉開序幕,作為候選人之一,常紀文身上的標簽與頭銜引人注意,他既是中國民工民主黨中央委員、北京市委副主委,也是國務院發展中心資環所副所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教授、湖南大學博士生導師,同時擔任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環境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被聘為國務院安委會咨詢專家、安監總局理論專家……
見到這位綠色年度人物候選人之時,他正準備參加當天國合會召開的“法治與生態文明建設課題組”2016年度第三次工作會議,或許是為了躲過北京的早高峰,他提前一個小時便到了會議現場,并稱,現在的生活,基本圍繞科研、上課、座談會而轉了,屬于個人的時間少之又少。
機緣巧合走進環保法
常紀文的個人資料顯示,他于2001年7月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在著名法學家馬驤聰教授和經濟法學家王曉曄教授的合作指導下,成為新中國首位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博士后。而對于最初選擇環境法作為研究方向,他卻說這是一個“機緣巧合”。
選擇的起點是25年前。當時,常紀文大學本科選擇的專業是環境規劃與管理。“那時候是農村孩子,一看到管理兩個字很高興,覺著讀管理就可以做官了”。對于走進環保領域的這個最初的動機,常紀文并不諱言,“這是真實的想法,當時填報了兩個志愿,一個是審計,一個就是環境規劃與管理”。后來,常紀文就被武漢大學環境規劃與管理專業錄取了,并對環境法選修課產生了興趣。當時武漢大學有一個政策,成績好的學生可以同時讀雙學士,于是,法律就成為他的第二專業,也為他之后在資源環境法領域研究奠定了基礎。
“一直到現在,我做資源環境保護法研究的目的是想切實保護我們的環境,但最初并不是這個想法,在我讀大學之前,環保是什么我們都不知道,就是簡單地把環保等同于環衛,打掃衛生之類的。環保是工業發展之后才有的,當時純粹是看到管理二字,才步入環保領域,所以我說這也是一定意義上的機緣巧合。”
黨政同責——跨界研究受益良多
2003年,常紀文留在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工作,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和社會法研究室副主任、主任。2010年7月,通過公開選拔擔任北京市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副局長。
談到安監經歷,他表示“跨界有好處,跨界研究能夠相互借鑒”。
北京市安監局副局長的經歷,對于他而言,“是另一個機緣巧合,但是,一個人要把巧合變成機緣,需要有基礎”。當時,常紀文為環保部污防司固廢處做化學品法相關研究已有三年,對國內外危險化學品的安全管理有了比較深入的認識,在多家期刊上發表文章,并出了一本專著,該項課題結題后,恰巧遇上北京市安全局副局長的公開選拔,而危險化學品的三年研究也讓他在此次選拔中脫穎而出,“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有工作基礎也就去干了”。
在安全生產領域一干就是三年半,2014年,常紀文重返學術界,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擔任資環所副所長。盡管在安監局的時間不是很長,卻對常紀文以后的研究工作有了很大啟示。
2013年12月,常紀文在《中國環境報》上發表“環境保護需黨政同責”,首創了“環境保護黨政同責”理論,提出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都對環境保護負有責任,出現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事件,或者環境質量退化時,都要追究地方黨委和政府的領導人的責任。這一理論的提出正是來源于安監局的工作經歷。
201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提出安全生產黨政同責的理念,其時,擔任北京市擔安監局副局長的常紀文,利用學者和官員的雙重視角,配合國家安監總局進行安全生產黨政同責的體制和制度、機制設計,在安全生產刊物上發表了幾篇安全生產黨政同責的理論文章,他撰寫的調研報告被國家安監總局領導批示,后為全國推介。2014年5月,國家安監總局邀請他為黨組擴大會講授安全生產黨政同責的推進問題,并聘任他為國家安全生產理論專家。
“環境保護和安全生產都屬于公益性質,很多工作需要政府主導,企業履行主體責任,行業參與,社會監督”,安監局的經歷與環境保護黨政同責的提出息息相關,而對于環境保護黨政同責要解決的問題,常紀文直言“關鍵要解決地方環境保護是否重視的總根源問題,環境保護地方黨委不重視,政府想重視也重視不起來。我們是黨領導的政府工作責任制,所以必須要讓地方黨委負起責任”。
2015年,中央出臺《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出現環境損害既追究政府干部責任,又要追究黨委干部責任。常紀文目前正參與中央“生態文明建設考核辦法”的起草工作,正是希望通過轉變考核方法使地方更加重視環境保護工作。談到未來環保領域黨政同責的推進,常紀文充滿樂觀,“黨政同責已經具有可操作性,目前各個地方均在起草環境保護黨政同責考核辦法,有的省委已經出臺,各級都在推進,一級推一級,這項工作才能夠一竿子插到底”。

參與《野保法》修訂
2016年7月2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在北京閉幕,表決通過了新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對放生等行為進行了規范。新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將野生動物放生至野外環境,應當選擇適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當地物種,不得干擾當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產,避免對生態系統造成危害。隨意放生野生動物,造成他人人身、財產損害或者危害生態系統的,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此次《野保法》修訂得到了法學界的充分參與,對于野保法修訂,常紀文曾建議,“要有長期的戰略,也要立足于目前”。我國一些野生動物的馴養繁殖已經成為事實,而且規模很大,驟然停止難免會帶來社會不穩定問題。因此,他建議要有一個堅定的目標,對于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嚴禁商業性馴養繁殖,并制定具體時間表;不能虐待野生動物,對待野生動物要符合善良風俗和公序良俗。“對于福利和動物利用,盡可能少用或者不做商業性的利用,禁止虐待性的利用,現在還在利用的應當加強福利保護”。
在常紀文看來,盡管修訂過程中困難很多,歷經一審、二審、三審,但是總體上來看,還是往前在走,而且進步很大。

7月2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十一次會議表決通過新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 。CNSphoto 供圖
未來:用中國的思維和方法解決中國的問題
2016年1月,常紀文發文建議把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擴展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環境需要和緊缺的資源供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論述在“十三五”規劃綱要第五章“發展主線”得到采納:“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必須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供給能力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在他看來,環境問題的解決需要革命性的措施。
談及當前的環境法治建設,他認為目前正處于轉型期,這個轉型期是中國經濟上的轉型期、社會上的轉型期,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型的階段,而我國的環保法也正處于邁向發達階段的環保法,已經借鑒了國外好多理論實踐,所有該借鑒的、能借鑒的基本都借鑒完了,下一步,我國的環境法治建設應走向本土化,立足于創新,用中國的思維和方法解決中國的問題。
在常紀文看來,黨政同責就是基于中國本土的思考,是中國本土化的、管用的措施,西方一些實踐對于我國而言并不適用,我國的制度設計不能脫離黨領導的原則、不能違背國家體制,必須在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結合情況下,設計管用的制度和機制。“學歐美學起來容易,但是沒什么效果,要參考,更要立足中國的體制制度和機制”。
“行路難,堅守更難,越是艱難的時候,越是希望到來的時候”。對于環保,他感嘆道,要有建設生態文明的定力,不能因為短期的經濟下行就放棄環保轉而繼續發展污染型經濟,同時要有長期的戰略,通過科技和管理的不斷創新,真正進入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新常態。“轉型期雖然痛苦,但不能三心二意、半途而廢,否則無法向后代交差”。
“向后代交差”“為后代考慮”,在常紀文看來,這是我們環保法里面所缺少的,盡管環保法目標里有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但真正為后代考慮的內容少之又少。
訪談結束時,常紀文再次提到,無論是科研、做人還是社會發展,都要有定力,有付出就有獲得,所有的機緣巧合都需要珍惜,也都需要基礎的積累。
2016年 7月,“2014—2015綠色中國年度人物”評選結果揭曉,常紀文當選為十大綠色中國年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