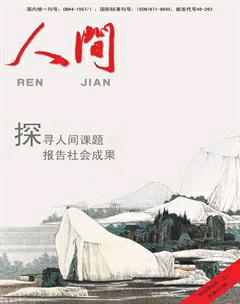花·存在·人類學(xué)
張苗苗
(廣西師范大學(xué),山東 青島 266000)
花·存在·人類學(xué)
張苗苗
(廣西師范大學(xué),山東 青島 266000)
花朵為什么開(kāi)放,在愛(ài)者的眼中開(kāi)放,而不問(wèn)為什么——花開(kāi)超越了哲學(xué)的追問(wèn)。
不然,為什么凝視這些陶器上的花卉紋時(shí),帶來(lái)一種更為日常的經(jīng)驗(yàn)。我猜度最初一定是一雙女性的手完成了這些紋飾的涂繪,她一定是在花中尋找自我的可能性。
數(shù)千年過(guò)去了,造型各異的花卉紋出現(xiàn)在不同的藝術(shù)品上,人類對(duì)花朵的凝視之愛(ài),從《詩(shī)經(jīng)》時(shí)代以來(lái)未曾改變:“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那種灼熱和投入的姿態(tài),委身于愛(ài)情的火焰,甚至灼傷了我們的眼眸;“參差荇菜”似乎是君子的愛(ài)情宣言,帶來(lái)“求之不得”的詩(shī)意矛盾,美麗的女子在綻放與枯萎之間,黯然心碎;“竹葉”紋形象征著貞潔與恬靜,高禖石上的“竹葉”紋成為對(duì)貞女柔韌生命的禮贊。
花有自己的夢(mèng)想:那是曼逸的花姿或安止或開(kāi)放,仿佛女性呈露出自己的身體,朝向世界。那是一個(gè)美妙而神圣的時(shí)刻的降臨,于是,我們凝視,無(wú)論是“水草”刻畫(huà)紋,還是“葉瓣”紋,這些形似眼眸的紋飾不也同樣凝視著我們?那是一種不死目光的余存。花紋不是視覺(jué)的炫目,而是來(lái)自于內(nèi)心的傾訴,即使工藝上可能還很粗陋,但陶器上的花開(kāi)自心中。這些花朵一旦被繪制上彩陶上,哪怕恒久埋沒(méi)于大地,回歸塵埃,幾乎就一直處于黑夜的背景中。直到某一天它們被人類學(xué)家從沉睡中喚醒,于是,這一次出現(xiàn)了花的存在之思:世界進(jìn)入了黑夜,在黑夜里只有花朵還可能發(fā)出最后也最為燦爛的光芒,觸及這些花朵的重生,這些來(lái)自深淵的花染上了一層莫名的憂郁,但它們不在黑夜中成眠,而是要更為激烈地燃燒,成為“皎若夜光尋扶木”的那種詩(shī)意寄予,這使得這些腐朽陶器上氤氳著生命的氣息,不死的氣息!
在人類學(xué)者的眼中,這些素樸而雅淳的花卉紋飾,從來(lái)不是死寂,而是活生生的,這些融合了審美性與人文性的藝術(shù)形式,是人類生殖崇拜文化的藝術(shù)見(jiàn)證,是原始初民的愛(ài)欲的簽名。花,是人類學(xué)所要思考的句法和修辭。有一種花朵或者花紋的人類學(xué)嗎?面對(duì)花朵,人類學(xué)轉(zhuǎn)化為對(duì)生命存在的思考,最為富有生命意涵的發(fā)生人類學(xué)。然而,最初這些花紋的創(chuàng)造者卻永恒的缺席了,僅僅留下殘破的圖像、漫漶的歷史和斑駁的記憶,當(dāng)時(shí)發(fā)生了什么?這些花卉紋為什么會(huì)被描繪出來(lái)?格羅塞認(rèn)為,原始民族的造型藝術(shù)非但不能證明是宗教的,甚至也不是審美的。格羅塞謬以千里!花的精神是自我燃燒,是心的余燼,是精神燃燒的灰燼,以花卉為飾,乃是自我哀悼的藝術(shù),或者說(shuō)最為優(yōu)美的自戀,乃是自我獻(xiàn)祭,乃是自我精神的燃燒,是憂心如焚,是灰燼的收集。這是藝術(shù)的真理,又何嘗去分原始或現(xiàn)代,恰恰是原始藝術(shù)更為直接的面對(duì)天空和大地,才打開(kāi)了生命存在的空間,那也是審美游戲的場(chǎng)域,花才是唯一心性宗教。
歷史的黑夜要求內(nèi)心在黑夜的無(wú)所凝視中,讓生命成為光焰,因此在生產(chǎn)力落后的原始社會(huì),先民對(duì)黑暗的經(jīng)歷更為徹底,也許這就是歷史進(jìn)程中創(chuàng)傷所致?我們看到了這些色調(diào)偏深的陶器上,那一圈紋飾帶來(lái)一種刻骨銘心的情感,一枚枚花瓣朝向同一個(gè)方向,似乎旋轉(zhuǎn)了起來(lái),如同高禖儀典上的“桑林之舞”。這是一首無(wú)聲的夜歌,心心相印的螺旋圈,是一個(gè)個(gè)視覺(jué)的漩渦,也是一層層聲線的吸納。彩陶上的花朵們沉迷于自身燃燒的節(jié)日,凝視花朵乃是心的節(jié)日:內(nèi)心的激烈獲得了外在的形態(tài)。造型的簡(jiǎn)化,反而是最生動(dòng)傳神的暗示,每一束花火點(diǎn)燃了我們的身體,仿佛靈魂出竅一般:出離自身并且在跳躍中燃燒,因?yàn)樗齻円c(diǎn)亮的是黑夜本身。
原始藝術(shù)或許就是一場(chǎng)美的考古,在時(shí)間的厚度里敲敲打打,人類學(xué)家的目光聚焦于時(shí)間在消逝與挽留之間的那種停頓之間?如果有著對(duì)這個(gè)“之間”的思考,難道不是對(duì)花的思考?從無(wú)到有,從有到無(wú),花朵僅僅是中間物,是轉(zhuǎn)瞬之間的過(guò)渡之物。僅僅將花卉紋飾視為對(duì)女性的生殖崇拜,還是一種男權(quán)中心主義眼光,很難想象,最初的制陶人不是一位女性,不是女性對(duì)自我生命的贊美和思想。生命的詩(shī)意和哀婉,以自身作為女性特有的細(xì)膩感受,揉捏入手中的泥土,最后凝結(jié)為一朵花的綻開(kāi)。
碰觸這些嬌嫩的花朵,只能溫柔地吮吸,如同蝴蝶淺吻玫瑰,水與風(fēng),光與花,在彼此的親近中有著生命元素的交流。這些滋養(yǎng)生命的果實(shí),接受陽(yáng)光雨露的滋養(yǎng),在風(fēng)雨中無(wú)數(shù)花枝之間的交相輝映,是姿態(tài)的浪漫,也是生命在存在中涌現(xiàn)。以至于凝視這些象征性的紋飾,是有著細(xì)微差異的重復(fù),讓人陷入激情而性感的眩暈中。
花朵是植物,“從表象來(lái)看,花瓣、葉片、某些果實(shí)可狀女陰;從內(nèi)涵來(lái)說(shuō),植物一年一度開(kāi)花結(jié)果,葉片無(wú)數(shù),具有無(wú)限的繁殖能力。”因?yàn)槠湫螒B(tài),花枝繁盛,甜美而并不艷俗,讓我們側(cè)目。花“蒂”綻放出來(lái),對(duì)其崇拜、對(duì)其祈求,果實(shí)豐盈、蕃衍不息。但是,花一旦選擇了開(kāi)放,也就有著被摧折的可能性和威脅,被風(fēng)雨所毀容,花枝的折斷如同割禮的戕害,這并非一個(gè)禮物,反而是禮物的褻瀆。還有什么比花朵更為柔弱,更需要呵護(hù)?在時(shí)間的權(quán)柄上成塵、成灰,然而這也是大自然地傾吐,從血脈上,從淵默的深處。凝視這些來(lái)源于久遠(yuǎn)歷史的余物,那是一種既迷戀的興奮又壓抑的感傷。花,柔弱卻勇敢的燃燒,永遠(yuǎn)不會(huì)麻木,哪怕瞬間就化為灰燼,或是在漫漫歲月中不會(huì)人知的枯萎,但此凋零卻留給我們一個(gè)深刻的美!
在黑夜中低吟的花朵,也是晚安的別名,花是夜晚的溫存與問(wèn)安,乃至于花瓣的盛開(kāi)就是夜色之吻!生命的種子在黑夜播撒,如同《小雅·甫田》寫(xiě)道: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nóng)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原始初民的生命風(fēng)格如此奔放,又如此舒展,如此迷人的愛(ài)欲的歌唱,是花朵最初的吟唱!是從夜的更深處傳來(lái)的合歡吟唱!
極富象征內(nèi)涵的花卉紋,對(duì)于那些原始初民而言是同樣也是一個(gè)光耀奪目的女神化身,如同我們?cè)凇洞笱拧ど瘛分锌吹降模苋藭?shū)寫(xiě)了其始祖姜嫄的神跡故事,“履大人跡”而生子“稷”。在原始社會(huì),思想要從混沌中開(kāi)端極不容易,個(gè)體生命如果面臨虛無(wú)的深淵還能夠在其旁自由的舞蹈,那種綽約的身姿一定是女性所獨(dú)有的。她們找到了自己的語(yǔ)言,從而在花的紋寫(xiě)中尋找著身心靈動(dòng)的表達(dá),有所顧盼,卻又怡然獨(dú)立,如同一支花的綻開(kāi),那種羞怯姿態(tài)之為思想最初的開(kāi)端。
人類學(xué)對(duì)人類文明起源的考察,不就是在觸及這個(gè)開(kāi)端的羞怯(Scheu),“我們通過(guò)觀看那不顯眼的簡(jiǎn)樸(Einfache),越來(lái)越原發(fā)地獲得(aneignen)它,并且在它面前變得越來(lái)越羞怯,而學(xué)會(huì)這種注意。”這個(gè)羞怯,落在生命最為切近的感受上,難道不是對(duì)于隱藏在女性身體下的神圣禁區(qū)的好奇和探秘。所以,再一次,凝視這些花紋,譬如大汶口出土的彩陶,花朵的紋樣有的由數(shù)片花瓣組成,并在花瓣上畫(huà)出葉脈紋,將花瓣一分為二,甚至在中間用濃重的黑彩畫(huà)出花心。花瓣也是唇瓣,打開(kāi)這個(gè)唇口,并進(jìn)入、停留,那是對(duì)花之核心的觸及,是生命神邃的開(kāi)放,仿佛兩具芬芳的肉身融化了彼此。在這個(gè)身體被點(diǎn)燃的時(shí)刻,一顆心朝向另一顆心狂跳,這是花心的顫栗(Erzitterung),是肌膚的感發(fā)。
“最深的是皮膚”——這句來(lái)自于瓦雷利對(duì)藝術(shù)思考異常神奇,陶器的平面就是如最深的花朵之皮膚了,如此表淺也如此深邃,這個(gè)平面的張力或皺褶的撐開(kāi)是原始初民對(duì)于存在最為直接的經(jīng)驗(yàn),那種獨(dú)特的時(shí)間和空間的折疊,都發(fā)生在這個(gè)最為平面也最為深邃的皮膚上。這些花卉紋就是陶器的皮膚,觸及皮膚更深層的肌理讓我們感受到了生命力的悅動(dòng),躍動(dòng)與涌動(dòng),有著對(duì)生存的焦慮,也有著美感消失的疼痛。
然而,生命的柔韌或者堅(jiān)韌,不就是面對(duì)疼痛,而依然選擇吟唱出生命之歌。是的,從當(dāng)初荒涼的大地上,花,一直吟唱著生命的激情和柔情。
歌聲不息,大地上繁衍的生靈,生生不息!
Q98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1671-864X(2016)08-0051-02
張苗苗(1991-),女,漢族,籍貫山東青島,廣西師范大學(xué),民俗學(xué),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