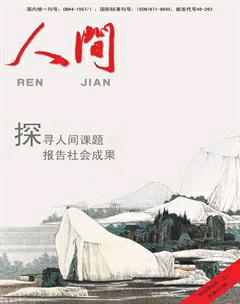莊周“逍遙”的境界之辨
馮磊
(西北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陜西 西安 710000)
莊周“逍遙”的境界之辨
馮磊
(西北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陜西 西安 710000)
一提到莊子,就不得不說莊子的逍遙游,一說到逍遙游,就不得不講鯤鵬、蜩與學鳩的故事。物各其性是不論大鵬鳥、鯤魚,還是蜩與學鳩,翱翔九萬里是逍遙,決起而飛也是快樂,逍遙和快樂在境界上是有不同的,正如西方哲學所追求最高的善,即至善,也是沒有莊子所說的逍遙游的境界高。
莊子;逍遙;逍遙游
逍遙游已經成為了道家的境界高地,特別是莊子的代名詞。西晉莊學的研究大家郭象在對《莊子》一書作注時,這樣寫道,“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1],郭象理解的逍遙游大概是鯤鵬,蜩與學鳩,都有體積大小之分,鵬的背幾乎幾千里,翅膀像云彩一樣。雖然體積有大小之分,但是他們的逍遙只有鯤鵬、蜩與學鳩自己才會體會,鯤鵬有鯤鵬的逍遙,蜩與學鳩也有他們自己的逍遙,快樂。
逍遙應當是只有鯤鵬的翱翔萬里,才可以稱之為逍遙,縱橫萬里。當然,蜩與學鳩的快樂是應自由,如果稱之為逍遙,確有不當,莊子的思想和他的文風一樣,汪洋恣肆、天馬行空。我們是猜不透、抓不著,就像莊周夢蝶一樣,是蝴蝶在夢我,還是我在夢蝴蝶。鯤鵬之大我們只能遙想,不可比劃,所以說,這樣的情形,似乎只有莊子才可以想得出來。
一、“逍遙”境界之源
大鵬鳥的志向在天池,因此它會不遠萬里,長途跋涉,任何艱難險阻都阻擋不了它進取的目標,而蜩與學鳩在自己的生存模式下,只需要吃飽,徜徉于它的領地即是快樂的。雖然蜩與學鳩的快樂的獲得,比鯤鵬獲得的快樂看起來簡單得多,但是它們可以“物各其性”,從而獲得快樂的形式有所不同,其實它們各有各的快樂。對于快樂的理解,在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中這樣寫到,“既然快樂被一切生命物追求,這就表明它對于所有生命物是最高善”[2]。西方哲學把追求所有的目的,叫做至善,快樂也就和善的可以劃約等號,而東方哲學中,特別是道家代表人物莊子的逍遙境界是比快樂更高一層的,所以我也可以給“逍遙”做另一個西方式定義,那就是“至樂”,以此來區別西方式的“至善”。
莊子的逍遙境界,不僅是超越現實,更是超越未來。在那個農耕的奴隸社會,溫飽基本上是人們的普遍追求,只有諸侯貴族們或許才會享受生活。而莊子這樣的哲學家就去思考人生,感受人生,實屬不易。或許正是在那個戰亂的年代。莊子在尋求一種出仕的人生態度,我們現在看起來道家是消極避世,我更愿意說莊子在尋求另一種超脫的生活。
二、“逍遙”境界之辨
莊子的內篇——逍遙游,為我們講到了鯤鵬之大,遷徙至南冥,“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2]莊子通過極其夸張的手法,把鵬的狀態為我們展現在眼前。或許莊子在他那個時代也是道聽途說有鯤鵬這樣的巨物,但莊子借物表意,給予我們無盡的想象。莊子認為,一個人應當突破功、名、利、祿、權、勢、尊、位的束縛,使精神活動達到優游自在,無牽掛、無阻礙的境地。全篇以奇特的想象和浪漫的色彩,用寓言和比喻的方法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要使人的精神活動入乎優游自在、無拘無束的境地,必須順其自然,超脫現實,明“無用之用”,臻于“無己”、“無功”、“無名”之境,將自己與萬物混為一體,而切不可為外物所役,為功名利祿、權勢尊位所束縛。
晉代的郭象和唐朝的道士成玄英,都是是研究莊子的大家,他們研究的角度和觀點雖然不盡相同,但在解釋《逍遙游》中的鯤鵬與蜩、學鳩的對比上,二人的理解大致相同,都主張物各異其性,性各異其情,不應按照一個統一的要求來衡量是否逍遙自由。大鵬摶風九萬,小鳥決起榆枋,雖然遠近相差很大,在適性方面來說是一樣的,各自都能盡己之能,取得自由。故而,“雖復升沉性殊,逍遙一也。亦猶死生聚散,所遇斯適,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應當說,這樣的解釋是違背了莊子《逍遙游》本旨的。后人多承襲兩人的觀點,是沒有理解透莊子的思想在達觀中蘊涵著進取。《逍遙游》中所講的明乎“小大之辯”。人不論能力大小,只要善于積累,立志高遠,那么即使如蜩、學鳩般決起榆枋,如芥為之舟般游于坳堂,也是以積極態度的態度入世。“天生我才必有用,直掛云帆濟滄海”。相信通過自身的努力,終有展翅高飛的時候。
三、“逍遙”之境界
莊子的《逍遙游》中是開篇是這樣來介紹他的逍遙境界的。莊子運用寓言的筆法,大筆揮灑,以描寫神奇莫測的巨鯤大鵬開端,向我們展示了一幅雄奇壯麗的畫卷:在那無風洪波百丈,溟溟無端崖的海中,有一條“不知其幾千里”長的巨鯤,它竟又變化為一只大鵬,當它騰空而飛之時,斷絕云氣,背負青天,垂陰布影,若天邊彌漫之云。這只鳥并不甘心在荒涼的北冥蟄居,它向往“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的自由翱翔,它向往南冥的生活,于是,它振翅奮飛,擊水三千,然后盤旋而上,高飛九萬,飛至半年,到達天池,才滿志而息。在文中,他先是以大鵬形體之大、飛翔之高、憑借風力之厚和蜩與學鳩形體之小、飛行之低、憑借風力之薄作對比,描繪了不畏艱難險阻、執著于自己的追求、展翅翱翔的大鵬形象,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安于現狀、不知進取、沒有追求的蜩與學鳩。“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而止,時則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九萬里而南為?’”對于學鳩的嘲諷,莊子斥責曰:“之二蟲又何知!”。接著,莊子轉而從生命的長度上來論述見識的差異。他展開想象,虛構出了以“五百歲為春,以五百歲為秋”的冥靈甚至以“八千歲為春,以八千歲為秋”的大椿,并提出了“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觀點,并由此得出結論:此小大之辯也。他善于運用這些子虛烏有的東西來闡釋自己的哲學,毫不吝惜,卻又真誠無比。
逍遙是一種優游自得,無拘無束,不受羈絆的生活。在如今這個物欲橫流的現實世界中,人與人之間不再有一切相對價值觀念,如尊卑、貴賤、高下、大小、美丑、善惡、得失、是非……所引生的惶恐和爭斗。耳目的錯覺和欲望的紛馳都會被凈化,因之,一切人為加諸于人類身心的羈絆也都解除,人生便能獲得自在逍遙的境界了。
[1]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莊子集釋卷一上第1頁.北京,中華書局. 2013
[2]亞里士多德.著/廖申白 譯注.尼各馬可倫理學:第十卷290頁.北京,中華書局 . 2015
[3]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莊子集釋卷一上第5頁.北京,中華書局. 2013
B223.5
A
1671-864X(2016)08-0150-01
馮磊(1992-10-14-), 男,漢族,陜西西安人,西北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碩士研究生 專業: 倫理學,研究方向:陜北、關中民俗倫理道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