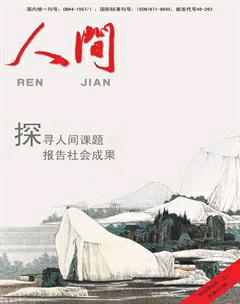本·奧克瑞《饑餓的路》審丑研究
張新
摘要:審丑創作將美與丑做出對比,同時又打破美丑界限。筆者從作品中人鬼混雜的世界著手,具體通過鬼孩兒阿扎羅和當地貧民的視角,對作品中描寫的生活污穢、骯臟、惡心以及人的暴力、丑陋進行揭示。同時筆者利用狂歡化所表現的非常規、非理性的特征來分析奧克瑞的審丑寫作,在分析的過程中,深入體味作者的人性關懷。
關鍵詞:審丑;狂歡化;人性關懷
中圖分類號:B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8-0015-02
本·奧克瑞1959年出生于非洲西部國家尼日利亞,是一位用英語寫作的尼日利亞作家。《饑餓的路》是他1991年的作品,他憑借此作品獲得英國最高獎項布克獎。作品利用民間傳說將現實世界和鬼魂世界結合起來,描寫了尼日利亞擺脫殖民主義統治的前夜,人民痛苦、無助、麻木的生活狀態。作者通過鬼孩兒阿扎羅和當地貧民的視角,進行審丑化的描寫。鬼孩兒阿扎羅為了生存而掙扎,親眼目睹了政客們的卑鄙無恥、丑惡貪婪,鄰居的麻木不仁、愚昧無知,打手的殘暴無情、兇神惡煞,草藥醫的神通廣大又視財如命……作品中大量的“丑惡”現象,讓讀者觸目驚心、難以忘懷。
一、《饑餓的路》中丑的表現
《饑餓的路》中對丑的描寫隨處可見又觸目驚心,筆者在分析奧克瑞審丑寫作的過程中,從環境之丑和人之丑兩個方面丑的表現來分析。
(一)環境之丑。
首先是政治環境之丑。正如葛浩文評價莫言:“這位小說家對官方歷史與記錄在案的‘事實不感興趣,而是慣于運用民間信仰、奇異的動物意象及不同的想象性敘事技巧,和歷史現實(國家和地方性的,官方和流行的)混為一體,創造出獨特的文學。”①這句評價用在奧克瑞身上,同樣適合。在《饑餓的路》中,奧克瑞以無拘無束、隨心所欲的虛幻手法,從“鬼孩兒”的視角來敘述尼日利亞政治的荒誕。在人鬼混雜的世界中,窮人黨和富人黨相互爭權奪利,黨爭背后是外國人的勢力。兩個黨派模仿西方的民主選舉制度,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將普通民眾作為他們政治征程的棋子。富人黨和窮人黨為了贏得黨派間的爭斗給貧民窟的人們種種許諾。但是他們的黨爭不僅沒有給普通民眾帶來所承諾的美好生活,反而給他們帶來無盡的苦難:噪音、毒奶粉、破爛的校舍、骯臟不堪的貧民窟……民眾在整個過程中都是麻木的,他們追求的是眼前的利益,不能配合政黨的要求,最終使得黨爭成為一場場荒唐的鬧劇。
其次是貧民窟之丑。作品對貧民窟的描寫很多,貧民窟最顯著的特征是破爛不堪。在集市上貨物到處堆放,散發出一陣陣令人作嘔的臭味。貧民把垃圾扔到路上,下雨的時候垃圾被沖到路邊的沼澤里。在高溫作用下,沼澤里冒著氣泡傳出一陣陣的臭味。雨天貧民窟的路是泥濘的,黑水在路面上泛濫。雨勢大的時候,臟水流進院子里,甚至流到屋子里,水上漂浮著死老鼠。屋子里的空間很小,“地板又糙又硬。一排排的螞蟻沿著墻縫爬行。櫥柜附近有好幾個蟻穴。一條蚯蚓拖著長長的身體從爸爸的鞋邊爬過。壁虎和蜥蜴順著墻壁上下躥行。在房間另一頭的晾衣繩上掛著太多的衣服,繩子因不堪重負而向下耷拉著。……”②阿扎羅學校也是殘破不堪。對貧民窟的描寫反映出當時貧民的生活狀態,講述了尼日利亞在擺脫殖民主義統治前夜的生活狀況。貧民生活環境越惡劣,生活場景越丑陋就越能反映殖民者給尼日利亞帶來的苦難。作者多次描寫貧民窟的現狀,作品中多次寫到黨爭,即窮人黨和富人黨為了拉選票而給群眾的許諾,這些許諾與現實環境形成對比,體現了他們的虛偽和欺騙性。從貧民肆意地將垃圾丟到大街上,可見人民甘愿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沒有一絲想要改變現狀的想法,只為眼前利益,茍延殘喘,這種狀態是長時間受到殖民統治失去自我而形成的一種麻木狀態。
(二)人之丑。
《饑餓的路》對人的描寫堪稱經典。奧克瑞不僅塑造了“我”、“我”的父親母親、寇朵大嬸、房東等一系列的人物形象,而且還塑造了一些外形恐怖可怕的人物,他們穿梭于人鬼世界,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產生強烈的沖擊感。在奧克瑞筆下,人的身體紛紛產生“異化”,從而由異化產生出恐怖的效果。
寇朵大嬸另一個身份是巫師,她知道阿扎羅是鬼孩兒,因此陰險地利用他來招攬“客人”。自從阿扎羅在她的酒鋪里出現,酒鋪里就相繼出現了許多奇怪的“東西”,他們有些是人有些是鬼。在作品中酒客的形象總是與“赤裸”、“寒酸”、“垃圾”“膿瘡”密不可分。這些人往往不是精神有問題就是身體畸形。還有一類人就是奧克瑞筆下的乞丐。那些乞丐有的腿是彎的,有的腳長在腦袋的后面,一只眼睛高一只眼睛低,瞳孔像是被擠爛的蛋黃。
在《饑餓的路》中,民眾的內心變得不再善良,他們在生活苦難的壓抑之下,愚昧不堪、麻木不仁。在利益面前,他們不顧親情友情,露出一張張丑惡的嘴臉。作品中多次提到,“我”的鄰居為了小利益,放棄自己的原則。當政客們的宣傳車開到貧民窟時,他們瘋狂的搶奪錢幣,不惜自己的臉面;他們搶奪奶粉,結果中毒,上吐下瀉。到后來宣傳車再次來的時候,他們竟然不再記得此事,不想報仇。“我”的父母親為了“我”平安歸來舉辦宴會,眾多鄰居、不來往的親戚、甚至陌生人紛紛前來,父親不得不向他們中的一些人賒東西來供給這么多人的吃喝,但是第二天昨晚的客人搖身一變成了可怕的債主,堵住家門逼迫可憐的父母還債……
作品中這樣的描述比比皆是,在作者的筆下,民眾不僅形丑陋,內心也變得畸形。通過對人性陰暗的描寫、對丑陋面的大書特書,毫無顧忌地從丑的角度揭露人性,不費吹灰之力地營造出一大堆令人毛骨悚然的場景,并隨心所欲、鎮定自若地將這些鏡頭冷靜地展示于讀者面前,演繹著別人無法書寫的奇異故事。
二、審丑的敘述視角
敘述視角是敘述過程中對故事內容進行觀察和講述的角度。同樣的故事用不同的視角去進行表述就可能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人看來也可能會有不同的意義。《饑餓的路》主要從鬼孩兒阿扎羅和貧民的視角進行敘述,對丑惡現象描寫的非常深入。
(一)“鬼孩兒”視角。
在《饑餓的路》中,最主要的一個敘述視角就是“鬼孩兒”阿扎羅的視角。作者之所以選擇兒童作為敘述視角,一方面是鬼孩是全知全能的,能夠全面的掌握所發生的事件。另一個原因是“童言無忌”。“他用兒童的視角來透視這個真實的現實世界,看清存在于社會中不僅僅只有美,還有丑,不僅僅只有善,還有惡。”③大人往往受到道德、倫理、秩序的束縛,在表達觀點之前首先考慮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社會的規范。因此利用兒童視角來進行敘述是一個很好的方式,能夠使人的思維擺脫束縛,不受任何羈絆。他想通過兒童去洞察成人的世界,從而給人一種亦真亦假的震撼,達到一種心理上的誤差。
筆者前面提到,這部小說以約魯巴文化中關于“阿庫比”的傳說作為意象來敘事。這種亦真亦假的寫作,利用“童言童語”,成了作者進行審丑寫作的最好的武器。關于寫作的真實性作者不必向讀者做出任何的保證,可以大膽地充分表達自己的所見所思所感,而不必承擔任何責任。當小孩子面對丑陋的社會的時候,他必會產生一種受傷的心理,原來世界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般美好。以孩童的眼光看待成人的世界,也正是為了強烈刺激成人那早已麻木的神經。所以作者以鬼孩兒的眼光來看世界,表達他對世界的看法,對傳統的美好的事物進行批判,這種極端的審丑便開始了。
(二)貧民視角。
作品的敘事中并不是以“鬼孩兒”單一的視角來進行的,中間穿插了貧民窟里貧民對于生活感受的表達。對勞苦大眾的貧窮、沒有政治立場、為了生存不擇手段的描寫是作者寫作的又一視角。民間文化和生活具有復雜多樣性,作者將寫作視角著眼于民間,描寫民間勞苦大眾的生活和苦難,一方面表達出殖民主義對當地居民的摧殘,另一方面表現出人的生命的本質。社會發展是有規律的,而所有民間生命個體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方式,都是在充滿必然性的同時,由一個個天災人禍等因素導致的。
“我”的父親是貧民中的一員,他用思想和行動表達對的丑惡的看法。父親是個身體強健的人,與“我”和“我”的母親一起生活在貧窮但很溫暖的小家庭中。但是生活的苦難一次次的襲來,做搬運工的父親身體漸漸被壓垮、脾氣越來越暴躁、我們的家庭也越來越貧困。面對政客們的相互傾軋,父親作為貧苦人的一份子,一開始選擇支持窮人黨,后來發現窮人黨與富人黨沒有本質的區別,于是打算自己做首相,領導窮人過上好日子。可悲的是在貧民窟里貧民并不關心政治,他們只關心自己能夠獲得多少利益。父親的政治夢想只能成為一場夢,雖然有幾個乞丐支持他。
貧民窟的其他成員一直抱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他們關心的是能夠獲得多少利益。他們每次聽到附近有宴會,就會恬不知恥的跑去蹭吃蹭喝。“我”家的兩次宴會、寇朵大嬸酒鋪門前的政治集會中,都有很多的鄰居和陌生的窮人前來,他們不管宴會的目的是慶祝還是為了政治宣傳,只要有吃的滿足他們饑餓的腸胃就可以了。
民間大眾所表現的這種狀態,是一種非自然的,后天所形成的狀態,是天災人禍共同作用的結果。作品中的貧民大部分麻木、沒有思想、沒有表達,這反而形成另外一種表達,是一種沉默和無知換來的對生活和生命狀態的深度的反思。生活的苦難是強大的堡壘,他們長期被困于其中,遭受苦難的摧殘、在長期殖民統治下沒有獨立思想,有現在的模樣不足為奇。
三、狂歡化的表達方式
審丑本身就表現出極大的狂歡化。將審丑運用到小說的創作中,是對小說創作的創新和開拓,也是對傳統壓抑生命文化的批判,是對腐朽的社會規則的顛覆。作者以極端的審丑書寫,肆無忌憚地打破壁壘森嚴的美丑界限,強烈沖擊了文壇傳統的審美規范,以極端的寫作方式證明自己在文壇上的存在價值。審丑寫作開闊了人們的審美視野,使審美方式由線型模式轉向縱深方向。《饑餓的路》的審丑寫作,給讀者帶來很強烈的震撼。
第一,反常規。作品采用當地民間傳說作為故事的核心,將人鬼生活穿插起來,從而對恐怖的人物和場景大量書寫,給人一種非真實感。聲音和顏色出現的頻率很高,而且利用通感的手法,將人體的器官調動起來。“頭發上粘著紅色的液體”、“無不狂熱的汗臭味”“白膜覆蓋的眼珠”“黃色的膿液”、貓頭鷹從樹上掉下來,變成黃色的水,蒸發到空氣中去了,長著三個腦袋的人,集市上倒立行走的人……這些非常規化的描寫產生了一種狂歡化的效果。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的小說時,提出其中所體現的所謂“怪誕現實主義”,即有關粗俗、猥褻、瘋狂、怪誕所表現的中世紀民間藝術的狂歡化特征。這些違反常規的民間文化和藝術中蘊藏著的魅力使得創作具有更強的生命力。
第二,非理性。“非理性是指一切有別于理性思維的精神因素(包括情感、直覺、下意識、幻覺、靈感)等。”④作品中很少寫安寧的生活,只有在少數幾個地方寫“我”的父母給我創造過這樣的生活環境,更多的時候是在寫人鬼混雜的場景、飲酒無度的混亂、打手欺負貧民的殘酷無節制……這些非理性的場景,通過感官和肉體的沸騰來達到一種狂歡化的效果。
奧克瑞的創作通過對丑惡事物的描寫,表現出殖民主義撤出非洲進而非洲獨立以后,產生的種種問題。不倫不類的新政治、獨裁暴力和貪污腐敗的社會毒瘤、饑餓控制下的貧苦大眾等。作家在創作中看到了那掩埋在深處的丑陋的一面,快意書寫人生百態,對社會的陰影進行揭露,對人們的丑行進行抨擊。在審丑寫作過程中作者犀利的諷刺現實,同時又表現出對人性深入的了解與關懷。小說不厭其煩地描寫污穢、骯臟、惡心的場景,讓讀者有種惡心驚悚的感受,并不是僅僅呈現丑陋這一表象,而是在告訴讀者這些丑大部分是真實的,是我們平時不愿意相信的東西,是對我們生活的一種反向呈現。在既有的生活狀況下,應該反思這種丑陋的生活與我們生活的關系,同時為改變丑陋付出行動。奧克瑞這部作品無疑是很成功的,但是作品在審丑寫作中存在一點瑕疵,即很多地方出現重復性的寫作,讓人讀起來有些疲倦。
注釋:
①陳旭東,有技巧的揭露——評莫言小說的審丑藝術[J].名作欣賞,2014(24)-73.
② [尼日利亞]奧克瑞.饑餓的路[M].王維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34..
③桓芳.莫言的“審丑”寫作[D].中南大學,2008-17.
④劉瑾.“理性-非理性”概念考[J].音樂探索,2003(1)-75.
參考文獻:
[1][尼日利亞]奧克瑞.饑餓的路[M].王維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8.
[2]巴赫金.詩學與訪談[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3]吳曉梅.論后殖民時期的文化身份認同——以本·奧克瑞的小說《饑餓的路》為例[J].長江大學學報(社科版),2015(8).
[4]吳曉梅、孫妮.難以擺脫的殖民心態——從后殖民主義批評視角解讀《饑餓的路》[J].長春大學學報,2014(11).
[5]吳強.本奧克利作品的“黑非洲”書寫——《以饑餓的路》《迷魂之歌》為主[D].西北民族大學,2013.5.
[6]劉瑾.“理性-非理性”概念考[J].音樂探索,2003(1)
[7]王洪岳.審美的悖反:先鋒文藝新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8]王洪岳.西方現代審丑思潮與中國先鋒小說丑學觀念[J].鄭州大學學報,2003,(2).
[9]桓芳.莫言的“審丑”寫作[D].中南大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