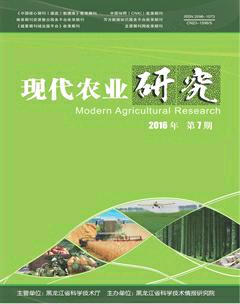農村土地征用問題及對策
于上
近十年來,各地土地出讓金在地方財政收中的比重不斷提升,2009年達到1.5萬億元,相當于同期全國土地財政總收入的46%。2010年全國土地財政收入2.9萬億元,土地市場火爆,高價地頻出,地價不斷被推高,大量的農村土地被地方政府征用,已逼近18億畝耕地的紅線,農村的土地出讓制度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1 農地被征用的現狀
中國近些年在現代化的建設過程中,耕地面積銳減,目前全國的耕地面積已減至18.26億畝。在過去的11年中,耕地減少1.25億畝,平均每年減少1000多萬畝。由于征地補償的標準普遍偏低,農民從征地中得到的利益較為微薄。土地增值的收益大部分被政府和開發商獲得。據估算,在近20年問,國家從農村那里獲得土地資產收益高達2萬億元以上。
在農地的征用過程中,征用土地的主體五花八門,有些屬于國家征用,有的則為地方政府征用,有些農地是由基層鄉鎮政府和村級組織征用,有些農地是由企業或開發商征用,有的土地則為農民內部自己占用。不同的征用者由于其法律地位以及與農民的關系不同,因而他們征地的利益追求也存在較大差別,從而造成征地后的補償標準不一致,導致失地農民的權益難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從現有的征地手段來看,征地的手段也是各種各樣,有通過先建后批的方式征用,有的是以租代征的方式來“迂回”征地,有的則是通過土地作價入股再通過股權轉讓的方式來征地。這些征地方式,規避了法律和土地管理制度,大大降低了征用的難度,而且,征地單位或個人在規避法律和政策規定的同時,實際上給被征地農民帶來了巨大的法律風險,使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法律保障。
2 農村土地制度存在的問題
農村土地制度本身不完善,存在的問題較多。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的歷史表明,農村集體土地是社會政治變革直接分配土地的結果,而非通過市場交易取得的土地所有權,后來的土地變動情況說明,通過政治運動獲得了土地產權,同樣也可以通過政治運動來改變土地產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多征用私人所有的土地,土地征用的基礎是私人所有的土地,土地的私人所有制約著土地征用行為。我國集體所有的土地產權界定不清晰,主體不明,農民集體所有權是一種受限制的產權,而國家是農村集體土地產權的實際控制者和潛在所有者,由此產生了征地過程中缺乏限制濫用征地權的硬性約束,頻繁發生侵權行為,農民在國家、集體的利益強勢下,始終是產權的弱者。農民對土地沒有處置權,使農民在征地過程中無權行使自己的權利,農民對土地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因而農民對于自己承包或使用的土地被征用提出完全補償的要求缺乏法律依據。
3 農村集體土地制度缺陷的原因分析
農村土地被大量占用的現象之所以較多地發生,其癥結就在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與新的經濟體制之間的背離。農村土地所有權主體——集體其實不再是獨立的利益主體,而是由個體和某些集團利益混合而成的所有權,而土地真正的受益主體——農民的地權在集體所有權結構中沒有充分體現和保護。所有權主體和利益的分離不可避免會引起土地資源在市場經濟中的重新配置而產生的增值,不是由土地的利益主體所獲得,而是被模糊的集體所有權主體和復雜的個人和集團所獲得。與此同時,由于所有權主體不是直接的利益主體,也就是說雖然農地是集體所有,但農地轉讓并不使集體利益受損,因為集體利益在新形勢下本身就是一種虛擬的利益,所以,代表集體行使土地所有權的個人和集團會愿意以較低的價格轉讓農村土地,從而導致多種多樣的建設和開發能夠輕易地以低廉的價格從農民手中獲取土地,而農民則難以從中討價還價,獲得合理的價格補償。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主體與土地使用權主體——農民之間權利集合的嚴重不對稱,造成了真正耕作土地的人對土地失去了必要的控制權。
土地的征收引發的農地產權和失地農民的權益保障問題,較長時間以來成為了各界關注的熱點論題,解決農地征用問題,不僅需要進一步的理論探索,觀念更新,更重要的是制度變更和政策供給。對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改革。并不等于實行土地私有。改革集體所有制的關鍵是如何使農村的土地產權更加明確、更加細化。而目前集體所有制的界定模糊,因此只有依賴法制,征地拆遷中的正義才會回歸到常識,只有法律有足夠的尊嚴,地方官員及地方政府才不會在征地拆遷中肆無忌憚,任意踐踏法律,侵害農民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