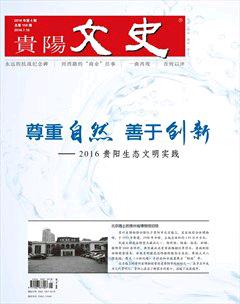徜徉在綿延的群山里
黃圓



在傳統中國文化中,自然總是會被賦予某種人文的精神,一塊山石、一抹芳草不再只是物理或是植物的屬性,一定會揉進人的情感,帶有幾許想象,沾染上心緒。
一直生活的土地上,放眼望去一定會看見山。很多時候,山具有一種力量,或許就是在最哀傷、最絕望的時候,讓生命可以安靜下來、飽滿起來的魅力。
黔地多山,重巒疊嶂,綿延縱橫,山高谷深。滄海歲月中的地質變遷,造就黔地各處不同風韻的山勢山型:北部有大婁山,自西向東北斜貫北境;中南部苗嶺橫亙;東北境有武陵山,由湘蜿蜒入黔;西部高聳烏蒙山,屬此山脈的赫章縣珠市鄉韭菜坪為貴州境內最高點。
山,是靜穆的,卻帶有豐富的聲響,有風聲,有鳥鳴,有許許多多的細微動靜,這份專屬于山的清音,有時候也是自己某一刻心底的微瀾。
徜徉在貴州的山間,傾聽山的清音,或許對于生命生活有更深切的質問。
小時候生活在盤縣的礦區,巍峨連綿的大山,似乎望不見山巔。每當夜色四溢的時候,遠遠的山影映襯得夜空越發遼遠。
那個時候對山是敬畏的,因為山里還有野獸出沒,大人們一再告誡小孩,一定不能夠瘋玩到山里。對山也有期待,每逢趕場天,山里的老鄉會帶來很多新鮮的玩意,櫻桃、楊梅、獼猴桃,山里藏著很多美味。
每一年和母親都會翻山越嶺在路上顛簸一兩天,翻過一座又一座的山,風塵仆仆到貴陽的外婆家。一直記得,汽車在公路上揚起灰塵的同時,曾經高不可攀的山漸漸縮小被丟在身后,當山勢漸漸平緩,路途不再險峻,貴陽也就近了。
烏蒙山的險峻對于幼時的我不是那么深刻,直到大學里的一位朋友來自那里。每每聽到他說起回家的路途,尤其是冬季里的奔波艱險,才知道自己曾經有過的經歷,實際上不是記憶中那般僅僅是辛苦。
依然記得,有一年冬季那條路上就出了惡性事故,和朋友說起,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寒假回家,車子在山路上蜿蜒,很多次感覺車子會在結冰的路面上沿著彎道飛出去,如果真的那樣,那就是真的到了世界盡頭。他說的時候帶著微笑,而我卻聽出了別樣的滋味:再險峻的山,也隔絕不了游子與家之間的深深羈絆。
再到烏蒙山一帶,從貴陽出發只要三四個小時,幼時那可是兩天一夜的路途,朋友曾經也要花差不多一天的時間在路上。交通的改變,縮短空間的距離,可是,山還是山,依舊靜默地看著人世的變遷。歸家路上的群山,是從異鄉到故鄉的標識:青山作伴好還鄉!在一些時候,連綿的群山不是阻礙,是用來將鄉愁調制得更加濃烈的念想。
再一次身處烏蒙山區,走過湖泊、草場、溪谷、山地,沒有記憶里對于高山的忐忑與新鮮,望著藍天白云下的重重群山,忽然想到有人說“去到某個地方,總有隱隱的理由。”或許走過一座一座的山,不過就是為了在這個年紀、在這個時間點去邂逅一份遼闊,去感知曾經留在記憶里的片段,重溫過去的某些小小時刻。對山的觀照帶來心境上的變化,是不是在刻錄著自己生命的軌跡?處于遼闊當中,是該悲壯還是驕傲?是該啜泣當初年幼不知母親這一路的心緒,還是該慶幸朋友沒有真的見識“世界的盡頭”?無窮山色,無邊往事,冷清清。
有人說,山是有靈魂的。貴州的山,是看不厭的,每一處的山各有妙處。
有一年初冬去梵凈山,上山的石階鋪滿了落葉,走上去悉悉索索的,山間有云霧繚繞,望不見太遠的山景,只能夠一步一步埋著頭向上而去。偶爾山林間飛鳥掠過發出聲響,讓人停下腳步傾聽,這初冬的山里并不蕭索寂寥,在幽靜和深邃中蘊藉著某種能夠讓人飽滿起來的力量。自古佛教與名山相連,的確,在山間自然而然就會有一種與空寂精神相契合的自由,會想到“坐看云起”,會想到“鳥鳴山更幽”。許許多多蘊涵佛理的詩句,仿佛一直藏在梵凈山里,只是等著在這一刻滿溢心間。
上到梵凈山的金頂,來時經過的山都在眼底。山風呼呼地掠過,將山巔的云不斷聚合離散,每一秒看到的山景都不一樣,面對這樣的山,竟會有一種既渺小又遼遠的復雜情感。人在天地間真的會小到仿佛微塵,但是又可以從山的溝壑起伏中汲取精神上的豐富、情懷上的遼遠。生命雖然會卑微的幻滅,但是一定會有發著光的某一瞬吧?
黔東南的山給人的感覺是處處生機,那樣雋秀的山勢連綿不絕,林木繁茂,散落山間的苗鄉侗寨本身就是生命韌性的最好詮釋。每當木樓屋頂山升起炊煙,與山間的霧靄一起縈繞,無論晨昏還是明晦,山色山形都仿佛在述說著蓬勃無盡的靈感氣韻。最喜歡在夜色中穿行于黔東南的山里,當暮色漸起時,崇山峻嶺慢慢成為剪影,林木影影綽綽,這個時候,山高,林寂風涼,月明星淡。
在這片山里,所有的蒼涼與傷痛都會被漸漸撫平。山地靜好,醇厚淡遠,不徐不疾的生命,尋常樸素的生活,一切剛剛好。
凡物皆有可觀,茍有可觀,皆有可樂。親昵自然,含著人性的細致是東方傳統的情緒。或許在有的時候,人就是通過對山的種種想象來實現自我、尋找自我。徜徉在綿延的群山里,不論是在山腳時的施施然而行,還是在蜿蜒山路上的跋涉,萬里峰巒,山就在那里,只要親近,不僅是一份“原來你也在這里”的相遇,也是一起寂靜一起歡喜的彼此守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