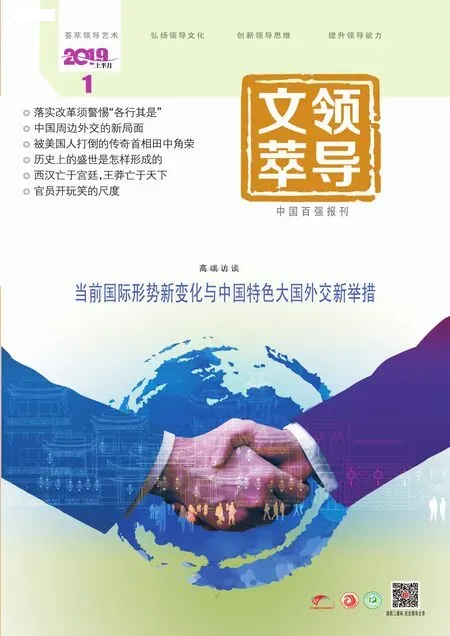美國對華的思維困境和中美關系“新常態”
王建偉
進入2015年以來,中美在南海、網絡安全等問題上沖突加劇,兩國關系似乎又迎來一個緊張動蕩期。有美國學者認為,中美關系已經到達一個“臨界點”。
在“臨界點”背后
美國這場新的對華戰略大辯論有著國內和國際的雙重背景。從國內來看,美國即將步入大選年,兩黨有意角逐總統大位的候選人都開始浮出臺面、進入角色,例如民主黨的希拉里·克林頓和共和黨的杰布·布什,都已經宣布參選。從以往的經驗來看,美國無論是保守還是自由的或是標榜無黨派的影響力比較大的智庫以及相關學者都會開始就各種內政外交問題發表言論和看法,試圖影響未來候選人和政府的政策走向,也不排除一些有政治抱負的學者想提出一些不同凡響的政見以引起兩黨主要候選人的注意,以作為晉升之階。
從國際的大環境來看,奧巴馬的外交政策總體而言乏善可陳,在其國內不斷遭到詬病。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外交在全球范圍內空前活躍,并屢有斬獲,對美國形成一定的壓力。
應當承認,習近平執政之后的中國外交在理念和實踐上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尤其在亞洲,中國外交可謂“三箭齊發”勢頭強勁。政治上,習近平前年在亞信會議上提出“亞洲安全觀”,強調亞洲的事情要靠亞洲人民來辦,亞洲的問題要靠亞洲人民來處理,亞洲的安全要靠亞洲人來維護。這被美國不少人解讀為中國版的“門羅主義”。經濟上,中國倡議發起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去年以來勢如破竹,西方國家(除了日本之外)沖破美國的阻撓,紛至沓來,跌破所有分析家的眼鏡。到頭來,美國反而成了孤家寡人。安全上,中國在南海諸島上加快了填海造陸的力度和速度,有效地改善了在該地區的力量均衡。所有這些,使美國朝野某些人產生了嚴重的挫敗感,產生了要求華盛頓改弦更張,以扭轉不利局面的強烈沖動。
陳舊的新戰略
于是,美國一些戰略家和分析家得出結論——美國需要一個新的對華戰略,以改善美國的對華態勢,并紛紛為此建言獻策。在已經出爐的政策報告中比較系統論述美國對華新戰略并引起廣泛關注的,當推外交關系委員會去年3月發表的那份特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告”的標題立場鮮明地提出要修正美國的對華大戰略,作者認為,中國最近的行為證明美國過去幾屆政府以對華接觸、融合和合作為主的對華戰略失敗了。中國沒有成為美國所希望的“利益攸關者”,而變成了美國的“戰略競爭者”。因此,美國對華新戰略的重點要從合作轉向競爭,美國不能再繼續幫助中國崛起,而是要更多的“平衡”( balance)中國的崛起。
總之,雖然美國的戰略家們希望提出一個新的更有效的對華戰略,但實際上他們的思維卻很難擺脫過去的窠臼。從美國主觀上說,這是由它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文化所決定的。對外關系委員會報告的作者直言不諱地承認,從美國立國開始,它的大戰略就是要謀求和保持對其他大國的力量優勢,先是在北美大陸,然后是在西半球,最后是在全球范圍內。而在冷戰結束不久,小布什政府就明確提出了后冷戰時期“美國第一”的大戰略,也就是要防止出現一個在全球范圍內與美國處于同一數量級的戰略競爭者。換言之,建立乃至維持美國在全球和地區范圍內的霸權是美國恒久不變的戰略目標。
更有甚者,美國還喜歡以己度人,認為中國也和美國一樣,要謀求地區乃至全球的霸權地位。這種戰略思維的邏輯就決定了美國不會愿意看到和接受中國的全面崛起。將這種戰略思維變成對華政策,中美之間的戰略沖突確實不可避免。所以,美國某些人士雖然到目前為止還不愿意公開使用“遏制”這兩個字,但是他們提出的所謂新戰略無非就是冷戰時期對付蘇聯那一套做法而已。
中美關系“新常態”
這次對話之前的劍拔弩張和對話之后的和風細雨形成鮮明對照,表明中美關系進入了“新常態”。這種“新常態”至少呈現出以下特點:一是中美在全球范圍內依然合作大于競爭,而在地區層面則出現競爭大于合作的趨勢。
二是在兩國關系中的一些傳統安全問題如臺灣問題上,雖然雙方仍存在矛盾,也不排除在特定條件下再次激化的可能,但是總體還處于緩和可控狀態。
三是總體中美關系和具體中美關系之間的相對獨立性在加強。雙方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可以針鋒相對、互不妥協,但都注意不讓具體問題上的分歧影響中美關系的大局。
可以預見,在美國既不愿意完全接受中國的崛起,但也不愿意承擔與中國全面對抗風險的戰略思維的支配下,中美關系競爭與合作交錯共存的“新常態”將會長期存在。擺在中美兩國領導人面前的挑戰,是如何不讓局部的競爭變成全面的競爭,不讓“健康”和“負責任”的競爭變成惡性的和零和的競爭,不讓競爭變成對抗。這需要雙方都表現出新的戰略思維,而不是在歷史的胡同里徘徊,不是沒完沒了地去討論對方是敵是友,討論如何壓倒對方,不是以己度人,而是顧己及人。
(摘自《思想理論動態參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