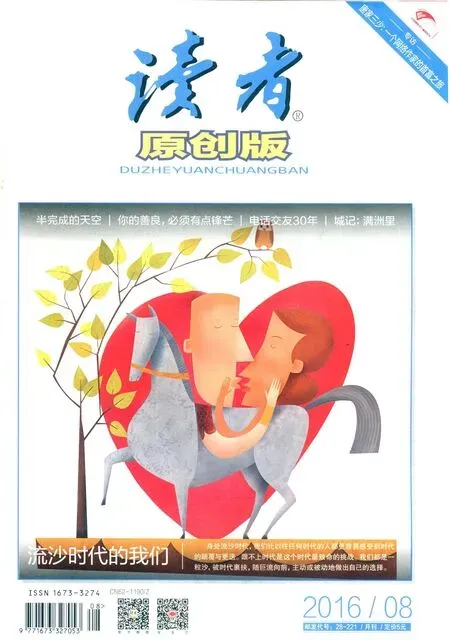電話交友30年
文_hayashi
電話交友30年
文_hayashi

在2016年4月舉辦的北京國際電影節上,我一共觀看了6部電影,最先看的一部是森田芳光導演的《春天情書》(1996年),最后看的一部是蔡明亮導演的《青少年哪吒》(1992年)。巧合的是,兩部電影講的都是陌生人之間的交往,而且都有意無意地把重點指向了通信工具。
《春天情書》描述了一段互聯網初興時期的愛情故事,這也可以看作是陌生人之間以相同興趣為基礎進行社交的肇始,因為男女主人公一開始是在一個電影主題的線上聊天室認識的。1995年,Windows95系統的登場使得互聯網在日本急速普及,森田芳光一年后拍攝的這部電影,既是自己的美好愿望,說不定也是對微軟公司的一通表白。
因為在這之前,陌生人之間的社交雖不乏興趣成分,但恐怕“性趣社交”還是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這其中的代表,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是“愛人銀行”,顧名思義,即以鈔票換取愛人的中介機構;隨后,“愛人銀行”漸漸演變成賣淫組織,于1984年被日本政府取締;緊接著到了1985年,“電話俱樂部”接過接力棒,并一直存續到了今天。
實體“電話俱樂部”的內部裝修很像現在日本的漫畫吃茶店,內部分成一個個的隔間,每個隔間配備一部電話。男士直接到店,支付隔間的使用費,在房間里等待女士來電。女士則利用自家的電話或公用電話撥打“電話俱樂部”的專線,等待被接入。女士往往是從街頭免費派發的雜志或者紙巾中獲取“電話俱樂部”的信息的。整個過程中,女士僅需支付電話費,無須另外付錢給“電話俱樂部”。當“電話俱樂部”流傳到臺灣時,這種模式有了一種更加朗朗上口的說法:男來店,女來電。頗為巧妙,更何況“來電”在漢語中還有雙關含義。

《春天情書》海報
在“電話俱樂部”里,男士接聽電話的規則有兩種,一種是搶接型,即電話鈴聲響起時,誰先拿起聽筒,誰就能得到和女士說話的權利。所以分散在各個隔間里的男士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像搶答競賽一樣去應對每一通電話。其實接進來的電話并沒有好壞之分,“電話俱樂部”既不會也無法預先把打電話進來的女孩分成三六九等。所以搶接的理由,除了迷信“運氣是自己爭取來的”這一點外,主要還是因為“電話俱樂部”并不是按接聽了多少通電話來收費,而是按在隔間里待了多久來計算。后來,有一些手慢的男士實在受不了這樣高強度的競爭,第二種輪流接入型“電話俱樂部”的數量才多了起來。
“電話俱樂部”的創舉,在于實現了社交雙方直接卻仍保有距離的接觸,而且給予了雙方幾乎同等的選擇權。從技術層面上講,支付了使用費的男士擁有的權利似乎更大,在遇到聊不來的女士時,男士可以選擇回撥到前臺,中止通話。可即使男士覺得聊得來,想跟女士進一步接觸,也無法自己決定,而是必須取得女士的許可。
但正是這樣的創舉,使得“電話俱樂部”和當時日本社會的“少女援助交際(未成年人以身體換取金錢,簡稱‘援交’)風潮”像套餐一樣捆綁在了一起。由于“電話俱樂部”不收取女士的費用,交際又建立在你情我愿的基礎上,抱有援交愿望的女高中生大都對“電話俱樂部”相當青睞,其中不乏山長水遠地從各地匯集到“電話俱樂部”產業發達的東京參與援交的少女。有些讓人哭笑不得的是,相當一部分少女一開始其實是抱著惡作劇的心態撥通“電話俱樂部”的專線的,聊著聊著,受到金錢的引誘,才打開了援交之門。
借助民營化的日本電信電話株式會社的新技術,一部分“電話俱樂部”得以實現從線下向線上的轉換,這里的“線”指的是電話線。有賴于這條線路,男士也不必到實體店鋪去了,規則從“男來店,女來電”變成了“男匯現,女來電”。社交的私密性進一步得到保證,同樣的,援交和性交易的聲勢也被掩蓋了。
性交易是以身體換取金錢,這在大多數國家都是違法的;援助交際在大多數國家也是違法的。但是兩個自由的成年人能不能約會呢?日本法律給出的答案是:可以。所以,2002年《日本風俗營業法》改訂時,增加了眾多對于“電話俱樂部”的規定,比如接待的客人無論男女都應在18歲以上,午夜零點到日出期間不得營業。只是這些規定未免來得太晚了點兒,因為“電話俱樂部”其時早已衰落。
不可否認,“電話俱樂部”成就過沒有性意味、沒有肉體關系的友誼,但那畢竟是少數。它從30年前誕生起就帶著濃濃的性暗示,現在的“電話俱樂部”里還提供內容與性相關的雜志,供男士在等電話的間隙消磨時間。
網絡時代全面到來之后,約見類網站取代了“電話俱樂部”。性交易的問題自然還在,并且隨著約見手段的增多和隱蔽性的增強,發現和查處的難度越來越大,但是兩個自由的成年人,仍舊享有自由約見的權利。
工具不該被譴責,因為它本身并無思考的能力。正如因為有大批少女通過“電話俱樂部”進行援交,就完全禁絕“電話俱樂部”,并不是值得贊許的方法,或許也解決不了援交這一社會問題。

《青少年哪吒》海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