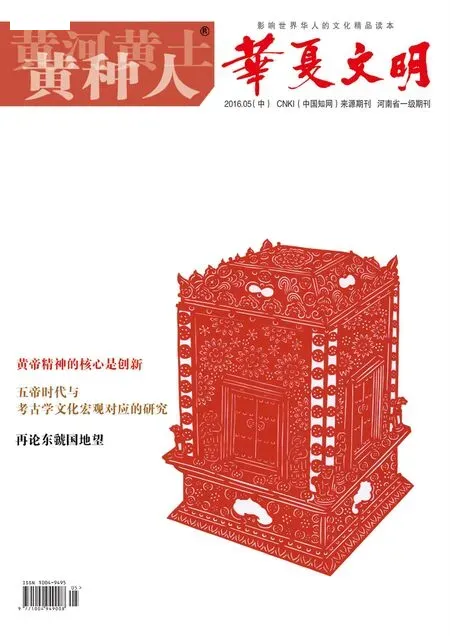伊拉克南部古遺址考察見聞
□劉拓
伊拉克南部古遺址考察見聞
□劉拓
伊拉克所在的兩河流域,是世界文明最早的起源地之一。不同于埃及和中國文明相對而言的封閉性,這里自古以來就是各方勢力逐鹿的中央地帶,人群如走馬燈一樣更換,留下了數量和種類都讓世界其他地區嘆為觀止的歷史遺跡。2014年下半年,“伊斯蘭國”組織在伊拉克西北部興起,迅速占領了尼尼微省和安巴爾省的大部分地區及薩拉赫丁省的北部,并于2015年2月開始,有計劃地摧毀新亞述時期的尼姆魯德 (Nimrud)、豪爾薩巴德(Khorsabad)以及安息時期的哈特拉(Hatra)古城,大肆破壞當地博物館和伊斯蘭教、基督教文物及古建筑,種種暴行發生在這樣歷史厚重的土地上,讓人深感痛心。2015年3月,作為對恐怖組織行為的抗議,關閉12年之久的伊拉克國家博物館重新開張。借此契機,筆者在2015年7月,走訪了伊拉克南部政府控制區的重要遺址、古建筑和博物館。受篇幅所限,略去古建筑和博物館的部分,在這里簡單介紹一下當地大遺址保護工作的現狀和展望。
在自然地理上,以如今的巴格達(Baghdad)和薩邁拉(Samarra)一線為界,伊拉克兩河流域大體分為北部亞述(Assur)和南部巴比倫(Babylon)兩個部分,南部地形極為平坦,而北部河流比降稍大,至摩蘇爾(Mosul)以北進入山地,自然地理的差異也造就了巴比倫和亞述地區在建筑外觀上的一些不同。巴比倫地區以兩河時期的宗教圣城尼普爾(Nippur)為界,又可分為兩個部分:南部是蘇美爾人最初的活動區域,也是兩河文明最早的誕生地;北部是阿卡德人興起之處,在蘇美爾人退出歷史舞臺后,又成為巴比倫系列文明的中心。本次的考察最北只到薩邁拉,沒有涉及北部亞述地區。
伊拉克紛繁復雜的古代歷史,簡單說來以公元前539年居魯士大帝滅亡新巴比倫、公元637年阿拉伯人攻破薩珊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公元1258年蒙古人滅亡阿拔斯王朝幾個重大事件為界,可以分成四個階段。居魯士之前是獨立發展的兩河文明時期,遺留下眾多的古代城址,本次考察涉及了烏魯克(Uluk)、烏爾(Ur)、基什(Kish)、尼普爾、巴比倫、波爾西帕(Borsippa)六個重要的遺址。居魯士之后,兩河流域成為東方波斯帝國的附庸,從此失去了獨立文明的地位,但在亞歷山大東征之后的塞琉古、安息、薩珊波斯王朝,各個帝國的首都依然建立于此,筆者考察了著名的泰西封遺址。阿拉伯人到來之后,庫法成為半島外第一個首都,雖然倭馬亞王朝遷都大馬士革的時間很短,但其后的阿拔斯王朝則回遷到這里建立新都,薩邁拉遺址和巴格達城中遺留的阿拔斯時期建筑,是伊斯蘭教早期不可多得的瑰寶。蒙古人的入侵,讓兩河流域失去了持續4000多年的區域中心地位,然而這里依然是什葉派穆斯林的圣地,分布在巴格達、卡爾巴拉、納杰夫、薩邁拉的四座伊瑪目圣墓,在建筑上也頗為可觀。
首先說一下筆者看到的幾個兩河文明時期大遺址的現狀。以南部居中的尼普爾遺址為例,它位于迪瓦尼耶(Diwaniyah)城東約50公里的荒漠中,由于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改道,當年的城市現在已經離河很遠,完全不適合人類居住。兩河地區的地勢極為平坦,天地交界通常是一條直線,因而十幾公里外就能看見遺址,那其實只有20多米高的土丘——這是兩河諸遺址在視覺上給人的第一印象。
尼普爾面積很大,沒有圍墻,在進入遺址的公路上有門房,里面有文物管理員和數個駐軍。說明來意,待他們請示上級后,即可免費入內。遺址內部土丘連綿,高低起伏,很難辨別出建筑的具體格局;土丘表面的堆積物極為松軟,一平方米內大約有上百個陶片,密度十分驚人——兩河諸遺址在發掘之前,主要呈現這種不同時期巨厚、松散、堆積物埋沒的狀態。尼普爾是兩河宗教最重要的大神恩利勒的駐地,城中最顯眼的建筑就是一座20多米高的塔廟,塔廟頂端有一座美國人在19世紀末發掘時建造的泥磚房屋。因為泥磚建筑并不耐久,常常需要重建和修繕;而兩河城市受文化習慣的影響,一般不輕易搬遷,在不斷重建中,城市的基礎會不斷加高,諸如塔廟等高聳的建筑,也會內老外新套上一層層的外皮——尼普爾在整個兩河時期,奉祀未曾中斷,很好地體現了這一疊壓的特色。主塔廟建設于蘇美爾早王朝時期,但目前遺存的外觀尤其是塔廟南側遺留的一段非常完整的泥磚墻體,是新巴比倫最后一次修繕的結果,相隔2000年之久;發掘者通過一層層的解剖,可以揭露出建筑在不同時期的平面造型和改建過程。現在站在塔廟頂部向下看去,一些陡立的墻體便是當年發掘出的不同時期的建筑遺跡。
此行看到的年代最早的建筑遺跡在塞馬沃(Samawah)城南部的烏魯克遺址。可能因為當地政府的重視,這里保護措施極為嚴密。雖然面積廣大,但是四周由新建的鐵質圍墻完全圍住;遺址不售賣門票,需要到幾十公里外的塞馬沃文物管理處審查來意后才可購買門票,每人20美元,進入遺址后,有專人陪同講解。兩河流域的城址雖然多如繁星,但以文字出現為標志的文明誕生,卻是在烏魯克。這里在大約7000年前的新石器時期已經形成前文明階段的城市,至5500年到5300年前的層位,出土了最早的蘇美爾古樸文字。當時的建筑遺跡仍可以在烏魯克遺址的伊南娜(Inanna)圣區和白神廟(White Temple)看到:前者地表除了一些夯土墻體的殘存外,隨處可見散落的長陶釘——原先是著名的馬賽克墻體裝飾;后者還可以看到一個回字形的建筑基礎。這些建筑在蘇美爾早王朝時期顯然得到了重新修繕,可以見到不少印有蘇美爾語銘文的方形磚塊。
遺址中最為顯眼的塔廟,修建于距今約3500年古巴比倫滅亡后的加喜特(Kassite)王朝。塔廟磚體風化嚴重,但鋪墊在其中的草席,保存還非常完好。這以后,烏魯克的又一個大規模建設時期就到了亞歷山大東征后形成的塞琉古王朝,一座裝飾藍色琉璃磚的巨大建筑,和一個有典型希臘柱式的小型宮殿,顯示了完全不同于古典兩河時期的風格,擴大了烏魯克遺址的內涵。
說到烏魯克,不能不提到基什,因為烏魯克王吉爾伽美什 (Gilgamish)與基什王阿旮(Aga)那場史詩般的爭霸。基什位于尼普爾的北側,在巴比倫城的東部十余公里,處于無人看管的狀態。從地表可見的情況看,其內涵遠遠遜于烏魯克,不僅面積很小,而且只能看到一座低矮的重修于新巴比倫時期的神廟。與之類似的無人看管遺址還有巴比倫的附屬小城波爾西帕,這是水星神那布(Nabu)的駐地,目前遺存一座非常壯觀的塔廟。塔廟面積不大,但異常高聳,在已經坍圮成土丘狀的磚堆基礎上,聳立著一面十多米高的相對完整的磚質墻體;周圍顯然經過火燒,散落著數個燒黑的巨大磚質結塊。這座塔廟的核心可以追溯到早王朝,但目前見到的磚質外殼應該還是新巴比倫重修的。因為沒有受到任何保護,單薄高聳的磚墻似乎岌岌可危。
蘇美爾時期保存最為完好的城市遺址,當屬納西里耶城北約5公里的烏爾遺址。這里的管理方式與尼普爾相似,沒有圍墻,有門房守衛,登記后免費參觀。烏爾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由英國著名考古學家伍雷(Woolley)主持發掘,不僅發現了舉世震驚的烏爾王陵,也揭示了大量不同時期的古建筑,經過伊拉克政府后來的修復和保護,極大提升了這一遺址的觀賞性。烏爾城在新石器時代即存在聚落,在早王朝時期已經非常富庶,而至烏爾第三王朝達到極盛。城中最為壯觀的塔廟,坐西朝東,奉祀月神南納(Nanna),目前仍保留了20余米高的基座,雖然在新巴比倫時期重修,但主體架構還保存了4000多年前烏爾第三王朝的風貌。20世紀六七十年代,伊拉克政府對這座塔廟的外部進行了包磚保護,目前僅有下部三分之一是原始墻體,方磚之間用瀝青黏結。塔廟東南有一小的圍院建筑,稱為埃農馬赫(E-Nun-Makh),其東面有一窄高的磚拱,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磚拱實物。塔廟南側有一組保存較為模糊的建筑,稱吉巴烏(Gi-par-u),是地面附屬祭廟。而吉巴烏的東南側有一組基礎保存完好、內部結構十分復雜的方形宮殿建筑,是烏爾第三王朝開創者父子烏爾納姆(Ur-Namma)和舒爾吉(Shulgi)的寢宮,受到一定程度的挽救維修。
寢宮南部有一大片未回填的墓穴,地下部分均為磚塊壘砌,其上似有夯土建筑。靠西為早王朝時期的國王墓地,靠東埋葬著烏爾第三王朝諸王。墓地也有受到維修的跡象,但整體仍較為破敗。這一區域謝絕游客進入,不知墓室內部的詳細情況。墓地再向南,是連綿的未經發掘的土丘和數不清的陶片,一些磚墻的基礎隱約露于地表,是當時的平民住宅區。這一區域根據發掘實況,復建了一大片泥磚住宅,當地人認為是先知亞伯拉罕(易卜拉欣)的居所。
最后要談的兩河文明遺址,是著名的巴比倫城。巴比倫位于希拉(Hillah)城北5公里處,橫跨幼發拉底河兩岸,內城東西寬約2.4公里,南北長約1.6公里,大致呈長方形;目前地面可見的遺跡,主要局限在內城的河東部分。德國著名考古學家科爾德威(Koldewey)領導的隊伍從1899年開始,進行了將近20年的發掘工作,僅僅揭示了古城的很小一部分,最重要的就是在河東北墻附近的南宮、北宮及伊什塔爾門等遺址。除此之外,在南宮東側可以見到復建得面目全非的希臘化時期劇場遺址,而城神馬爾杜克 (Marduk)曾經被認為是巴別塔的巨大塔廟,在南宮南側約1公里處,僅僅留存了一個方形土丘狀的遺跡。巴比倫的歷史雖然極為悠久,但目前所能看到的遺跡,全為新巴比倫時期最后一次重建時所造的。
遺址收取20美元的門票,有專人引導參觀,進入后最為顯眼的是薩達姆時期復建的南宮遺址。重修巴比倫雖然是一項為了彰顯民族凝聚力、發展旅游業所進行的花費巨大的工程,但是毫無疑問對遺址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壞——高達十余米的新建墻體直接壓在2600多年前的舊磚上,造成了一些磚體的破裂;很多地方新建的部分不能和舊有部分進行有效區分,整個區域毫無古意。與之相反,隔城墻相望的北宮遺址,保留了發掘時的原貌——大量歪斜的磚墻聳立在土丘中,站在高處,依稀可以看到宮殿破敗的格局,但這種過分的放任,也在導致遺址遭受年復一年的風化。在南宮和北宮之間,巴比倫的雙層城墻雖已坍圮,也還有兩人來高,順著城墻向東走,就是著名的伊什塔爾(Ishtar)門。
伊什塔爾門是兩河南部文明在原址遺留下的最為壯觀、細節最豐富的建筑。兩堵十多米高的磚質墻體夾出一條10米左右寬的門道,進深30多米,行走其間,給人巨大的壓迫感。磚墻上裝飾有橫列四排神獸的浮雕,角龍與公牛型動物交替出現。這一建筑最著名的部分,原本續接在磚墻之上,是一座以藍色為底色的釉磚彩色大門,已經遷移到柏林的博物館中展出。現在的原址遺存可能在釉磚門建造時就埋入地下,成為新建筑的基礎。從現場情況來看,這座大門的修繕工作做得相對較好,磚墻后的新建墻體加固了搖搖欲墜的外皮,同時也沒有影響到其古樸的風貌。從大門向北走,還可以看到著名的巡游大道——這座大道上鋪滿了瀝青,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柏油馬路。
至此,筆者造訪過的六個兩河時期遺址已經介紹完畢,因為當地局勢較為復雜,時間也比較緊張,諸如埃里都 (Eridu)、拉伽什(Lagash)、吉爾蘇(Girsu)、拉爾薩(Larsa)等極為重要的遺址都未能現場考察,在時代序列上還有缺環,有待別人的資料進行彌補。
新巴比倫滅亡之后,兩河流域進入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政治中心遠離伊拉克。至亞歷山大東征,塞琉古王朝定都底格里斯河西的塞琉西亞(Seleucias);帕提亞安息后期,在塞琉西亞對岸建都泰西封,并一直沿用至薩珊波斯滅亡。筆者現場考察了泰西封遺址。
泰西封位于巴格達東南約50公里的馬爾丹(Madain)城南,由于沒有經過考古發掘,城市的格局不甚清楚,地表遺留的只有一座建立于薩珊晚期的巨大宮殿大門 (大門東側約700米是阿拉伯人攻破泰西封后建造的宮殿,不過是現代復建)。馬爾丹位于伊拉克遜尼派聚居區南部邊緣,與什葉派地區接壤,安全形勢在巴格達以南的諸遺址中最為緊張。宮殿被高墻完全圍住,一般人不允許進入參觀,即使參觀也不能拍照,我通過多道手續,才獲得拍照的權利。
宮殿的主體部分是一個坐西朝東的巨大磚拱,高34米,跨度達25米,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磚質拱券。拱券北部是一面30多米高的具有濃郁薩珊風格裝飾的墻體,四五排形式各異的拱門組成了樸素而又變化多端的立面。老照片反映了上世紀初以來,這個建筑不斷坍塌的狀況,拱券南側的磚墻,拱券東半部都已經不復存在。現場所見,磚拱的厚度大約只有一米,和巨大的體量相比,堪稱薄如蟬翼,在局勢如此動蕩的地區,隨時存在危險。2014年,拱券曾進行過一次大修,希望它能挺立到伊拉克局勢平靜的一天。

巴比倫伊什塔爾門
最后介紹的,就是此行到達的唯一一處世界文化遺產,位于巴格達以北約100公里的薩邁拉遺址。公元836年,巴格達哈里發受突厥衛隊的脅迫,北遷薩邁拉,在這里建立了一座比巴格達更為巨大的都城,但在50多年后,再次遷回巴格達,因此,薩邁拉完整保存了一座中古時期帝國都城型城市瞬時性的規劃,有著難以替代的價值。2014年下半年,“伊斯蘭國”軍隊一度兵臨薩邁拉城下,給古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壞,目前恐怖勢力雖已清除,但當地形勢依然較為緊張。
薩邁拉遺址的主體在底格里斯河東,現代的薩邁拉城北部,大約可分為南北兩個大城,順河南北延伸,綿延將近30公里,東西寬四五公里,極為遼闊;在現代薩邁拉城之南及底格里斯河西,還零星分布著七八處規模宏大的宮殿與園林——所有這些幾乎都是地表可見的遺存,即使在衛星圖上看,都不能不讓人驚嘆。時間所限,我只參觀了河東南城和北城的兩個螺旋宣禮塔,并沿路瀏覽了一些普通建筑基址。
站在現在薩邁拉城內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看見北方那座高達52米的Malwiya清真寺宣禮塔。這是薩邁拉乃至整個伊拉克最具標志性的建筑。宣禮塔南側有一座長240米、寬158米的巨大清真寺,目前僅僅遺存外墻。這里目前受到了良好的保護,塔下可以看到世界遺產標志,有軍隊在西側入口處看守,不收取門票;塔和清真寺的墻體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繕,少量游客亦在宣禮塔上和清真寺內部游玩。
乘坐出租車沿公路向北行20公里,就到了北城北部的另一座帶有螺旋宣禮塔的清真寺,名為Abu Dulaf,它的格局與Malwiya相同,但面積和高度幾乎小了一半。從老照片上可以看出,舊時的宣禮塔幾乎攔腰折斷,現在已經補修完整,但清真寺還保持著殘垣斷壁的外觀。這一區域幾乎完全處于戈壁之中,沒有任何保護措施。
同樣沒有任何保護的還有兩個清真寺之間20公里幾乎連續不斷的房屋基址。汽車在筆直的公路上前行,底格里斯河的沖積平原依舊如鏡面一般平坦,無數道高不到一米的墻體,密密麻麻排列在廣袤的戈壁上,找一高處俯瞰,幾乎可以識別出每一戶家庭的房屋格局:這可能是我見過的最為壯觀的土遺址群,它們慢慢風化、坍圮的現狀讓人非常痛心。

泰西封遺址
至此,我介紹了去年7月在伊拉克南部考察的幾個大遺址。總的說來,在目前動蕩的局勢下,伊拉克的遺址保護狀況比我想象得樂觀,烏爾、基什等遺址,甚至仍在進行小規模的發掘工作。多數遺址或多或少有人看管,無人看管的遺址,目前也沒有非常明顯的盜掘現象。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泥磚建筑在世界其他地方分布較少,可能缺乏保護經驗,在伊拉克的很多遺址都出現了修舊如新甚至舊跡毀壞的現象。伊拉克考古始于1842年尼尼微省豪爾薩巴德的發掘,幾乎可以算是世界考古史的開篇,大規模的發掘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重大發現不可勝數。從現場情況來看,這些遺址的規模和內涵遠遠超出我的想象,早先的發掘,只揭露了大部分遺址的很小一部分。因為此,我們不能不期待著伊拉克迎來局勢平靜的一天,期待40多年來產生的新技術應用于這批取之不盡的寶藏,更好地勘測、發掘和保護它們,尤其是期待中國學者能在可能到來的兩河考古機遇中,占據自己的一席之地。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責任編輯 趙建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