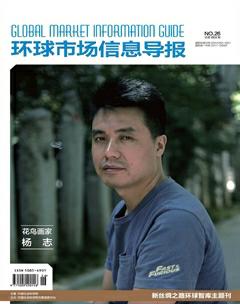袁芳:如修道士一般走在音樂(lè)的路上
袁芳:如修道士一般走在音樂(lè)的路上

那個(gè)被譽(yù)為“少數(shù)能彈出作曲家靈魂的青年鋼琴家”袁芳,在2016 年伊始,做了令業(yè)界稱贊與不解的兩件事兒,她在美國(guó)卡內(nèi)基音樂(lè)廳舉辦獨(dú)奏會(huì),異常成功,同時(shí),她也從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辭職,放棄了體制內(nèi)令人羨慕的教授身份。她說(shuō)“不懼不惑,在勇往向前的路上,我知道現(xiàn)在最該要什么,自由,還有沉淀。”在國(guó)家大劇院的一間音樂(lè)廳,袁芳站在臺(tái)上,一手撫摸著身旁的鋼琴,一手拿著話筒,分享自己對(duì)于貝多芬音樂(lè)的理解,那段時(shí)間她還在忙碌著和著名指揮家祖賓·梅塔的合作演出,但依然會(huì)抽出幾個(gè)周末的時(shí)間,進(jìn)行公益的講座分享,參加的人很多,活動(dòng)結(jié)束,很多人圍住袁芳,尋求指導(dǎo),他們中有不少甚至是從外地趕來(lái)的。

有幾位家長(zhǎng)拉住袁芳,希望她能聽孩子彈首曲子,袁芳大都應(yīng)允了,“你很棒,讓我來(lái)猜一猜你每天彈琴的時(shí)間,一個(gè)小時(shí),并且用了其中的20分鐘來(lái)練習(xí)哈農(nóng)。彈琴有一些枯燥嗎?你好像度過(guò)了這個(gè)階段,因?yàn)槟惆l(fā)現(xiàn),在練習(xí)之后,音樂(lè)給你回饋了很多的美,我覺得你已經(jīng)明白了,現(xiàn)在能天天堅(jiān)持練琴,以后也能堅(jiān)持做好任何事情。”這“自言自語(yǔ)”式的對(duì)話往往讓那些小家伙深深點(diǎn)頭認(rèn)同。
這是我之前見到袁芳的一個(gè)場(chǎng)景,那時(shí),她長(zhǎng)發(fā)飄飄,是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最年輕的副教授,也是業(yè)內(nèi)頗具影響力的青年鋼琴演奏家。
袁芳說(shuō)自己的父母,包括祖輩都是音樂(lè)的癡迷者,她四歲由母親啟蒙鋼琴學(xué)習(xí),在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附小和附中階段,師從中國(guó)著名鋼琴教育家吳元教授。高中畢業(yè)后赴德國(guó)留學(xué),成為鋼琴大師杰哈德·歐匹茲的第一位中國(guó)弟子,她的老師被認(rèn)為是德國(guó)當(dāng)代最偉大的鋼琴家,沒有之一。
豐富、全面的音樂(lè)學(xué)習(xí),讓袁芳充分吸收和掌握了德奧音樂(lè)的精髓,她也以出色的成績(jī)獲得了慕尼黑音樂(lè)與戲劇學(xué)院鋼琴和室內(nèi)樂(lè)的雙博士學(xué)位。畢業(yè)后,她在很多不錯(cuò)的發(fā)展機(jī)會(huì)向她遞來(lái)橄欖枝時(shí),選擇回國(guó),在發(fā)展自己演奏事業(yè)的同時(shí),也在母校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做一名教育的傳承者,那是2008年。
一切都很順?biāo)欤籽蜃脑迹瑹o(wú)論在音樂(lè)表達(dá)還是在事業(yè)生活中都充滿著愛與力量,作為獨(dú)奏藝術(shù)的表現(xiàn)者,能走遍最知名的音樂(lè)廳,和最牛的樂(lè)團(tuán)合作,并成為舞臺(tái)中心的人,本就是鳳毛麟角的存在,袁芳做到了。
按一種世俗的說(shuō)法,功成名就不需要再被功名利祿折磨的她,卻依然有如修道士一般, 每天練琴五個(gè)小時(shí),“關(guān)掉手機(jī)、摒除雜念,一口氣練下來(lái),中間不吃飯,也許別人覺得苦,但我覺得苦中有樂(lè)。”
“極富感染力”“能彈出作曲家的靈魂”是業(yè)內(nèi)對(duì)她的公認(rèn),“逐夢(mèng)”是她的自評(píng),“從鮑家街43號(hào)起步,學(xué)校的所在是多么響亮的名字,還在上學(xué)的時(shí)候,我就夢(mèng)想回到這里當(dāng)老師,所以,剛回來(lái)的幾年,我非常滿足,那是一個(gè)夢(mèng)想實(shí)現(xiàn)了。
“第二個(gè)夢(mèng)想是30歲前結(jié)婚生子,這個(gè)我也做到了。所有這些完成之后,我又開始拷問(wèn),我的內(nèi)心還住著什么?我想我還需要更深地追逐我對(duì)音樂(lè)的夢(mèng)想。”
我記住了逐夢(mèng)這個(gè)詞,再次見到袁芳,她把多年的長(zhǎng)發(fā)剪短了,她在2016年的年初,在美國(guó)卡內(nèi)基音樂(lè)廳上演了出色的獨(dú)奏會(huì),她也在這個(gè)時(shí)刻,從母校辭職,“要自由,也要沉淀”,更多的練習(xí),更多舞臺(tái)的綻放,更多對(duì)音樂(lè)的理解,她要這些,而面對(duì)諸多質(zhì)疑與不解的聲音,逐夢(mèng)的袁芳說(shuō),“放心,我始終不會(huì)放下對(duì)音樂(lè)教育的熱情和責(zé)任。”
內(nèi)心被束縛,一定不行
記者:今年年初,你從音樂(lè)學(xué)院辭職,很多人都覺得可惜和不解。走在標(biāo)準(zhǔn)化的路上,好好的,你為何偏要做出非標(biāo)準(zhǔn)的舉動(dòng)?
袁芳:的確是一個(gè)不太常規(guī)的、不太世俗的選擇,但對(duì)我來(lái)講是一個(gè)自然的過(guò)程。并不是我不喜歡教學(xué),我特別珍惜和學(xué)生在一起的時(shí)光,我也不會(huì)中斷在中國(guó)做音樂(lè)教育的熱情。但是人在某一個(gè)階段一定要有一個(gè)重心,演奏音樂(lè)也是挖掘心靈的寶藏,如果你感到內(nèi)心是被束縛的,那一定不行,我是一個(gè)表里如一的人,我渴望自由,但是自由里有我的強(qiáng)烈的專注,對(duì)我而言,強(qiáng)烈的專注才能創(chuàng)造藝術(shù)的純凈。在相對(duì)能夠追求自由的年齡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最有創(chuàng)造力的階段去演出去創(chuàng)作,對(duì)我而言就是自然的。當(dāng)然我也是很慎重的,當(dāng)然慎重并不意味著膽小,只是更督促你把每一步走得扎實(shí)。

我也不想停留在目前的成績(jī)里,我總覺得還應(yīng)該給學(xué)生更多。我把目前的重心放在練習(xí)和演出上,演出需要親力親為,你自己有多寬廣,你的學(xué)生才有可能多寬廣。我想之后能培養(yǎng)出一個(gè)學(xué)貫中西、最終能成為大師的人,而不只是一個(gè)獲獎(jiǎng)選手,那這就需要我有更厚的積淀,我的理想是像李斯特那樣,他是一個(gè)偉大的作曲家、鋼琴家,很少有人提他教育家的身份,但我很欣賞他的教育。他有深厚的東西給予學(xué)生,而且是無(wú)私地給。
所以我一直要求自己像一個(gè)修道士一樣練琴,這是我最留戀的生活方式。很多人覺得一口氣練五六個(gè)小時(shí)枯燥,但是枯燥的背后是豐盈,特別是社會(huì)這么浮躁,更需要這種踏實(shí)練習(xí)的那種沉靜。
記者:在面對(duì)鮮花和掌聲的時(shí)候,你享受的是什么?覺得自己夠成功嗎?
袁芳:我不太執(zhí)著于成功的那一刻,也很少發(fā)朋友圈或用其他方式“推廣”自己,在掌聲的背后,我更享受把自己都打動(dòng)的彈得真的夠好的那首曲子,我會(huì)想為什么彈得激動(dòng),過(guò)程中都做了什么準(zhǔn)備,下次要怎么準(zhǔn)備,我把它當(dāng)作個(gè)人化的體驗(yàn),而不會(huì)停留在掌聲里,至于什么是成功,我覺得自己開心,活得踏實(shí),一家人融洽生活,是我更認(rèn)可的成功,而真正的幸福也都是個(gè)人化和隱私化的。同時(shí),我也依然給自己一個(gè)學(xué)習(xí)計(jì)劃,想彈的曲子,想深入研究的音樂(lè)家太多了,我也還在路上。
記者:不懼不惑,繼續(xù)向前,接下來(lái)可見的計(jì)劃有什么?
袁芳:我一直都是有敬畏之心但勇往直前不怕困難的性格,接下來(lái),我會(huì)在德國(guó)多待一段時(shí)間,那里依然是古典音樂(lè)的中心,音樂(lè)傳承的歷史,現(xiàn)在的發(fā)展以及市場(chǎng)都非常棒。也簽約了音樂(lè)經(jīng)紀(jì)公司,但我也講到,這幾年盡量不要給我安排太多的演出,至少在近三年的時(shí)間里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最重要的都是自我提升。我想突破一些局限,也信奉厚積薄發(fā),而演出那一刻本身除了舞臺(tái)經(jīng)驗(yàn)的積累,它并不會(huì)帶來(lái)技術(shù)和理解的進(jìn)步,這是我很早就明白的道理。在一些計(jì)劃內(nèi)的演出中,我也嘗試加入中國(guó)元素的創(chuàng)新,比如在美國(guó)卡內(nèi)基音樂(lè)廳的獨(dú)奏會(huì)中,我把《黃河》鋼琴協(xié)奏曲做了一定的改編,讓這首經(jīng)典作品作為一首獨(dú)奏作品被展現(xiàn)得更飽滿,讓更多人了解這部作品和其特有的情懷。
音樂(lè)不是附屬品,是必需品
記者:為什么音樂(lè)那么美,很多學(xué)音樂(lè)的人卻顯得痛苦?
袁芳:像吳元老師那樣在音樂(lè)藝術(shù)包括人生理解上都對(duì)學(xué)生有輔助有愛的老師挺難找的,我上學(xué)的時(shí)候住校,吳老師在生活上關(guān)心我,之后出國(guó)聯(lián)系學(xué)校,甚至回國(guó)發(fā)展,每一刻都有她的關(guān)愛。我想,你發(fā)自肺腑感謝一個(gè)人、喜愛一個(gè)人,并因?yàn)樗鼰釔垡婚T藝術(shù),那個(gè)你感謝的人所做的這些一定不是利益驅(qū)使的。我也聽到不少聲音說(shuō),練習(xí)很多年之后,一輩子都不想碰琴了。我想說(shuō),鋼琴不是玩出來(lái)的,老師嚴(yán)格是必須的,但作為老師也要通過(guò)自己的心,帶領(lǐng)學(xué)生們感到音樂(lè)哪里好,哪里令人激動(dòng),哪里發(fā)人省思,哪里有意思。

在2016人民大會(huì)堂新年音樂(lè)會(huì)上,袁芳與捷克愛樂(lè)樂(lè)團(tuán)合作奉獻(xiàn)精彩演出
還有一些人覺得這條路“宅”,特別是學(xué)鋼琴,有幾個(gè)能走到塔尖,站在舞臺(tái)中心啊,既然很可能是要墊底的,那還不如早點(diǎn)不做陪練,不搞專業(yè),業(yè)余玩一玩就好。我也不認(rèn)可這種說(shuō)法,學(xué)音樂(lè)學(xué)鋼琴可以做很多工作,業(yè)余也比專業(yè)的市場(chǎng)大多了,音樂(lè)無(wú)處不在。千萬(wàn)不要局限于我要不要搞專業(yè)?我要不要考音樂(lè)學(xué)院?我上音樂(lè)學(xué)院以后干什么?從喜好出發(fā),音樂(lè)學(xué)院出來(lái)也可以搞流行,做電影電視配樂(lè)也很棒啊,我們現(xiàn)在所談的主要還在古典音樂(lè)的領(lǐng)域里,如果你能將古典與流行結(jié)合不是也很棒嗎?
同時(shí),做小學(xué),中學(xué)的音樂(lè)教師,更大的層面上普及音樂(lè)知識(shí)傳播音樂(lè)之美,都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在精神層面的東西你必須要深信不疑,深信不疑也不等于沒有疑惑,常常疑惑過(guò)后掙扎過(guò)后,更加深信不疑,那才是真的熱愛。如果,我們這些精神行業(yè)的從事者,可以不斷和各個(gè)時(shí)代、各個(gè)領(lǐng)域的音樂(lè)先賢對(duì)話的話,我覺得這是一個(gè)非常棒的事情。音樂(lè)不是附屬品,而是生活的必需品。

記者:除了自己練內(nèi)功,你有什么建議幫大家和作曲家更好地理解音樂(lè)?
袁芳:焦元溥對(duì)古典音樂(lè)評(píng)析的書都很不錯(cuò)。另外我還推薦《莫扎特的德意志蘭》《慰藉·救贖·解放》這兩本書,當(dāng)然還有《傅雷家書》,特別是家有琴童的家長(zhǎng)可以看看,都能加深對(duì)音樂(lè)的理解,在音樂(lè)里你能感到詩(shī)詞的韻律,也能如萬(wàn)花筒般看到變化的美。當(dāng)然,多去現(xiàn)場(chǎng)聽音樂(lè)會(huì),才能被撲面而來(lái)的音樂(lè)所覆蓋,就像做一次全身心的SPA。
記者:會(huì)讓女兒彈琴嗎?在音樂(lè)之外,你考慮最多的問(wèn)題是什么?
袁芳:會(huì)的,在耳濡目染之下,學(xué)習(xí)音樂(lè)愛上音樂(lè)對(duì)她來(lái)說(shuō)應(yīng)該是很自然的事情,她現(xiàn)在喜歡畫畫、唱歌,還跟我小時(shí)候一樣,尤其喜歡跳舞,很陽(yáng)光。我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我對(duì)人生不懼不惑的態(tài)度,孩子也能體會(huì)到,也許我不能給她解答她人生中所有的問(wèn)題,但我希望能成為她精神上的依靠,彼此理解。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音樂(lè)和生活其實(shí)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一定要把音樂(lè)看作事業(yè),生活歸于生活的話,可以說(shuō),我考慮最多的問(wèn)題就是讓家人生活得更舒服,把家庭生活安排得更合理,一家人每時(shí)每刻和睦融洽地在一起,也算是理想主義者的一種表現(xiàn),哈哈!
(文/王皎,來(lái)源:《北京青年》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