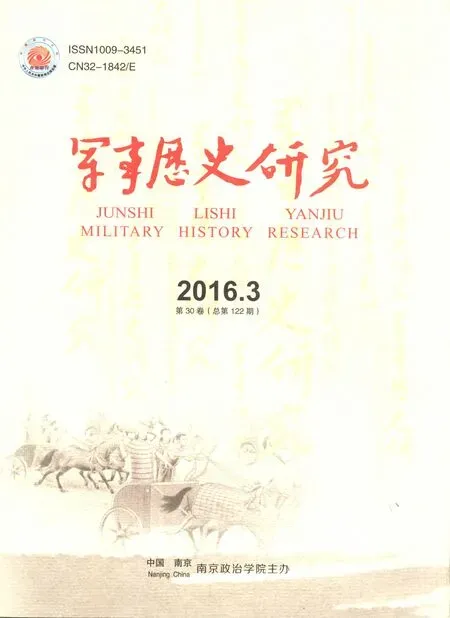蒙元軍將領劉深考實
朱建路
(南開大學 歷史學院,天津 300071)
?
·專題論文·
蒙元軍將領劉深考實
朱建路
(南開大學 歷史學院,天津 300071)
《元史》未為蒙元軍將領劉深立傳,依據新發現的劉深為遷葬母親所立墓碑的碑文,并結合現有文獻可知,劉深字仲淵,籍貫為大都路寶坻縣,于1259年蒙元軍渡江攻鄂之役中脫穎而出,平定李璮之亂后進入水軍,被任命為百戶,攻襄樊期間先后被任命為千戶和管軍總管,焦山之戰后被任命為萬戶,此后,他繼續參加追討南宋殘余勢力的戰斗。征討八百媳婦國是劉深人生的重大轉折點,此次出征雖為劉深首倡而以失敗告終,但其罪責不應歸于劉深一人之身。
劉深蒙元軍八百媳婦國元成宗完澤
劉深是在征宋戰爭中成長起來的戰功赫赫的蒙元軍著名將領。他首倡征討八百媳婦國,卻因戰敗而被元廷誅殺,《元史》不為其立傳。目前學界對劉深的了解,僅局限于散見在《元史》及元人文集中關于他的征宋、征八百媳婦國的零星記載。1983年天津市寶坻縣城關鎮史各莊鄉陳甫村出土一塊與劉深關系密切的墓碑,楊新先生撰寫《寶坻區劉深墓碑考釋》*《天津博物館論叢2012》,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104—110頁。一文,對此碑釋錄并參以正史列舉了劉深參與的主要戰役,分析了劉深征討八百媳婦國失敗被殺的經過。但楊文所錄的劉深碑文不完整,對碑主是誰、立碑時間、劉深被殺的深層原因等問題的考證分析也不準確。鄒萬霞以此碑為依據撰寫的《淺析金頭將軍劉深衛國之功過》*鄒萬霞:《淺析金頭將軍劉深衛國之功過》,《黑龍江史志》2015年第5期。一文,也只是粗略、通俗地向讀者介紹了劉深這位重要的蒙元軍將領。筆者認為此碑的價值尚未得到充分發掘,故從碑刻內容出發,勾稽文獻中關于劉深的記載,對劉深的身世、征宋歷程及其征八百媳婦國被殺原因等進行重新考證,以期還原這位蒙元軍將領的真實面貌,為深化蒙元軍歷史研究提供新的參考。
一
天津市寶坻區學者宋健先生為筆者提供了墓碑的碑刻拓片,通過對碑文的考釋,可初步了解劉深的身世及其早期征宋的歷程等。為研究方便,現將碑刻拓片與重新釋錄的碑文展示如下:

(元劉母太夫人遷葬碑)
1.(前缺)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劉元撰,承事郎大都路總管都同提舉前翰林兼國史院編修□□(后缺)
2.(前缺)至元十五年歲次戊寅秋七月,昭勇大將軍、前沿海經略使、行征南左副都元帥劉公率海艦七百艘追捕余燼,獲文武□□□□□□□□
3.(前缺)太夫人黃氏易葬有期,帥府僚佐張彬文卿與予有梓里之好,因彬以文為請,曰:“天下之事,未有無所自而遽至于大者,□□□□□□□
4.(前缺)世□□,其來也有源,其積也有漸耳。況惟不肖崛起布衣,猥登帥閫,上膺旌(?)節之榮,下擁貔貅之眾,出入行陣,鏖戰海洋,脫萬死,獲一□□□□□
5.(前缺)□獲□□,其何能至于此哉。愿因太夫人之襄事之日,表揚潛德,著之文石,以示來裔。茲人子之至情也,先生幸留意。”其辭切,其情哀,其言婉,□□□
6.(前缺)弗□辭,乃用其所狀之行而撰次之。公諱深,字仲淵,世為大都寶坻人。自大父以上,遭金源板蕩,失其名次。父諱子成,性恬憺,不樂仕進,□□□
7.(前缺)兵南下,嘗扈從充監軍。河南平,脫身歸鄉里,悠游年歲,隱居以自適。今享壽八十,身其康強矣。母黃氏,系出名族,克閑婦道,其檢身垂教,□□
8.(前缺)享年七十有九,終于□坊私第之正寢,實至元十年歲次癸酉十一月之晦日也。次母楊氏,終于至元五年歲次戊辰十一月之五日,俱藁葬于□□
9.(前缺)□□有子三人,皆黃氏出焉。公其仲子也,幼尚氣節,頗兼吏能。己未之渡江,公在部伍中,遇敵轉戰,為師長奇之。中統三年,從攻逆璮于濟南,力□
10.(前缺)□□□物貨甚厚,尋
11.(前缺)□□水軍萬戶府□□,由是□知水戰之利。至元六年,師圍襄樊及百丈、鹿門二山,公首取其襄城外堡,又以舟師克敵于罐子灘,遂升千戶,□□
12.(前缺)□□□出伐,我師不得□,公率麾下力□之□,加武略將軍,佩金符,繼命公守鹿門,屢卻宋援兵。然自圍襄,歷四年不下,蓋襄之所以持久者,倚
13.(前缺)□□□□□□□□上取樊之策,仍□□臨沖鉤梯之具,且曰:“謀人之兵,敗則死之,如所言不效,請以死罪從事。”省府從之。連拔其城,擢管軍
14.(前缺)□□□□。至元十一年,大舉南伐,公在諸將中,每戰有功,如沙洋、新城、渡江之役,以功加武義將軍。焦山之役,以功升萬戶,佩金虎符。越明年,攻
15.(前缺)□□□□□□以功授獲遠大將軍,尋改授昭勇大將軍、和州達魯花赤。至元十四年以宋孽未殄
16.(前缺)□□□□以公為沿海招討使,俄授改沿海經略使、行征南左副都元帥,仍錫兩臺銀印綬,遂率白鷂舟艦自慶元遵海而南,與逋寇張世杰等
17.(前缺)□□□□□中數戰,世杰僅以身免,生獲文武官百、軍二千,有司奏其功
18.(前缺)□深加□□□八月□□
19.(前缺)□□□□□使□□兩臺銀章,其金虎符如故,以公宿將望重,仍敕巡鎮諸江口,故以舊率水軍肄焉,別賜其官屬金虎符一,金符六。
20.(前缺)有三□□□是從公給付之。將赴任,□□開平,遂有是請。予因詢諸將佐,簽云:公處心剛明,治軍嚴整,寬而猛,威而惠,故士卒樂為之用。
21.(前缺)□□古人□□□之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又曰:君子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不見乎。□者劉氏先世修其德,
22.(前缺)者不然何□□公□□康寧,子孫□吉,出良將于畎畝之中,表表有如是哉!況春秋鼎盛,極它日所□又未量也。監軍公諸子:長曰海,
23.(前缺)□。孫男八人:曰世英,□武略將軍、千戶、兼和州路總管府軍民達魯花赤;曰世昌,曰世隆,公之子也。曰世偉,曰世雄,曰世杰,海之子□
24.(前缺)女孫一人,□□□□□□□□□□□□□是月廿有八日,奉太夫人黃氏及楊氏之柩附葬于縣□王村之先塋,□□□□□
25.(前缺)□□□□□□□□□□□□□之□起□□□而不辭,朝為白屋之烈士,暮為細柳之將軍,譬□□木區以□□□□□□□□□□□□
26.(前缺)□公□□□元□□□□不充□□□乎□□□□有如是者,吾□列宗。亦云:
27.(前缺)□□□
這篇碑文殘缺較嚴重,影響了對其解讀。楊新先生認為這是劉深的墓碑,且其立碑時間應在元大德七年(1303年)劉深被誅之后。但碑文第3行說,“太夫人黃氏易葬有期,帥府僚佐張彬文卿與予有梓里之好,因彬以文為請”,碑文第24行說,“奉太夫人黃氏及楊氏之柩附葬于縣□王村之先塋”。筆者認為,這應該是至元十五年(1278年)劉深因遷葬其母黃氏、楊氏,而通過“僚佐張彬文”請來翰林直學士劉元撰寫碑文,此碑為劉深母親之墓碑而非他自己的墓碑,可定名為“元劉母太夫人遷葬碑”(后文簡稱“遷葬碑”)。*依據敦煌吐魯番文書整理的規范,對一些沒有標題的文書要擬定一個題目,為研究方便故將此碑定名。一般來說,撰寫碑文與立碑時間不會相差太久,因此立碑時間應為撰寫碑文后不久,即碑文第2行所說“至元十五年歲次戊寅秋七月”之后不久。*《中國文物地圖集·天津分冊》中說此碑立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但沒有說明理由。見《中國文物地圖集·天津分冊(文物單位簡介)》,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年,第121頁。碑文第19至20行說:“以公宿將望重,仍敕巡鎮諸江口,故以舊率水軍肄焉……將赴任,□□開平,遂有是請。”劉深在離開上都將去赴任前請劉元撰碑文,可見撰文的地點為上都。《元史·劉元傳》載有元代著名雕塑家劉元傳略,撰“遷葬碑”文者與雕塑家劉元是否為同一人呢?《元史·劉元傳》記載劉元于至元年間“行幸必從”,*宋濂等:《元史》卷230《劉元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點校本,第4546頁。“行幸”專指古代皇帝出行。元代實行兩都制度,皇帝于每年春夏北巡上都,秋冬返居大都。“行幸必從”指劉元每年跟隨皇帝往返上都與大都之間。筆者推測,至元十五年在上都為劉深母撰碑者劉元,即是《元史·劉元傳》記載的雕塑家劉元。
《元史》中關于劉深的記載分散在一些本紀和列傳中,且主要是關于其征戰的紀錄,目前學界對劉深的籍貫、家世與名諱等所知甚少。清張之洞《寶坻縣志》卷10《墓塚》載:“劉元帥墓,為中書行省左丞諱劉深之墓,在縣西八里,石獸碑碣尚有存者。”*《乾隆寶坻縣志》卷10《封表·冢墓》,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482頁。劉深的墓碑與其母之墓碑一樣,也在寶坻縣,說明寶坻縣應是劉深家族墓地之所在。“遷葬碑”碑文第6行明確記載:“公諱深,字仲淵,世為大都寶坻人。”由此可知,劉深,字仲淵,其籍貫為大都路寶坻縣。
關于劉深的家世,碑文也有一定的介紹,第6行說:“自大父以上,遭金源板蕩,失其名次。”可知劉深家族在金代并沒有什么人擔任顯赫的官職,否則不會名諱盡失。碑文第6至7行說,劉深之父“諱子成,性恬憺,不樂仕進,□□□(前缺)兵南下,嘗扈從充監軍。河南平,脫身歸鄉里,悠游年歲,隱居以自適。”“兵南下”在元代史料中多指蒙元軍隊南下攻打金軍,“河南平”指公元1234年蒙元滅金。劉深之父劉子成為寶坻縣人,能在蒙元軍隊中任職,應為較早投降蒙古的漢人,“嘗扈從充監軍”,說明后來他在蒙元軍中充當監軍。*唐代后期的監軍一職,主要負責監視軍隊將領的行動,多以宦官充任。《金史》記載金代設“元帥左右監軍”,正三品,但沒有注明職掌。蒙元軍進入中原,歸順的漢地世候沿用金代官職,多設置監軍,具體職掌亦不清楚。但推測其主要還是一種監視軍人將領的官職,如《康熙束鹿縣志》卷10《耿氏先世碑銘》記載世候耿福歸順木華黎后,勸降金恒山武仙,武仙即“懇請一人監治軍事。公曰:君仗義來歸,豈反復者,何以監為?固請不已,遣董善為之佐。”這則材料記載武仙請求派監軍監視自己,以此求得對方信任。劉子成投降蒙古后肯定不能立即充當監軍,至于后來如何充當監軍,碑刻簡略,不得其詳。第22行有“出良將于畎畝之中”之句,“畎畝”說明劉深出生于農家。第25行有“朝為白屋之烈士,暮為細柳之將軍”一語,“白屋”指茅屋,代指寒士的住所。上述說明,當時劉氏家族并不是閥閱之家。
“遷葬碑”碑文第9行說:“己未之渡江,公在部伍中,遇敵轉戰,為師長奇之。”“己未”即憲宗九年(1259年)。史載,憲宗八年(1258年)忽必烈受命代替塔察兒統帥左翼軍,攻擊長江中游重鎮鄂州,以接應主力東出四川。“己未之渡江”應是指公元1259年蒙軍渡江攻鄂州之役。由碑文可知,劉深參加了這場戰爭,并在此戰中脫穎而出,受到重視,為以后晉升打下基礎。
“遷葬碑”碑文第9至11行說:“中統三年,從攻逆璮談于濟南,力□(前缺)□□□物貨甚厚,尋(前缺)□□水軍萬戶府□□,由是□知水戰之利。”這段文字缺漏較多,但還是可以看出大意:中統三年(1262年),劉深參加了討滅李璮的戰役,*李璮是金末紅襖軍首領李全養子,1231年襲父職為治益都行省,專制山東30余年,是金元之際著名的漢人世候。中統三年,李璮趁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無暇南顧,獻漣水等三城予南宋,發動叛亂,進據濟南。忽必烈命親王合必赤、史天澤率軍平叛,李璮投大明湖未死,后被俘處死。此次叛亂對元代政治影響很大,平叛防止了漢人世候的分裂,鞏固了忽必烈的統治;此后忽必烈對漢人的猜忌也加重,各地漢人世候紛紛交出兵權,漢人官僚也被元廷疏遠。此后參加了水軍萬戶府,由此開始了在水軍中的征戰。蒙元軍擅長馬戰,隨著戰線向南方推進,河流湖泊越來越多,訓練一支水軍變得越來越迫切。蒙元水軍最早由易州人解誠創建。*王風雷:《元代水軍訓練及軍事科技教育》,《蒙古史研究》第11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91頁。《元史》卷165《朱國寶傳》載:“朱國寶,其先徐州人,后徙寶坻。……憲宗將攻宋,募兵習水戰。國寶以職官子從軍,隸水軍萬戶解誠麾下。己未,世祖以兵攻鄂,國寶攝千戶。……(中統)三年,圍李璮于濟南,佩金符,鎮戍東海。從征襄陽,攝四翼鎮撫,督造戰船,筑萬山堡。”*宋濂等:《元史》卷165《朱國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點校本,第3876頁。朱國寶與劉深都是寶坻人,都因父職入官參加水軍,兩人后來的攻鄂、征李璮、征襄陽等經歷都相同,劉深初期可能也是隸屬于水軍萬戶解誠麾下。碑刻漫漶,“水軍萬戶府”后二字不清,聯系后文主要記述劉深從千戶到總管再到萬戶的升遷,筆者推測此處漫漶文字可能為劉深任水軍萬戶府的“百戶”或“彈壓”。
平定李璮之后,至元四年(1267年)安撫使劉整獻策,*劉整為宋荊湖制置使孟珙部將,累遷潼川十五軍州安撫使,知瀘州軍州事。中統二年(1261年)以瀘州降元,為夔府行省,兼安撫使。至元四年(1267年)建議先攻襄陽,使蒙元軍進攻重點從四川轉移到荊襄,這加速了南宋的滅亡。建議集中攻打漢水流域的襄樊城。襄陽和樊城跨漢水兩岸,攻下襄樊后水軍可以順漢水抵長江,順流而下到達臨安,攻滅南宋。襄樊地位的重要性使蒙元與南宋對襄樊都極為重視,雙方在此進行了長時間的對峙。攻打襄樊期間,蒙元軍大建水師,至元七年(1270年)劉整“與阿術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乘驛以聞,制可。既還,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宋濂等:《元史》卷161《劉整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點校本,第3787頁。作為水軍將領的劉深在水軍迅猛發展時期也得到快速升遷,“遷葬碑”碑文第11行說,“至元六年,師圍襄樊及百丈、鹿門二山,公首取其襄城外堡,又以舟師克敵于罐子灘,遂升千戶”。蒙元軍在襄樊周圍鹿門、白河口、百丈山、萬山等處修筑城堡,圍困襄樊,宋軍也展開反包圍的戰斗,碑文中所說的罐子灘之戰,即史載至元七年(1270年)宋將范文虎援助襄陽的戰斗,劉深在奪取襄城外堡后,又率領舟師取得罐子灘之戰的勝利,因此而升千戶。
襄樊戰役是宋元之間一場耗時5年的圍困戰,襄陽與樊城守軍互為唇齒堅持抵抗蒙元軍的圍攻。至元九年(1272年)三月蒙元軍攻破樊城外郭,次年正月攻破樊城。不久宋軍守將呂文煥即以襄陽投降蒙元軍。“遷葬碑”碑文第12至13行說:“然自圍襄,歷四年不下,蓋襄之所以持久者,倚(前缺)□□□□□□□□上取樊之策,仍□□臨沖鉤梯之具,且曰:‘謀人之兵,敗則死之,如所言不效,請以死罪從事。’省府從之。連拔其城,擢管軍(前缺)”。“上取樊之策”,此句所指應為攻樊城之事,“省府”應該指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屬于臨時執行軍事征伐任務的行省。*李治安:《元代河南行省研究》,《蒙古史研究》第6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93頁。碑刻漫漶,但大致可以看出在攻取襄樊的戰略戰術上,劉深主張先攻取樊城,后來也取得成功。《元史》卷7《世祖紀四》也記載:“(至元九年十一月)癸酉,以前拔樊城外郛功,賞千戶劉深等金銀符。”*宋濂等:《元史》卷7《世祖紀四》,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點校本,第143頁。可見劉深在攻克樊城之戰中確實立下大功。元制“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萬戶、千戶、百戶分上、中、下。萬戶佩金虎符,符趺為伏虎形,首為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蘇天爵:《元文類》卷41《雜著·經世大典政典總序·軍制》,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第591頁。如前文所述,劉深在罐子灘之戰后升千戶,在焦山之役后升萬戶,佩金虎符(后文有述),而樊城之戰發生時間正處于這兩場戰役之間,依據蒙元軍制可知,劉深在攻取樊城后應該擢升為管軍總管,即蒙元軍制中萬戶之下的總管。
“遷葬碑”碑文第14行說:“至元十一年,大舉南伐,公在諸將中,每戰有功,如沙洋、新城、渡江之役,以功加武義將軍。焦山之役,以功升萬戶,佩金虎符。”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任命伯顏為征宋軍總統帥,大舉南伐。大軍自襄陽而下,首先到達郢州,伯顏觀察地形,大軍在黃家灣堡繞道漢水,放棄攻郢而去。《平宋錄》載:“丞相遣數將率兵進黃家灣堡,即日克之,總管劉二、李勞山首獲戰功。”*劉敏中:《平宋錄》卷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08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041頁下。據“遷葬碑”碑文記載,劉深之父“有子三人,皆黃氏出焉。公其仲子也。”劉深在家排行第二,《平宋錄》所提“總管劉二”應是劉深。渡江之役,指陽邏堡渡江戰斗。關于渡江的地點,伯顏頗費心機。《元文類》卷41《經世大典序錄二·征伐》載:“(至元十一年)十一月廿三日,大軍至蔡店,伯顏大會諸將,議渡江,遣總管劉深、千戶馬福觀沙湖水勢,令諸將皆趨漢口。諸將曰:漢口水急且有備,不若由淪河轉取沙武口以入大江。伯顏遣覘沙武口,宋將夏貴堅守,其勢難犯……”*蘇天爵:《元文類》卷41《雜著·經世大典政典總序·征伐》,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第556頁。此后蒙元軍攻占沙武口,進至陽邏堡,伯顏秘令阿術趁夜自陽邏堡渡江,順利到達長江南岸。在焦山之役中,劉深“以功升萬戶,佩金虎符”。《元史》卷8《世祖紀五》記載:“(至元十二年秋七月庚午朔)辛未,阿術、阿塔海登南岸石公山,指授諸軍。水軍萬戶劉琛循江南岸,東趨夾灘,繞出敵后。董文炳直抵焦山南麓,以掎其右;招討使劉國杰趣其左,萬戶忽剌出搗其中。張弘范自上流繼至,趣焦山之北。大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天地,乘風以火箭射其篛篷。宋師大敗,世杰、虎臣等皆遁走。”*宋濂等:《元史》卷8《世祖紀五》,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點校本,第168頁。劉深繞出敵后,與諸將合圍取得焦山之戰的勝利。《元史》記焦山之戰前劉深已經是萬戶,但據“遷葬碑”碑文記載,焦山之戰后劉深才升為萬戶,筆者認為《元史》的記載應屬事后追述,“遷葬碑”碑文為一手材料,劉深應是在焦山之戰后才升為萬戶。
“遷葬碑”碑文第14至15行又說:“越明年,攻(前缺)□□□□□□以功授獲遠大將軍,尋改授昭勇大將軍、和州達魯花赤。”“越明年”指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史》卷59《地理二》記廬州路下有和州:“和州,中。唐改歷陽郡,后仍為和州。宋隸淮南西路。至元十三年,置鎮守萬戶府。明年,改立安撫司。又明年,升和州路。二十八年,降為州,隸廬州路。”*宋濂等:《元史》卷59《地理二》,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點校本,第1411頁。“遷葬碑”碑刻文字殘缺,但基本可以推測,劉深被任命為和州達魯花赤應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或之后不久。

至元十四年(1277年),劉深自慶元南下征伐南宋流亡小朝廷。“遷葬碑”碑文第17行說:“與逋寇張世杰等(前缺)□□□□□中數戰,世杰僅以身免,生獲文武官百、軍二千,有司奏其功。”《宋史》卷47《瀛國公紀》記載:“(至元十四年十一月)元帥劉深以舟師攻昰于淺灣,昰走秀山……(十二月)丁丑,劉深追昰至七州洋,執俞如珪以歸。”*脫脫等:《宋史》卷47《瀛國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943—944頁。碑文中所提到的“世杰僅以身免,生獲文武官百、軍二千”,應是《宋史》所記載的七州洋之戰。《宋史》中記載“執俞如珪以歸”,大概劉深在淺灣、七洲洋之戰后回軍慶元。

《元史》卷10《世祖紀七》記載:“(至元十六年十一月)戊辰,命湖北道宣慰使劉深教練鄂州、漢陽新附水軍。”*宋濂等:《元史》卷10《世祖紀七》,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點校本,第217頁。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一月,已是湖北道宣慰使的劉深受命教練鄂州、漢陽新附水軍。《元史》卷11《世祖紀八》載:“(十八年十月)立行中書省占城,以唆都為右丞,劉深為左丞,兵部侍郎也黑迷失參知政事。”*宋濂等:《元史》卷11《世祖紀八》,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點校本,第 235頁。劉深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月被任命為新建立的占城(亦稱占婆)行中書省左丞。后占城反叛元廷,元廷以唆都為將征伐占城,《元史》卷12《世祖紀九》載,至元十九年(1282年)“戊戌,以占城既服復叛,發淮、浙、福建、湖廣軍五千、海船百艘、戰船二百五十,命唆都為將討之。”*宋濂等:《元史》卷12《世祖紀九》,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點校本,第243— 244頁。《元史》卷129《唆都傳》亦載,唆都于至元“十八年,改右丞,行省占城。十九年,率戰船千艘,出廣州,浮海伐占城。”*宋濂等:《元史》卷129《唆都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點校本,第3152頁。此時劉深作為占城行省左丞,應該也隨同唆都一起參加了至元十九年(1282年)征占城的戰爭。此后史籍對劉深的記載較少,《元史》卷136《哈剌哈孫傳》記載:“(大德)五年,同列有以云南行省左丞劉深計倡議曰……”*宋濂等:《元史》卷136《哈剌哈孫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點校本,第3293頁。可知,到了元大德五年(1301年),劉深已是云南行省左丞。
二
劉深前半生戰功赫赫,但大德年間征八百媳婦國是他從輝煌走向滅亡的轉折點。大德初年,八百媳婦國經常進攻云南邊境。《經世大典》記載:“大德元年,八百媳婦國與胡弄攻胡倫,又侵緬國,車里告急,命云南省以二千或三千人往救。二年,與八百媳婦國為小車里胡弄所誘,以兵五萬與夢胡龍甸土官及大車里胡念之子漢綱爭地相殺,又令其部曲混干以十萬人,侵蒙樣等。云南省乞以二萬人征之。四年,梁王上言,請自討賊。”*蘇天爵:《元文類》卷41《雜著·經世大典政典總序·征伐》,第581頁。《元史》卷136《哈剌哈孫傳》載,元大德五年(1301年)“同列有以云南行省左丞劉深計倡議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上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國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宋濂等:《元史》卷136《哈剌哈孫傳》,第3293頁。這里的“同列”指右丞相完澤,《元史》卷156《董士選傳》記載:“時丞相完澤用劉深言,出師征八百媳婦國。……完澤說帝:‘江南之地盡世祖所取,陛下不興此役,則無功可見于后世。’帝入其言,用兵意甚堅,故無敢諫者。”*宋濂等:《元史》卷156《董士選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點校本,第3678頁。可見,征八百媳婦國是由劉深首倡,丞相完澤對此支持并上奏成宗皇帝。蒙古帝國是黃金家族的共同財產,每位大汗都有擴大這份財產的責任。此時的元成宗即位時間不長,他也想借此次征戰來建立軍功、樹立威信,這次出征被賦予了很多的政治意義。
但這一建議遭到左丞相哈剌哈孫和御史中丞董士選的強烈反對。哈剌哈孫認為:“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宋濂等:《元史》卷136《哈剌哈孫傳》,第3293頁。董士選進言:“今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令當取,亦必遣使諭之,諭之不從,然后聚糧選兵,視時而動。豈得輕用一人妄言,而致百萬生靈于死地?”*宋濂等:《元史》卷156《董士選傳》,第3678頁。哈剌哈孫自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至大德二年(1298年)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對西南邊疆的狀況較為了解。他總結世祖朝對外夷征戰的經驗教訓,在諫止征交趾發湖湘富民屯田廣西一事時,曾提出“往年遠征無功,瘡痍未復,今又徙民瘴鄉,必將怨叛。”*宋濂等:《元史》卷136《哈剌哈孫傳》,第3293頁。元世祖忽必烈的數次海外征伐,有半數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有的甚至還損失慘重。哈剌哈孫和董士選的反對不失為遠見卓識,不幸的是他們的意見并沒有被一心開邊建功的元成宗采納。
大德四年(1300年)十二月,元成宗“遣劉深、合剌帶、鄭佑將兵二萬人征八百媳婦,仍敕云南省每軍十人給馬五匹,不足則補之以牛。”*宋濂等:《元史》卷20《成宗紀三》,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點校本,第433頁。以劉深為主將開始征伐八百媳婦國。《元史》卷20《成宗紀三》記載:“大德五年二月丁亥立征八百媳婦萬戶府二,設萬戶四員,發四川、云南囚徒從軍。大德五年二月己卯……以劉深、合剌帶并為中書右丞,鄭佑為參知政事,皆佩虎符。大德五年五月丙寅,詔云南行省自愿征八百媳婦者二千人,人給貝子六十索。丁卯,太白犯井。”*宋濂等:《元史》卷20《成宗紀三》,第433頁。
西南地區地勢險要、交通不便,軍需籌措不易,“江漢、湖湘之民餉軍,率用米三十石不足致一石。父子皆行,困踣道路,累百人無一二還者。”*虞集:《道園類稿》卷37《董忠宣公家廟碑銘》,《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第197頁。這次出征還未到達八百媳婦國,即因征調軍需激起了土官蛇節、宋隆濟的叛亂。《元史》卷20《成宗紀三》載:“(大德五年五月)壬戌,云南土官宋隆濟叛。時劉深將兵由順元入云南,云南右丞月忽難調民供饋,隆濟因紿其眾曰:‘官軍征發汝等,將盡剪發黥面為兵,身死行陣,妻子為虜。’眾惑其言,遂叛。”*宋濂等:《元史》卷20《成宗紀三》,第435頁。《元史》卷136《哈剌哈孫傳》載:“道出湖廣,民疲于饋餉。及次順元,深脅蛇節求金三千兩、馬三千匹。蛇節因民不堪,舉兵圍深于窮谷,首尾不能相救。”*宋濂等:《元史》卷136《哈剌哈孫傳》,第3293頁。宋隆濟叛亂之后,劉深未能立刻控制住局面,反因潰逃而被朝臣彈劾。大德六年(1302年),江南行御史臺中丞陳天祥針對征八百媳婦國上《征西南夷疏》說:“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生變,所在皆叛。深既不能制亂,反為亂眾所制,軍中乏糧,人自相食,計窮勢蹙,倉黃退走,土兵隨擊,以致大敗。深棄眾奔逃,僅以身免,喪兵十八九,棄地千余里。”*宋濂等:《元史》卷168《陳天祥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點校本,第3984頁。由上可知,此次叛亂的主要原因是征集軍需導致民不堪命。
除因征集軍需引發叛亂外,軍隊將領間的矛盾可能也是這次出征失敗的重要原因。參與這次出征的還有著名的水軍將領張弘綱。據《張弘綱墓志》載:“右丞劉深任開邊,夙忌憾公,故擠挽有是行。公愬于淮東宣司曰:劉右丞不知兵,貪功勤遠,使隸麾下,必挾隙沮我,身不足惜,系國事匪輕爾。即就道,深果督軍務深入,公策皆不聽。道當由八番進,八番賂深,改道鬼州,頑苗先叛,雖所向無前直抵蠻穴,繼而糧盡兵疲,伏發桫樹,箐斷險要,弮空鼓竭,公揮刃大呼曰:吾效命今日矣。遂歿于陳,實是年十二月七日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元鐵可父子墓和張弘綱墓》,《考古學報》1986年第1期。陳旅《安雅堂集》卷5《張武定廟堂詩序》載:“深與公有宿釁,迫公同行,公年六十五矣,計不得脫,則曰:‘即死深手,不若死于戎行,吾其擇死所乎?’至鬼州畫計,深皆不從,驅兵入險阨,餽運不繼,士卒饑憊不能戰,深棄軍宵遁,公遂力戰以死。”*陳旅:《安雅堂集》卷5《張武定廟堂詩序》,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年,第205頁。許有壬《左丞張武定公挽詩序》記這次征八百媳婦國說:“主帥憸人,且夙有隙,公策可決勝,皆捍格不行。”*許有壬:《許有壬集》卷30《左丞張武定公挽詩序》,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91頁。由上述史料可知,劉深與張弘綱“夙忌憾”“有宿釁”“夙有隙”,二人之間矛盾突出。出征軍隊將領間不能和衷共濟,反而矛盾重重,這必然影響征戰進程。
蛇節與宋隆濟的叛亂,被平章劉國杰平定。大德六年(1302年)二月“罷征八百媳婦右丞劉深等官,收其符印、驛券。”*宋濂等:《元史》卷20《成宗紀三》,第440頁。劉深得罪,遇天下大赦應赦免,但被哈剌哈孫以“徼名首釁,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宋濂等:《元史》卷136《哈剌哈孫傳》,第3293頁。而拒絕。大德七年(1303年)二月乙巳,“以征八百媳婦喪師,誅劉深,笞合剌帶、鄭祐,罷云南征緬分省。”*宋濂等:《元史》卷21《成宗紀四》,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點校本,第450頁。征八百媳婦國的失敗,挫傷了元成宗即位之初希望像世祖皇帝一樣建立赫赫武功的雄心,從此他再沒有發動對外夷的大規模戰爭,元成宗終成一代守成之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殺掉劉深也是元成宗轉變對外政策所釋放的一種政治信號。
對于劉深的評價,元人均持否定態度。陳天祥在《征西南夷疏》中認為:“此乃得已而不已之兵也……軍勞民擾,未見休期,只深一人,是其禍本。”*宋濂等:《元史》卷168《陳天祥傳》,第3948頁。元人揭傒斯和虞集分別在《寄題張齊公廟》*揭傒斯著,李夢生標校:《揭傒斯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2頁。和《道園類稿》卷1《萬戶張公廟堂詩并序》*虞集:《道園類稿》卷1《萬戶張公廟堂詩序》,《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5冊,臺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第290頁。指責劉深“射功利”,鼓動成宗開邊。清人汪輝祖不同意將征八百媳婦國的罪過加諸劉深一人的說法,其所著《元史本證》針對《元史·完澤傳》給予完澤“能處之以安靜不急于功利,故吏民守職樂業世稱賢相云”的評價,指出:“案《董士選傳》,‘丞相完澤用劉深言,出師征八百媳婦國,’‘由是民死者亦數十萬,中外騷然。而完澤說帝‘江南之地盡世祖所取,陛下不興此役,則無功可見于后世,’‘帝入其言用兵意甚堅。’是完澤固急于功利者,《傳》諱之太深矣。”*汪輝祖著,姚景安點校:《元史本證》卷35《完澤傳》,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92頁。汪輝祖認為完澤是征八百媳婦國的重要推動者,《元史》對完澤的評價并不客觀。汪輝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上文也提到這次出征得到元成宗批準,其中隱含有重要的政治意圖。筆者認為,大德初年八百媳婦國常挑動戰爭,征伐八百媳婦國的決策是正確的。只是戰前準備不足,行軍中途在當地征索軍需激起民變,加之將領之間矛盾,作戰中指揮失當,才導致征戰失敗。勝敗乃兵家常事,并不能將責任都推在劉深身上。丞相完澤與元成宗希望通過戰爭建立功業,草率發動戰爭,才應該對此負主要責任。劉深被殺,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元成宗和丞相完澤的替罪羊。
上文通過將出土碑刻與文獻相結合進行研究,使我們對蒙元軍將領劉深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和了解。劉深在己未年參與渡江之戰,平定李璮之亂后進入水軍,被任命為百戶,攻襄樊期間先后被任命為千戶和管軍總管,焦山之戰后被任命為萬戶。此后,他繼續參加追討南宋殘余勢力的戰斗。征討八百媳婦國是他人生的轉折點,因出征失敗而被殺,成為元成宗的政治犧牲品。由于史料缺乏,目前學術界尚不清楚至元后期到征八百媳婦國前近10年里劉深的人生歷程,這有待于今后新史料的發掘。
(責任編輯張陳)
Study on Liu Shen, General of Mongol Army of Yuan Dynasty
ZhuJianlu
(School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TheHistoryofYuanDynastycontains no biography of Liu Shen, general of Mongol Army of Yuan Dynasty. Existing literature plus newly discovered tombstone inscriptions for Liu’s mother reveal that the native place for Liu Shen, also named Zhongyuan, was Baodi County, Dadulu. In the 1259 Battle of Hubei in which the Mongolian army crossed the river, Liu showed his talent. After Li Tan’s Rebellion was suppressed, Liu entered the navy and was appointed asBaihu(百戶). During the attack at Xiangfan he was first appointed asQianhu(千戶) and later as general head of the troop, and after the Battle of Jiaoshan he was appointed asWanhu(萬戶). Henceforth, he continued to participate in fighting the remnant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expedition to the 800-Women Kingdom marked the major turning point in Liu’s life. Although the expedition initiated by Liu Shen met with failure, but the blame should not have been solely and entirely put on him.
Liu Shen; Mongol Army of Yuan Dynasty; the 800-Women Kingdom; Temür, Emperor Chengzong of Yuan; Wan Ze
2012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遺存資料的搶救、發掘及整理研究”(12&ZD142)
朱建路,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邯鄲市博物館文博館員。
K247; E292
A
1009-3451(2016)03-006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