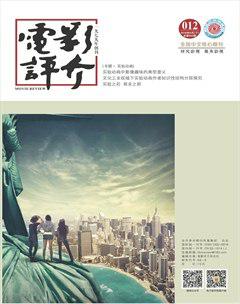《百鳥朝鳳》對“西部電影”風格的堅守
王海紅
《百鳥朝鳳》對“西部電影”風格的堅守
王海紅
2016年5月6日,中國第四代導演領軍人物吳天明執導的電影遺作《百鳥朝鳳》歷經艱辛終于在全國公映。電影《百鳥朝鳳》改編自肖江虹的中篇同名小說。小說主要聚焦農村一支民間嗩吶樂班的際遇,描寫了兩代嗩吶藝人以及嗩吶這種民間藝術形式在現代化的擠壓下正逐漸消亡的過程。而吳天明則對小說進行了“西部電影”式風格的改編,影片充滿情懷而感人至深,講述了在社會變革、民心浮躁的年代里,新老兩代藝人在現實困境之下為了嗩吶這一民間技藝的傳承,堅守信念的故事,表現了傳統民間文化與大眾流行文化的沖突,表達了對傳統民間藝術在現代流行文化沖擊下日漸式微,傳統文化生長土壤日趨貧瘠化,傳人匱乏的擔憂,以及對現實中下層人的人文關懷,體現了吳天明一以貫之的植根于黃土地的對于傳統文化的憂患意識,現實困境之中與命運不斷抗爭的精神,強烈的人文主義情懷。
一、“西部電影”風格
1984年3月6日,在西安電影制片廠的年度創作會議上,鐘惦斐在《面向大西北,開拓新型的西部片》中提議,美國有所謂的“西部片”,我們是否也可有自己特色的“西部片”。鐘惦斐首次提出了“西部電影”的概念,并大力倡導,此后這一提議在電影界引發強烈反響,以西安電影制片廠為代表的眾多電影創作者在創作實踐中開始有意識地“拍攝中國西部片”,形成了一種較為鮮明的、群體性的電影美學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從形式特征到深層內涵,中國的黃土地電影與美國的西部片的概念截然不同,只是借用美國“西部片”的名稱而已。
吳天明是中國第四代導演代表人物之一,還曾是西安電影制片廠的廠長,他開明,銳意改革,不遺余力地扶持后輩,啟用有才華的青年導演,讓黃建新、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周曉文、蘆葦、何平、顧長衛、趙非、曹久平等導演迅速成長。張藝謀說:“吳天明是我電影之路的伯樂,也是第五代導演的伯樂。沒有他就沒有《紅高粱》,他改變了我的人生,改變了我的命運。”20世紀80年代以來,吳天明將有才華的青年導演聚攏在西安電影制片廠,他們創作了一系列以展現西北黃土高原的風土人情為主,反映中華民族文化歷史、民族性格的結構特征與現實生存狀態的影片[1],開創了中國西部片的先河。
西部電影拓寬了民族電影的創作視域與境界,提供了新的電影審美形式與層次。西部電影在精神文化的表現上,無一例外地表現了西部人的性格特征、情感方式以及風俗民情中的那些真、善、美,同時也展示了西北人受地理、歷史和文化的影響而導致的愚昧、麻木和保守,這樣的電影表現或再現是對民族性格與民族命運的反思。西部電影立足本土,注重挖掘民族性的文化特征,拓展歷史性的人文視野,對西部地域文化充滿深切的人文關懷。概而言之,西部電影呈現了獨具韻味的空間美、基于深厚歷史文化下的悲劇美以及現實主義美學風格下的真樸美,其主流特征即堅守紀實風格并塑造典型的中低層人物形象來表達創作者對于民族性格、民族命運的體悟,并揭示民族內在文化的原動力。
不同的導演因其個人生活的時代背景、經歷及體驗、性格、價值觀、藝術審美不同,其作品往往都有獨特的個人藝術風格。吳天明作為土生土長的陜西人,有特殊的西北黃土地生活和感情經歷、個人體驗,他的個人藝術經驗源于苦難、憂患和悲憫。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先后創作了《人生》《老井》《變臉》等經典電影,無一例外都選擇了極具西部意象的黃土地、西北民俗、農耕文明等視覺呈現元素,開創了中國西部電影的先河。他的西部電影始終堅持關注社會現實,關注在苦難中與命運抗爭的人,保持著悲天憫人的人文主義情懷,影片呈現了強烈的憂患意識、苦難中敢于與命運抗爭的精神,其作品有著濃厚的悲劇美學意蘊,這些都構成了吳天明的西部電影風格。《百鳥朝鳳》正是這種西部電影風格的延續與堅守。
二、《百鳥朝鳳》中的“西部電影”視覺呈現元素
影片中,那三秦大地上巍峨粗獷的黃土高坡,那略顯破敗卻頗具地方特色的村鎮,那濃縮著千年文化積淀的民俗禮儀、婚喪嫁娶,那金色的麥田和綠油油的菜地等,使得影片散發出一股久違了的揮之不去的厚重的鄉土氣息與質樸。
對西北黃土地的偏愛。吳天明對大西北自然地理環境的險惡有著切身的刻骨體驗,對西北人生存的艱難始終擔憂,這種個人獨特的體驗為其電影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讓他更擅長表現或再現以黃土地為敘事背景的故事,用鏡頭注視著這片土地上生活、掙扎著的人們,這畢竟是他熟悉的故土。從《人生》《老井》到遺作《百鳥朝鳳》,無一例外吳天明均以黃土地作為視覺呈現元素。小說《百鳥朝鳳》原本寫的是肖江虹老家貴州修文的故事,吳天明則把小說故事發生地移植到自己的家鄉陜西。影片中,當鏡頭緩緩推開西北山水時,黃土地那么粗獷蒼涼,又那么厚重踏實。在天鳴父親帶其拜師途中,影片一再再現了八百里秦川的壯觀。師傅焦三爺為了讓徒弟們更好地傳承嗩吶這一傳統民間音樂技藝,在黃河岸邊讓徒弟們用一根長長的蘆葦桿從河里吸出水以鍛煉他們的氣力。而結尾處,徒弟天鳴在師傅墳前吹起《百鳥朝鳳》這一象征著逝者德高望重的嗩吶古曲。黃土地這一厚重而悠遠的底色奠定了電影的主基調——一種對傳統民間技藝、傳統文化逐漸式微的憂患意識,一種對歷史與現實詩意化的懷念與擔憂。吳天明最擅長表現關于黃土地的故事與人物,因為他生于斯長于斯,深深眷戀黃土地,始終關注大西北人的生存與發展,這種深沉的愛融入到其藝術創作中,就呈現了一種強烈的悲劇美,一種對苦難的哀思。
對農耕文明的深厚感情。黃河流域是我國農耕文明的發源地,吳天明生于陜西農村,上山下鄉期間又回到農村,來自農民,理解農民,始終關注中國土地上沉默的大多數,對農耕文明有特別情緣,即使當前農村題材的電影很難有市場,依然堅持拍攝《百鳥朝鳳》。《百鳥朝鳳》講述陜西農村無雙鎮的焦三爺傳承嗩吶技藝的故事。曾經吹嗩吶既是紅白喜事婚喪嫁娶中不可或缺的一項內容,嗩吶藝人深受老百姓的喜愛與尊敬,在無雙鎮,吹嗩吶絕不止于娛樂,而被賦予了更深的意味,成為對逝者的一種人生評價——道德平庸者只吹兩臺,中等的吹四臺,上等者吹八臺,德高望重者才有資格吹“百鳥朝鳳”。影片中查村長去世,嗩吶王焦三爺認為他為人無德,拒絕在其葬禮上吹奏《百鳥朝鳳》,因其當村長期間將其他四姓人擠走,只剩查姓。而當竇村長去世后,焦三爺認為他是有德之人,親自為其吹奏《百鳥朝鳳》這一象征死者德高望重的古曲,甚至吹到吐血,因其抗日期間打過鬼子,帶領村民修過水利。社會轉型巨變之時,面對西洋流行樂的沖擊,嗩吶日漸式微,小說中天鳴漸漸發現嗩吶與當下社會脫節,人心離散,出外打工。最后,連師父焦三爺也進城為徒弟藍玉的工廠看門。而影片中,吹奏嗩吶難以維持生計,當徒弟們紛紛向現實的生活妥協要進城打工時,三爺倔強地打了一頓想進城的徒弟。焦三爺拖著病體最后一次吹“百鳥朝鳳”,自己則吹嗩吶吹到泣血后。天鳴依然堅守吹嗩吶,只因師傅選他作嗩吶接班人時,他向師傅承諾過會把無雙鎮的嗩吶擔起來,傳下去。雖然焦三爺們老了、沒了,但“匠人”的精、氣、神還在,“匠人”的魂兒還在,匠心匠德還深深植根在農村。
具有精神指向的西北民俗。1980年代,“尋根文學”“傷痕文學”為電影創作提供了以傳統民俗為表現或再現對象的思路。第四代導演深入到蘊含豐富風俗民情的農村去尋找創作靈感。吳天明因其得天獨厚的西北地緣親近感,電影創作中呈現了豐富多彩的西北民俗風情奇觀。電影《百鳥朝鳳》中,運用傳統婚喪禮當中豐富多彩的具有象征性的嗩吶曲、寫意性的場景,以及嗩吶接班人培養過程中焦三爺選擇嗩吶接班人不只看天賦、后天努力,更看重人品德行,最終放棄天賦和技藝更好的藍玉,而選擇了德行好的天鳴,這種傳承與堅守的民俗具有精神指向性。影片結尾,天鳴獨自佇立在焦三爺墳前,用那把泣血的嗩吶吹出“百鳥朝鳳”,恍惚中,仿佛師傅就坐在半空中仔細聆聽,臨近曲終,師傅從太師椅上起身,頭也不回地緩緩地消失在嗩吶聲中。這組畫面對嗩吶這一民俗的美妙又蒼涼的再現,表達了吳天明對傳統民間技藝日漸式微的深切憂患。電影《百鳥朝鳳》對西北民俗的再現,不只豐富電影的表現元素,還通過民俗意象表達創作者對民族、文化的思考和反思,有利于中國電影本土化民族特色風格的形成。
在中國鄉土文化的表達上,吳天明無疑是最充分的一個。他的西部電影對黃土地、農耕文、西北民俗等的表現或再現,大西北那蒼涼而貧瘠的黃土地、古樸的農耕文明、豐富的風土人情都使得影片的視覺呈現更具沖擊力,讓人們透過社會表象來思考傳統文化在現代文明沖擊下的逐漸式微,這種新舊文化的沖突構成電影的美學內核,影片有凝重的悲劇美學意蘊。
三、新舊文化沖突的悲劇美學意蘊
悲劇美學是西方美學體系中的一種獨立的審美形式,在文學、音樂、繪畫、話劇、電影中被廣泛運用,通過藝術作品內在的矛盾沖突表現美,產生神圣而崇高的藝術效果,引發人們的思考、同情和共鳴。吳天明在《人生》中刻畫人與社會現實之間的沖突,在《老井》中刻畫人與惡劣的自然環境之間的沖突,在《百鳥朝鳳》中刻畫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之間的沖突,這種沖突構成了其電影的悲劇美學內核。
電影《百鳥朝鳳》通過表現社會轉型巨變中,在中國農村社會日漸變遷和裂解,傳統鄉村社會原有的禮俗與秩序逐步解體的背景下,嗩吶這一傳統民間技藝在現代化的擠壓下在傳承與堅守過程中面臨的困境,展示了現代社會中傳統民間文化所陷入的窘境,這種新舊文化之間的矛盾沖突構成電影的悲劇美學意蘊。影片關注民間藝術日漸式微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呈現出了身為文化傳承者們所面臨的困局與無奈。
影片中,西洋交響樂作為大眾流行文化的象征,席卷了大西北閉塞、落后的農村,帶給農民不一樣的新奇體驗,更易進入尋常百姓家,流行交響樂替代了嗩吶在村里流行開來,讓村里的年輕人開始浮躁,不再看重傳統的婚喪嫁娶等傳統儀式,因此,傳統的嗩吶班難以維持基本的生存,他們紛紛進城打工。而影片中無雙鎮的嗩吶王焦三爺始終視嗩吶技藝為生命,堅守著嗩吶技藝,想讓嗩吶班代代傳承。《百鳥朝鳳》表面上看是講嗩吶傳統民間技藝的傳承中的困境,本質上是表達了對鄉土倫理及中國傳統文化逐漸式微的深切的憂患意識,而這種新舊文化的沖突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人力無可奈何,這正是悲劇的沖突,讓吳天明的電影有著崇高的悲劇美。吳天明對傳統民間文化是極力挽留的,用一種近乎悲壯的方式來保持傳統文化的尊嚴。吳天明顯然對焦三爺這樣固守傳統民間技藝所秉承的藝術態度是肯定的。在娛樂化的電影市場里,吳天明堅持開拍,為傳統民間文化發聲,突顯了強烈的人文情懷。當結尾處,渾厚的黃土地上,響起悲愴的古曲《百鳥朝鳳》,是致敬有堅守的民間藝人,也是致敬真誠獻身藝術的人。這種悲愴讓人感慨,引發內心的震動,這就是悲劇產生的力量。焦三爺作為悲劇人物的縮影,體現了人的欲求與現實社會之間的矛盾,面對困境,有作為“人”的堅守,勇于同命運抗爭,抗爭精神讓人心靈震撼,更加凸顯了悲愴美。吳天明的悲劇意識源于他對藝術、黃土地及西北人的深沉的愛,強烈的紀實風格使其作品極具悲劇美感。
導演吳天明生前不止一次表示,電影《百鳥朝鳳》是他的感懷言志之作,影片中焦三爺說“嗩吶不是吹給別人聽的,是吹給自己聽的”,這也是吳天明對電影藝術的態度。
[1]何春耕.中西電影文化的一種表征——西部片《關山飛波》和《雙旗鎮刀客》審美特征比較[J].唐都學刊,2004,20(1):59-63.
王海紅,女,河南安陽人,鄭州工商學院講師,主要從事中國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