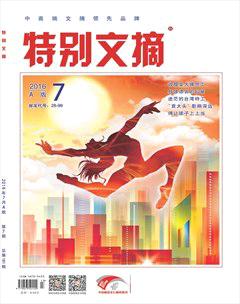“爺”的變遷
鄭也夫
“爺”自古就是口語中流行的字眼。在書面語言中其最初的意思是“父親”。北朝樂府《木蘭詩》中“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中的“爺”即指木蘭的父親,但在以后的口語中它更多地意指“祖父”。據清人趙翼考證,自唐朝始,從“爺”中引申出了尊人之稱的意思。以后這一尊稱的應用越來越廣。王爺、老爺、少爺、駙馬爺——有地位的男性最先被戴上“爺”的冠冕。繼之,宗教和神話中的神祇也被奉之為“爺”:佛爺、龍王爺、土地爺、財神爺、灶王爺。社會上的一般性尊稱也要努力借上這個字眼,原本指父親和祖父的“爺”,被人借用到客氣的稱呼上。走進老北京的澡堂子,你會聽到跑堂的殷勤地招呼:“爺兒們,里頭請。”“爺兒們”是市井社會中對陌生男子最流行的客氣稱謂。農村中若在大庭廣眾下講幾句話,開場的稱呼往往是“老少爺兒們”。遇上某位天不怕地不怕的漢子,周圍人多稱之“魯爺兒們”。下層社會中男性間發生沖突時,常有人拍著胸脯以“大爺”自稱,借此拔高以顯示高人一籌的氣派。江湖好漢間更流行著這樣的豪言壯語:“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爺”真有點頂天立地的派頭。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特定的歷史時期中,這句俗話后面又被添補了兩句:“處處不留爺,爺去當八路。”在當時“爺”與“八路”都給人以“好漢”“桀驁不馴”之感。然而那個時代的人們無論如何不會想到,八路最終是最不留爺的,恰恰是在革命勝利后,“爺”逐漸從語言和社會中消失了。
1949年以后,首先是平等的價值觀掃蕩掉了富貴者的尊嚴,“老爺”“王爺”“少爺”通通從語言中被鏟除。接著,無神論破迷信的活動趕走了“龍王爺”“財神爺”“土地爺”“灶王爺”。其后發展起來的社會滅絕了“大爺”的存在基礎。它不能容忍社會上有無數自命“大爺”的人存在。在這眾多帶“爺”的字眼消失后,上年歲的人掛在嘴上的“爺兒們”怕是“爺”的最后一縷余韻了。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自20世紀70年代末,在社會語言中“爺”又復活了。在一些新起的“爺”中,最紅的兩個角色是“倒爺”和“侃爺”。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一種社會現象已經在社會語言中凝固成了一個專用名稱時,這一現象必然是頗不一般了。“倒爺”和“侃爺”的稱呼幾乎風靡全國,也正與社會上“倒”和“侃”兩大風氣的流行相一致。但“倒”與“侃”卻并不相干,何以都掛鉤于“爺”,其共性何在?顯然,“倒爺”和“侃爺”中的“爺”都含有能干的意思,即不僅指常“倒”、常“侃”的人,更指“能倒”“能侃”的人。但對“能者”,漢語是不乏慣用表達方式的。“木匠”“工匠”“文字巨匠”中的“匠”均為“能者”之意。不選擇其他字眼,偏偏選中了“爺”,這意味著倒爺、侃爺的興起及這種稱謂的出現說明著個性的復活。倒爺是敢作敢為的,自不待言,侃爺大多也是頗有棱角的。官方將個體商販稱為“投機倒把者”,而大眾在語言上顯然不像官方這樣刻薄、極端,他們寧愿選擇一個玩世不恭、略帶嬉笑、主流上屬中性的詞匯。大眾畢竟與“倒爺”共生在一個社會中,他們即使對倒爺有幾分厭惡,卻也知道倒爺的必要性,他們不使用“投機倒把者”的稱呼說明了他們不想對這種角色大加討伐。社會語言上“倒爺”對“投機倒把者”的取代顯示了中國民眾的平和、幽默和寬容。
(摘自《語鏡子》中信出版社 圖/游飛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