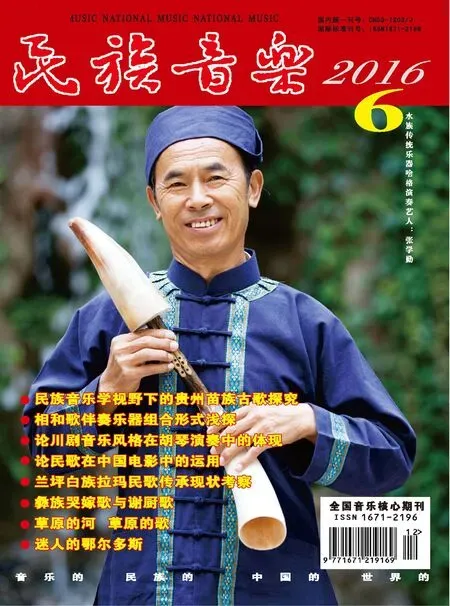民族音樂學視野下的貴州苗族古歌探究
■王建朝 單曉杰(貴州凱里學院音樂學)
民族音樂學視野下的貴州苗族古歌探究
■王建朝 單曉杰(貴州凱里學院音樂學)

所謂“苗族酒歌”,苗語稱為“夏婁夏告”,是指“以口傳心記為傳承手段,以全體民族為傳承載體,以盤問對唱為媒介的集苗族世界觀、社會觀、宗教觀、倫理觀、價值觀、法制觀、審美觀和編年史為一體的大百科全書——包括‘開天辟地’、‘鑄日造月’、‘蝴蝶媽媽’、‘洪水滔天’和‘跋山涉水’五部分內容的苗族創世史詩和以詩史為核心形成的包括文學藝術、宗教信仰、節日集會、風俗習慣等文化事象的具有空間同一、整體涵蓋特征的苗族非物質活態文化體系”①。據調查,苗族古歌主要在貴州省臺江縣及其周邊的雷山、榕江、施秉、黃平、凱里和鎮遠等地區廣泛流傳。可能正是基于苗族古歌之包羅萬象的綜合性,學界對其研究則體現出多元性和多學科性。綜觀其研究文獻,多學科的學者們主要從文學、語言學、美學意蘊和審美、倫理道德、哲學思想、民俗背景、生態意識、價值取向、社會文化功能、當代變遷、傳承與保護、演唱方法等角度對其進行多個層面的探研,且體現出宏觀敘事的趨向和特征,而運用民族音樂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其進行縱深的研究者則較為鮮見。基于苗族古歌的定義可以發現,苗族古歌不僅僅是一種集苗族民俗、文學、歷史、宗教等于一體的大型的綜合文化形式,而且是一種苗族群之至關重要的音樂表演藝術形式,與其民俗、歷史等文化背景有著密切的依附共生的關系,且在苗族民眾生活中發揮著民俗、族群認同、文化知識傳遞、經濟、交際、娛樂、審美等多樣性的社會文化功能。同時,我們通過田野調查還發現,苗族古歌演唱是承載苗族傳統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和手段,傳統社會中的很多苗族民眾主要是通過苗族古歌的演唱來獲得族群文化知識的,是其族群文化認同的重要文化符號。運用民族音樂學的理論和方法對苗族古歌進行多個層面的研究,既能夠更大程度上發掘苗族古歌之前所未及的知識盲點,也能夠將研究的觸角引向深層次。
資料搜集及其方法
眾所周知,田野工作既是民族音樂學的靈魂,也是該學科安身立命的法寶,還是搜集田野資料的重要途徑和方法。就學科研究方法和資料搜集而言,除了搜集和閱讀靜態的、文本的文獻資料外,民族音樂學家主要通過進入其研究對象的生存地點,采用訪談法(個人訪談和集體訪談)、參與觀察法、居住體驗法、跟蹤攝錄法等方法在田野中收集與研究對象相關的第一手的資料。在資料搜集過程中,尤其重要的是:研究者要與活態的被研究者進行面對面的直接接觸,既參與體驗其活態的表演活動,也通過訪談記錄其歷史記憶,來獲得歷史和當下之雙重的研究資料,以此為我們后期的民族志的文本書寫積累珍貴的研究資料。苗族古歌是從古至今一以貫之地流傳在苗族群之社會民俗生活中的文化藝術種類,用歷代古歌藝人演唱的形式承載了苗族的歷史文化傳統,維系了該族群的延綿存續。因此,運用民族音樂學之田野調查的諸種方法對苗族古歌進行文字、表演實踐、口述史、圖像、實物等多方面資料的搜集,能夠為其民族音樂學視野的縱深研究提供更加翔實的第一手資料,不但拓展了苗族古歌的研究范圍,而且加深了其研究內容的深入化程度。
研究內容的拓展
有關貴州苗族古歌的研究內容,除了上述所列范疇之外,運用民族音樂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其進行重新審視,由于研究資料的充實和研究角度的多元化,能夠極大地拓展苗族古歌的研究范圍,增加其知識量。此點無疑彰顯出研究資料和研究方法對學術研究拓展的重要性。就研究內容來看,運用民族音樂學的理論和方法對貴州苗族古歌進行綜合審視,其研究內容主要包括貴州苗族古歌的文化背景、局內人的音樂思想和音樂行為、實用功能、運行機制、音樂本體形態及其與唱詞格律的關系、與其他苗族傳統音樂的關系、區域性差異、變遷軌跡、與苗族族群之現實社會生活的關系、傳承和傳播途徑、藝人傳記及其文化身份建構、個案民族志、多點民族志和文化隱喻等方面,且每個方面一般可以獨立成文或多個方面相互結合形成綜合性的學術著作或學位論文,為其他音樂種類的研究提供參考和借鑒。可以說,這些研究內容都是苗族古歌的以往研究中無人涉及或者很少涉及的范疇。如果我們音樂學者能夠運用民族音樂學的理論和方法對上述內容進行多個層面的深入分析研究,并撰寫相關學術成果,苗族古歌這一“文化富礦”一定能夠被發掘出更多、更加珍貴的文化瑰寶。因此,筆者認為,我們音樂學者應該義不容辭地承擔起充分發掘貴州苗族古歌之文化含量的責任和義務,進而為苗族古歌的發揚光大做出應有的貢獻。
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
在學術研究中,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的合理擬定至關重要。只有擬定了合理、有序、科學的研究思路,課題研究進程才能夠按照預設的路徑循序漸進地有效開展,而避免研究過程中雜亂無序的弊端,并且能夠顯現課題研究的整個過程。可以說,這是當前的學術研究之科學性的重要體現。就本文的研究對象來看,結合貴州苗族古歌的生存形態,根據民族音樂學的研究路徑,筆者覺得采取以下思路進行系統的研究較為恰當。
(一)文化背景的考察與認知
一方面,通過查閱各類文獻資料,對貴州歷史上存在苗族古歌的地區的民族、民俗、宗教、歷史等發展、變遷的狀況進行了解和分析。另一方面,通過田野調查對現存苗族古歌的地區的自然生態、民族、民俗、宗教等概況進行實踐考察。力爭在歷史與現實的對比中,探尋苗族古歌之生存背景的發展與變遷軌跡,從而為苗族古歌的文化變遷研究提供有效依據。
(二)前期研究成果的整理和分析
通過互聯網、圖書館等信息渠道,對業已研究的相關苗族古歌的各類成果進行搜集、整理和分析,了解學界對其研究的現狀,明確其研究方向,奠定其研究基礎。
(三)田野調查及資料收集
定期對貴州省臺江縣及其周邊的雷山、榕江、施秉、黃平、凱里和鎮遠等地區的苗族古歌進行深入的田野調查。運用民族音樂學田野調查之居住體驗、參與觀察和直接訪談的方法,以“局內人之主位觀—局外人之客位觀”的雙重研究視角,對各地區苗族古歌的傳承人、傳承方式、表演過程、文化功能、運行機制乃至其與生存背景之間的互動關系等方面進行全方位的調查,并收集相關實物、音像、文本和局內人的口述史等資料。
尤其重要的是:研究者要與傳承人一起參與到苗族酒歌表演實踐的全過程,體驗其活態存在,洞察其在苗族人的各類社會活動中扮演何種角色以及發揮何種功能。另外,還要把傳承人的各類表演活動進行全程錄制,以此來為我們的音樂民族志個案書寫提供實錄文本。
可以說,“將音樂置于社會語境(上下文)中進行整體跟蹤記錄”的做法是當今音樂人類學研究所極力倡導的,鮮明地體現了美國著名音樂人類學家阿蘭·梅利亞姆所謂的“文化中音樂研究”和內特爾所謂的“文化語境中的音樂研究”的研究理念。此為本論題研究的基本思路。
(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結合文獻資料,綜合運用“局內人”之“主位觀”和“局外人”之“客位觀”的雙重視角對田野調查資料進行整理和分析,從而圍繞苗族古歌與文化背景之間的互動關系、苗族古歌的音樂形態、文化功能、不同地區的苗族古歌之異同比較及苗族古歌與其他苗族傳統音樂之間的關系等內容進行多個層面的分析和研究。
(五)案頭寫作
在田野調查體驗和資料分析的基礎上,按照論題階段性成果的計劃和要求,撰寫相關學術成果。在寫作過程中,我們將美國著名音樂人類學家蒂莫西·賴斯的音樂人類學研究模式——“歷史構成、社會維護、個人創造與體驗”和“時間、地點、隱喻”與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茲的闡釋人類學之文化“深描”的理論與方法相結合,將各種文獻資料、口述史資料、田野調查資料、個人實踐體驗相結合,將歷時性認知與共時性比較相結合,從而形成我們所預設的各種音樂民族志文本。
民族音樂學視野下的貴州苗族古歌音樂文化書寫
眾所周知,任何研究成果的呈現均是以文本的書寫來實現的,音樂也不例外。那么,作為一名民族音樂學學者,他應該怎樣對其研究對象——貴州苗族古歌進行民族音樂學視野的書寫呢?我們認為,民族音樂學的文本(即音樂民族志)書寫方式是多元化的,不應該強調千篇一律。那么,筆者認為,根據貴州苗族古歌的研究內容和問題意識的不同,應該采取宏大敘事(宏大理論)、個案描述和闡釋(即強調地方性知識)以及兩者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書寫較為合宜。譬如,有關貴州苗族古歌之音樂本體形態特征、變遷軌跡、實用功能等問題的研究,我們認為采用宏大敘事、總結規律的方式進行書寫較為合適,如此可以揭示其共性特征。而具體表演場域的個案音樂民族志、藝人傳記等內容的書寫應該采用個案描述和闡釋的方法,如此才能夠將研究對象置于具體的文化語境中進行“深描”,充分展現其文化內涵和意義。另外,一些綜合問題的研究應該采用宏大敘事和個案描述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書寫,如多點音樂民族志中的比較研究等,這樣才能做到宏觀和微觀的相互融合,充分挖掘出研究對象之深層次的文化隱喻。
在書寫過程中的問題分析方面,筆者贊成運用“局內人之主位觀和局外人之客位觀”的雙重視角進行問題的分析和闡釋,并輔以歷時和共時的雙重視野來審視研究對象,以達到全面理解其文化內涵和意義的目的。在表述風格方面,筆者贊同音樂學者楊民康“對位表述”②和“換位表述”的方式,也就是“在描寫或敘事過程中保持了第一、第三人稱角色,同時也盡可能尋找機會置入適用于研究對象的另一種第三(或第一)人稱角色,以產生和構成‘主位—客位’‘局內—局外’雙方話語‘對話’的條件”③。如此書寫的效果是:對于書寫者而言,“既盡力使其具‘權威’身份的語氣口吻還原為普通人(例如經常采用‘我[或某人]如何如何’)的語氣口吻,同時也不失時機地去闡述自己尋找局內人角色的種種感受及體驗過程”④。因此,該種表述風格兼容并蓄了“局內—局外”的雙重觀點,在貴州苗族古歌的書寫過程中尤其應該值得提倡。另外,所謂“換位表述”,闡釋人類學認為,通過了解“土著觀點”來解釋象征體系對人的觀念和社會生活的界說⑤。關于此,楊民康先生指出:“換位表述”也涉及到“通過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局內—局外’‘主位—客位’互動,而達到對地方性知識的獨特世界觀、人觀和社會背景(亦即‘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予以理解的目的”⑥。因此,筆者認為,“換位表述”的風格可以用于貴州苗族古歌之文化隱喻和符號象征部分的書寫,以到文化“深描”的目的。
總之,在文本的書寫方面,我們應該根據貴州苗族古歌的研究內容和問題意識的具體情況,靈活地采取宏大敘事或個案描述和闡釋的書寫方式,同時,在表述風格方面,根據苗族古歌的存在形態以及研究者的研究目的,采用“對位表述”和“換位表述”的表述風格來書寫貴州苗族古歌文化能夠達到深入闡釋問題的目的。
結 語
綜上所述,伴隨著20世紀80年代西方民族音樂學學科理論和方法引入我國音樂學界,我國傳統音樂尤其是少數民族音樂的研究理論受到很大的沖擊,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新生成果如雨后春筍般紛紛涌現,大大豐富了我國傳統音樂文化研究的知識量,作為我國少數民族音樂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貴州苗族古歌研究也不應該被排斥在外。然而,由于種種原因,盡管貴州苗族古歌所包容的文化含量異常宏闊,學界各學科學者也都根據其研究所長而從不同角度來審視苗族古歌,并產生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是卻極為缺乏民族音樂學視野中的研究成果,此之于苗族古歌之包羅萬象的文化含量而言著實不可匹配。本文試圖運用民族音樂學的理論和方法來對貴州苗族古歌這一研究對象進行多個層面的綜合審視,擴展了其研究內容的范疇,明確和規范了其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尤其是為貴州苗族古歌之民族音樂學視野下的文本書寫提供了可供參考的思路。該種做法不但能夠大大增加貴州苗族古歌研究的知識量,也能夠將其研究程度引向深入化的層次。因此,筆者認為,民族音樂學視野下的貴州苗族古歌研究將是其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
注 釋:
① 單曉杰,王建朝.論貴州苗族古歌的當代生存形態[J].凱里學院學報,2013(4):26.
②“對位表述”即指“主位—客位”的關系,也含有時下人類學家借用音樂名詞“對位法”來比喻這種關系的意思。
③陳銘道.書寫民族音樂文化[M].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0:9.
④陳銘道.書寫民族音樂文化[M].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0:9.
⑤克利福德·格爾茲.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C].王海龍,張家瑄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70.
⑥陳銘道.書寫民族音樂文化[M].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0:10.
本文受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貴州省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口述史研究”(項目編號:16YJC760010)、2016年度貴州省教育廳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貴州省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口述史研究”(項目編號:2016zd05)、2016年度凱里學院苗族侗族文化傳承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專項課題一般課題“文化人類學視域中的黔東南苗族酒歌研究”(項目編號:XTYB1635)、2014年度凱里學院校級重點學科“音樂與舞蹈學”項目 (項目編號:KZD2014010)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