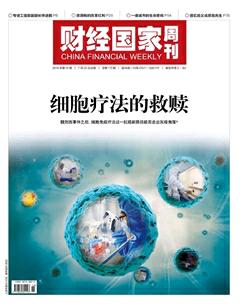醫療新技術監管難題
張曙霞
細胞免疫治療在國內處境尷尬,既不屬于藥物,也不屬于放開的第三類醫療技術,在臨床研究和應用方面的監管無據可依。
7月13日,CAR-T領軍企業Juno Therapeutics宣布,美國FDA批準其腫瘤免疫療法JCAR015的二期臨床試驗可以繼續進行。
而就在5天前,因兩名患者出現腦水腫死亡,這項臨床試驗被FDA叫停。JCAR015原本有望2017年上市,叫停事件當時讓不少業內人士懷疑該藥物的上市計劃將被無限推遲。
但不到一周的時間,劇情即出現反轉。在FDA的快速批準下,JCAR015或能如期上市。
“意料之中,FDA這么快就批準Juno恢復臨床試驗,值得國內同行認真學習,對出現的問題應當堅持理性分析。”上海細胞治療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錢其軍在微信朋友圈如是評論。

魏則西事件后,國家衛計委緊急叫停了細胞免疫治療的臨床應用。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兩個多月前的魏則西事件。青年魏則西之死,將細胞免疫治療領域的亂象一一揭開,國家衛計委也因此緊急叫停細胞免疫治療臨床應用,并規定僅限于臨床研究。
但《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在調研中發現,不僅臨床應用全面停止,而且由于管理規范、行業標準的缺失,沒有職能部門愿意接受備案材料,大部分臨床研究項目也受波及被迫中斷。
此前在干細胞、基因測序等醫療新技術領域都曾出現過類似情況。監管能力如跟不上技術發展的節奏,往往會出現亂一個就叫停一片的情形。
而在混亂與規范的時間差中,新技術喪失的發展機會和空間難以估量。
多位受訪專家和企業人士表示,當務之急是建立細胞免疫治療臨床研究和應用規范體系,引導行業走上規范化軌道。
針對《財經國家周刊》提出的未來監管方向等問題,國家衛計委回復:將繼續要求醫療機構提高依法執業意識,加強醫療技術臨床應用管理,同時依法依規開展醫療技術的臨床研究工作。
“最近,國家衛計委和食藥監總局都在咨詢相關領域專家,對細胞免疫治療到底是按新藥研發還是醫療技術監管,尚未達成共識。”有業內人士透露。
執行層面“擴大化”
魏則西事件之后,國家衛計委召開規范醫療機構科室管理和醫療技術管理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叫停細胞免疫治療的臨床應用,但臨床研究可繼續。
北科生物總裁劉沐蕓認為,此舉有助于整肅亂象、凈化市場,讓缺乏核心技術支撐、沒有切實療效的細胞免疫療法徹底退出,也淘汰一批違規、技術能力低下的公司。與此同時,給真正開展細胞治療研發和臨床試驗的企業帶來機會。
然而,在政策落地方面,卻有所偏差。
“一些地方政府或醫院從嚴管理,將正在開展的細胞免疫治療的臨床研究也暫停了。”錢其軍說,雖然國家衛計委叫停的只是臨床應用,但在執行層面“擴大化”。
多家企業人士表示,一個原因在于國家層面的監管細則尚未出臺,地方主管部門就會無據可尋,于是干脆拒絕接受臨床試驗備案,醫院院長也不敢冒險擔責,怕一不小心踩到“紅線”。據業內人士介紹,目前,除解放軍301醫院等少數幾家單位還在進行,全國大部分臨床研究都出于中斷狀態。
按相關規定,臨床研究只要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醫療技術管理委員會通過就可以進行了,但需要將臨床研究的方案送到衛生主管部門報備。
“曾經迅速發展的臨床試驗勢頭受挫。”博生吉醫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林表示,不僅是較為落伍的CIK、DC-CIK技術廣受影響,主流的CAR-T和TCR-T治療技術也在一段時間內受到牽連。
不少企業和醫院都在與衛生管理部門溝通,希望臨床試驗盡快重啟。安科生物董秘姚建平預計,不會有太長時間有進展了。
與此同時,一些單位通過聯合多家醫院共同申報科研項目,以臨床研究課題立項的方式來通過科研倫理,從而獲得少量的臨床試驗機會。“當然這只是監管規范尚未出臺情況下的權宜之計。”楊林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有專家認為,即便對于臨床應用,“一刀切”全部叫停的舉措是否很科學很合理也需要研究。“對常規治療手段失敗、無藥可選的腫瘤晚期病人來說,細胞免疫療法是最后的希望,治療需求一直存在,要科學對待、科學疏導。”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普外科副主任醫師龔渭華表示。
楊林介紹,其實有些治療方案已在前期應用中顯示了療效,例如,在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和急性髓系白血病方面,部分單位通過CIK免疫細胞聯合化療取得了明顯的治療效果。
龔渭華建議,可以暫時先批幾家試點,并嚴格規范臨床治療流程,建立病人數據庫并通過跟蹤回訪、對照組試驗等方式評估療效。
“不能因一起事件,把腫瘤免疫治療技術弄黃了,讓國內錯失可能在癌癥治療領域彎道超車的機會。”錢其軍說。
監管體系缺失
很長一段時間,細胞免疫治療在國內處境尷尬,既不屬于藥物,又不屬于放開的第三類醫療技術,在臨床研究和應用方面的監管均無據可依。
回顧細胞免疫治療的監管歷程,有三個重要節點,分別是2005年、2009年和2015年。
在2005年之前,細胞免疫治療監管權歸屬原國家食藥監局,基本按照藥品管理模式監管。2003年,食藥監局發布《人體細胞治療研究和制劑質量控制技術指導原則》,從體細胞采集、分離和檢定、體細胞的體外操作、體細胞制劑的檢定與質量控制、體細胞治療的臨床前試驗、臨床試驗方案等八方面做出詳細規定。
公開報道顯示,當時全國有5家醫院開展臨床試驗,參與臨床的患者均免費治療,做免疫治療的醫生認為“這是監管最好的時期”。
2005年食藥監局發生人事地震,不再受理生物療法申報。隨后的年底,免疫治療管轄權轉到原衛生部,細胞技術從藥品管理變軌為臨床技術管理。其后4年,沒有相關管理辦法出臺。由于暴利吸引,一些醫院和生物公司都紛紛參與,缺乏規范標準和監管的市場極為混亂。
在魏則西事件中被聲討的上海柯萊遜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就成立于2007年,短短幾年為國內30多家醫院提供細胞免疫治療技術服務,業務遍布全國20多個省市,2015年凈利潤高達4000萬元。
2009年,原衛生部公布《首批允許臨床應用的第三類醫療技術目錄》,“自體免疫細胞(T細胞、NK細胞)治療技術”被納入其中,允許開展臨床應用,衛生行政部門負責審批。
為規范相關技術的臨床應用,保證醫療質量和安全,原衛生部制定了《自體免疫細胞(T細胞、NK細胞)治療技術管理規范(征求意見稿)》,對開展臨床應用的醫院資格、自體免疫細胞制劑的制備、產品標準進行了規定。而該征求意見稿未見后文,公開資料中也沒有發現有醫療機構經衛生部門批準開展細胞免疫治療臨床應用。盡管如此,這項沒有經過安全性和有效性認定的療法依然在成百上千家醫院鋪開。
2015年7月,國家衛計委下發通知,取消第三類醫療技術臨床應用準入審批,并發布《限制臨床應用的醫療技術(2015版)》目錄。細胞免疫治療未被列入該目錄,故被視為只能開展臨床研究。
但只要沒有被明確禁止,“各個地方和單位形成了有利于自己的解讀,細胞治療得到了更大但缺乏嚴格監管的發展。”安科生物董秘姚建平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而且,臨床研究到底該如何開展,相關標準和流程一直是空白,是故,細胞免疫療法游走于灰色地帶。
業內人士曾嘗試建立規范體系。據了解,2009年中國科學院院士曾益新聯合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中國科技大學等四家單位,開展了包括細胞制備、細胞培養功能、細胞回收和回收后的臨床評估四大環節的標準研究和制定,并于2013年底提交給國家衛計委。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致電曾益新詢問該項目進展,曾院士表示“現在不適合回答”。有熟悉情況的專家說,提交后沒有下文。
魏則西事件后,國家衛計委要求,各級衛生計生行政部門“全面清理違規開展醫療技術臨床應用的情況”。5月底,國家衛計委副主任劉謙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將根據新技術臨床研究的規律和特點,制定并下發醫療新技術臨床研究管理辦法。至于管理辦法進展如何,國家衛計委在給《財經國家周刊》的回復中未說明。
“互動式監管”
“建立規范化的研發和應用環境不是一天兩天的事,需要多方協作。”哈佛大學醫學院蔡冬坡博士說,現在關鍵問題是最起碼的共識尚未達成:到底是按藥品還是醫療技術監管?
按照國內醫療監管體系,藥品審批是食藥監部門的職責,醫療技術則歸屬衛生行政部門監管。蔡冬坡認為,誰來監管不重要,重要的是監管內容是否到位,監管者是否中立。
出現分歧與大環境有關。“如果按照藥品管理,需要企業起到關鍵作用。”楊林表示,與國際上主要靠企業推動發展不同,國內在技術開發上唱主角的是醫院,即醫院自主研發、開展臨床研究,而由于醫院本身體制局限性,他們較少考慮產業化和標準化的問題。
楊林認為,真正健康的產業環境,是大學、研究所主要負責技術研發;企業通過收購、自主研發等途徑將新技術產業化,并在食藥監部門的監管下以新藥模式開展臨床試驗;醫院則承擔起臨床試驗研究的重任。
除醫療環境的束縛外,與藥品或常規生物制品有所不同,細胞免疫治療用到的是個體化“活”細胞,監管工作具有內在復雜性。錢其軍介紹,一是難以標準化,二是進入人體后具有自主性和自適應能力,不易定量,三是最終放行檢驗的時間窗口很短,難以完成常規生物制品所需要的檢驗。
而且,由于此前國內細胞治療主要模式是醫院自建或聯合企業共建實驗室,技術成熟度、人員專業水平、質量控制體系都缺乏保證,監管難度很大。
“任何新技術的突破都會走在政策前面。”錢其軍表示,在這種情況下,監管部門和創新主體之間互動協作的關系非常重要。而目前國內的情況是,一項新技術出現并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監管部門要求創新主體向其匯報,根據匯報情況決定如何監管,互相之間的討論和反饋機制尚待完善,是一種“匯報式”監管。
相比起來,發達國家的“互動式監管”值得國內借鑒。
“互動式監管”理念在Juno近期經歷的叫停事件中得到了完整呈現。據了解,在第一例死亡病例出現后,Juno就立即暫停了臨床試驗,同美國FDA及公司內部數據安全監測委員會開展復審,并按照FDA要求對患者知情同意書、試驗方案等四項材料作出了修訂。隨后,FDA在不到一周的時間內就將材料審閱完畢,并同意了Juno恢復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