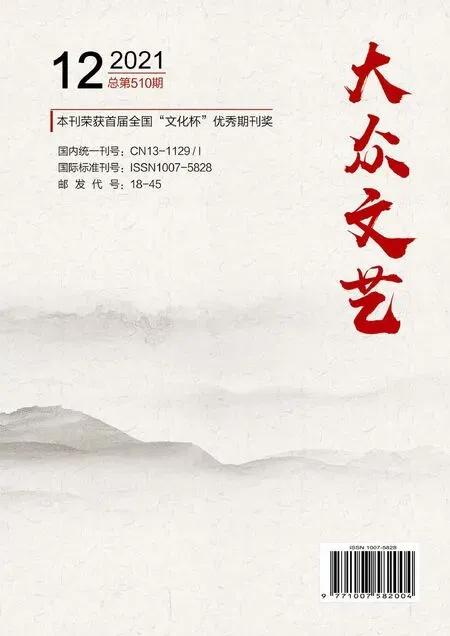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的“美麗”詮釋
——解析室內(nèi)樂(lè)作品《花夜》
梁奕飛 (四川音樂(lè)學(xué)院 作曲技術(shù)研究中心 610021)
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的“美麗”詮釋
——解析室內(nèi)樂(lè)作品《花夜》
梁奕飛 (四川音樂(lè)學(xué)院 作曲技術(shù)研究中心 610021)
室內(nèi)樂(lè)作品《花夜》是四川音樂(lè)學(xué)院教授楊曉忠先生在2001年創(chuàng)作的。獲文化部第十一屆全國(guó)音樂(lè)作品(合唱、室內(nèi)樂(lè))評(píng)獎(jiǎng)室內(nèi)樂(lè)作品作品獎(jiǎng)。入選新西蘭威靈頓2007亞太地區(qū)音樂(lè)節(jié)(ASIA Pacific Festival 2007 Wellington New Zealand)。2009年作品出版于《亞太音樂(lè)節(jié)優(yōu)秀作品匯編》。本文試圖揭示作曲家是如何合理運(yùn)用現(xiàn)代作曲技法結(jié)合中國(guó)民族民間音樂(lè)來(lái)表現(xiàn)和傳承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東方神韻。
楊曉忠;《花夜》;時(shí)序性結(jié)構(gòu);音色音響;民族民間音樂(lè)
室內(nèi)樂(lè)作品《花夜》是四川音樂(lè)學(xué)院教授楊曉忠先生在2001年創(chuàng)作的。“花夜”一詞,來(lái)源于羌族婚禮習(xí)俗。婚禮前晚,新娘邀集姑娘們到家中守夜,唱“花兒納吉”“盤歌”“格妹呦呀”等婚禮歌。它——被稱為“花夜”。作曲家被“花夜”散發(fā)出的濃郁的民族氣息和人文魅力所感染,用寫(xiě)意的手法營(yíng)造出羌寨夜晚寧?kù)o而神秘的氣氛;用樸實(shí)無(wú)華的歌調(diào)傾訴了新娘對(duì)父母的眷戀,對(duì)家鄉(xiāng)的熱愛(ài),和對(duì)未來(lái)生活的憧憬。
作品靈感來(lái)源于極具濃郁民族特色的羌族婚禮儀式,以“花夜”為切入點(diǎn),融合作曲家獨(dú)有的思維方式和西方現(xiàn)代室內(nèi)樂(lè)寫(xiě)作技術(shù),使作品具有豐富的表現(xiàn)力,既彰顯羌族音樂(lè)的獨(dú)特元素,又使其富有新的內(nèi)涵,讓人耳目一新。
進(jìn)入20世紀(jì),音樂(lè)的發(fā)展速度已遠(yuǎn)遠(yuǎn)快于過(guò)去幾百年,通過(guò)前人的研究和整理,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擁有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來(lái)進(jìn)行創(chuàng)作。但是作為中國(guó)人,我們更重要的是學(xué)習(xí)如何運(yùn)用這一理論體系創(chuàng)作出表達(dá)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新音樂(lè),走出一條不同于前輩的,我們自己的創(chuàng)作之路。《花夜》作為21世紀(jì)的新作品,創(chuàng)作技法和傳統(tǒng)文化有機(jī)結(jié)合的作品,已經(jīng)具有了自己獨(dú)特的風(fēng)格——后現(xiàn)代主義的特征。這部作品已經(jīng)找不到傳統(tǒng)意義標(biāo)準(zhǔn)的樂(lè)段式結(jié)構(gòu),作曲家在大事件背景下,將所有的形式與內(nèi)容細(xì)微化。本文將通過(guò)對(duì)《花夜》這部作品的分析與研究,試圖闡述作曲家是怎樣運(yùn)用中國(guó)民族民間音樂(lè)結(jié)合現(xiàn)代作曲技法,來(lái)表達(dá)和傳承對(duì)自己國(guó)家、民族文化的情感烙印。
一、時(shí)序性的結(jié)構(gòu)
這部作品采用時(shí)序性的結(jié)構(gòu),作曲家通過(guò)對(duì)“花夜”這一羌族特有的婚禮習(xí)俗的描述,作品由花夜前(陳述性)——花夜中(延伸)——花夜后(尾聲)三個(gè)段落構(gòu)成,即具有時(shí)序性的結(jié)構(gòu)特點(diǎn)。不管從小的短句的處理,還是三個(gè)大的段落的處理,都充分的融入了其三部性的特點(diǎn)。
如作品開(kāi)始處的第一個(gè)短句(1—5小節(jié))就具有三部性的特征。先由中提琴和小提琴的中低音區(qū)撥奏開(kāi)始,經(jīng)過(guò)兩小節(jié)弦樂(lè)三連音與八分音符的掃弦,最后回到弦樂(lè)撥奏。這種從靜態(tài)——?jiǎng)討B(tài)——靜態(tài)的形式中,看出其三部性的特征,同時(shí)也具有收束樂(lè)句的特點(diǎn)。其實(shí)也是全曲結(jié)構(gòu)的一個(gè)縮影。
在第二部分(35—64小節(jié))開(kāi)始處的短句(35—39小節(jié)),同樣的也具有三部性的特征。從中看出,中提琴的震音之后,小提琴揉弦再回到震音,這也是三部性的收束樂(lè)句。但是除這一特點(diǎn)外,較之1—5小節(jié)中八分音符掃弦的部分做了更多的延伸,形成了具有非對(duì)稱短句的特點(diǎn)。
以上幾例作曲家并沒(méi)有使用傳統(tǒng)的方整性收束樂(lè)段、樂(lè)句(2+1+1或2+2+4)等,而是運(yùn)用了非均衡的手法,讓B的部分盡可能的延伸,打破其方整性。如作品中第一部分的第一段落(1—17小節(jié))的處理,雖是三部性,但其內(nèi)部卻是非對(duì)稱的結(jié)構(gòu),即采用了(4+11+2)的結(jié)構(gòu),其中中間部分具有開(kāi)放的性質(zhì),使其更為張力和表現(xiàn)力。雖然作曲家在這部作品的短句,段落中運(yùn)用了三部的收束性結(jié)構(gòu),但作品并沒(méi)有失去其推動(dòng)力。相反的,作曲家依靠短句,段落內(nèi)部大量的延伸和密度的增加,采用非對(duì)稱的發(fā)展手法在三部性的收束結(jié)構(gòu)中尋求音樂(lè)的流動(dòng)性和推動(dòng)力與作品的延展。
在最后一部分(65—80小節(jié))的處理上,作曲家采用了所有樂(lè)器回歸最常態(tài)的演奏技法來(lái)演奏一段類似民歌的曲調(diào),前面所有出現(xiàn)的音高材料都可以在最后一段中找到原形。我們也能看到從前兩部分非均衡的短句、段落到這里的方整性樂(lè)句、樂(lè)段,從非傳統(tǒng)的演奏到中性的、常態(tài)的演奏無(wú)不體現(xiàn)了一種結(jié)論性的推導(dǎo)式尾聲方式。
作曲家在這部作品中運(yùn)用時(shí)序性結(jié)構(gòu)將羌族婚禮儀式的進(jìn)程表現(xiàn)的淋漓盡致,材料運(yùn)用的非常精簡(jiǎn)而有張力,不僅體現(xiàn)了作曲家對(duì)音樂(lè)材料的掌控能力以及使用高度統(tǒng)一音樂(lè)材料的能力,還體現(xiàn)出作曲家對(duì)整部作品結(jié)構(gòu)的把握和創(chuàng)新意識(shí)。
二、音響延伸的途徑——音色
音色就像畫(huà)家手中的調(diào)色板,畫(huà)家用五彩繽紛的顏色美化作品,同樣作曲家用多樣的音色來(lái)“裝飾”作品,成為音響延伸的途徑。在這部作品中音色、音響的處理顯示了作曲家深厚的文化底蘊(yùn)和高超的作曲技法與創(chuàng)作靈氣。作曲家根據(jù)作品背景中需要的意境,對(duì)弦樂(lè)的演奏法進(jìn)行了研究,使用了多樣的特殊演奏技法,讓音響在音色不斷發(fā)展和變化中得到延伸,推動(dòng)全曲的發(fā)展。它們也是構(gòu)成了其獨(dú)特音響的基本音樂(lè)元素。
1.多樣的音色
左手撥弦(ad lib+),這種撥弦的音響效果相對(duì)于常規(guī)的撥弦(pizz)顯得清脆、緊湊。作品一開(kāi)始便用了兩種不同的撥弦,作曲家恰好利用了左右手撥弦的差異性描述了一種延綿與清脆,混沌與淳樸的對(duì)比,準(zhǔn)確的表達(dá)了“花夜”前新娘矛盾的心理和羌寨靜溢的夜晚。
“楠溪沒(méi)有白米飯,只有番薯絲救條命。”“月里底(坐月子)吃蕃菇種——命逼倒。”說(shuō)明浙南人生存條件的窘迫。
用指甲揉弦(N),演奏者用指甲揉弦是像在模仿中國(guó)傳統(tǒng)樂(lè)器古琴揉弦的那種純凈,清晰的音色。
甚至在連接(插句)的部分(27—28小節(jié)),作曲家運(yùn)用手指虛按琴弦的泛音滑奏來(lái)表現(xiàn)一種模糊的試圖尋找某種東西的意境。
這部分與之前的撥奏、掃弦和之后的震音段落并不切合,但似乎又有著某種聯(lián)系,其實(shí)作曲家也正是運(yùn)用這樣的插部,和聽(tīng)眾一起努力的尋找著一個(gè)音調(diào),從幻想到現(xiàn)實(shí)的音調(diào)。從這里也可以看出作曲家融入了幻想的音調(diào)——尋找音調(diào)——聽(tīng)到現(xiàn)實(shí)的音調(diào),這一符合全曲三部性結(jié)構(gòu)的特點(diǎn)。
全曲第二部分新的音色出現(xiàn),弦樂(lè)揉弦對(duì)哭腔的模仿,作曲家非常形象的描述了守夜時(shí)新娘的復(fù)雜心情——悲傷和喜悅交織。
作曲家用自己獨(dú)特的方式使西洋樂(lè)器模仿演奏中國(guó)樂(lè)器所獨(dú)有的音色,這也正是作曲家深厚豐富的中國(guó)文化底蘊(yùn)的流露,也能看出作曲家對(duì)音色的獨(dú)特見(jiàn)解。
2.音色序
這些音色的變化其實(shí)都是輔助音響一步步得到延伸和推進(jìn)的手法。在這部作品中音色其實(shí)也呼應(yīng)了全曲結(jié)構(gòu)的時(shí)序性特點(diǎn)。

表1
從表1中我們可以看到音色在作品中由繁到簡(jiǎn)的變化過(guò)程,最終回歸到最常態(tài)的音樂(lè)形象。音色在其中起到了延伸的作用。
再例如,作品第一部分開(kāi)始處弦樂(lè)出現(xiàn)的撥弦和泛音(1-5小節(jié)和27-28小節(jié))到第二部分結(jié)尾處又出現(xiàn)了與其音色不同的撥弦和泛音(59-64小節(jié)),作曲家通過(guò)這樣的變化方式讓音色成塊的,具有了時(shí)序性的特點(diǎn)。
3.音色的過(guò)渡
這部作品中音色作為音響延伸的途徑,在段落間也起到了過(guò)渡的作用。例如第一部分的(25—34小節(jié))長(zhǎng)笛聲部花舌,連續(xù)運(yùn)用上行,弦樂(lè)聲部保持著雙音的節(jié)奏性拉奏將全曲推到一個(gè)高點(diǎn)。
其實(shí)這部分就是為第二部分的弦樂(lè)震音音色做了鋪墊,起到了過(guò)渡的作用。
又如作品第二部分長(zhǎng)笛聲部(59—64小節(jié)),也是通過(guò)幾個(gè)長(zhǎng)線條的下行運(yùn)動(dòng),弦樂(lè)聲部通過(guò)撥奏和泛音,逐步的將全曲從高潮退下。
這部分是向最后一部分中性的,常態(tài)音響的一個(gè)過(guò)渡,既有之前音色的出現(xiàn)又為后面的音響作了鋪墊。還有作品中的插部的音色(27-28小節(jié)),作曲家在插部做了最后一部分音響的隱伏,其實(shí)也是一種先現(xiàn)。
上面兩個(gè)例子中作曲家將基本音響材料大二度,純五度橫向的運(yùn)用在長(zhǎng)笛聲部,并且在不同的部分用了不同的音色,起了不同的作用。這種類似于旋律線的運(yùn)用也使其具有過(guò)渡連接性并賦予推動(dòng)力。
作曲家不斷地尋求變化,從而使其在音響上具有新鮮感和推動(dòng)力。這充分顯示出作曲家高超的創(chuàng)作手法。在這部作品中,只是采用了羌族音樂(lè)中的特性音響,就將整部作品帶入“花夜”的氛圍中,準(zhǔn)確而恰當(dāng)。雖然這部作品運(yùn)用了不少有特性的音色,但是整部作品并沒(méi)有覺(jué)得凌亂與不協(xié)和,相反的,它不僅讓聽(tīng)眾在西洋樂(lè)器演奏的作品中,感受到了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的特征并賦予其新的涵義,也使音響不斷的推進(jìn)延伸,音樂(lè)也有了極強(qiáng)的推動(dòng)力。作曲家用獨(dú)特的創(chuàng)作技法詮釋了對(duì)音色、音響的理解,既不拘泥于現(xiàn)代,又跳出了傳統(tǒng)的束縛。
三、羌族音樂(lè)的獨(dú)特運(yùn)用方式
近現(xiàn)代作品中,作曲家常在作品中融入自己本國(guó),本民族的具有地域性特色的音樂(lè),來(lái)尋求一條自我表達(dá)的方向。《花夜》這部作品就是一部將中國(guó)民族民間音樂(lè)和西方作曲技法完美結(jié)合并賦予其新的意義的作品。作曲家用自己獨(dú)特的方式,將羌族音樂(lè)元素巧妙的融入作品。
該部作品本身并沒(méi)有一味的,直接的運(yùn)用羌族民間音調(diào),而是先將其做了歸納——整理——提取精髓的過(guò)程,然后再運(yùn)用于作品中。
羌族音樂(lè)中所用的音階以五聲、六聲為主,如①la、si、do、re、mi、sol、la或②la、do、re、mi、fa、sol、la。該作品中作曲家除了提取羌族音樂(lè)中最具特征的純五度,大二度作為該作品的基本材料,還運(yùn)用了音階中小二度這一特性音程。(8-9小節(jié)中的弦樂(lè)聲部和33、42小節(jié)的小提琴聲部)
雖然材料簡(jiǎn)單,但通過(guò)音色、節(jié)奏、音材料的不斷變化,豐富的音響,作品的意境也被完美的勾畫(huà)了出來(lái)。
還有,羌族特有的民間樂(lè)器羌笛的曲調(diào)中仍然出了小二度音程(見(jiàn)譜例1)
譜例1:
上例羌笛曲調(diào)徐緩悠長(zhǎng),沒(méi)有劃分明顯的樂(lè)句的特點(diǎn),也正是全曲氣息的體現(xiàn),如長(zhǎng)笛聲部運(yùn)用的大量長(zhǎng)氣息的句子(見(jiàn)25-34小節(jié)和59-64小節(jié)),也是沒(méi)有明顯的段落劃分,在一個(gè)較長(zhǎng)的,甚至延綿不絕的氣息下,讓作品延伸出去。
作品最后一部分所出現(xiàn)的這段最常態(tài)的音調(diào)(見(jiàn)65-80小節(jié)),也并不是羌族某個(gè)民歌的照搬或縮影,而是作曲家通過(guò)長(zhǎng)期對(duì)羌族民間音樂(lè)的研究與積累而自然流露出的心中對(duì)“花夜”這一婚禮習(xí)俗的淳樸感受。雖然從旋律還是音色、音響都回歸到最原始,淳樸的中性狀態(tài),但是作品卻在這一部分得到的最大限度的升華。往往最淳樸,簡(jiǎn)單的東西,最能打動(dòng)聽(tīng)眾,作曲家將這部分放在全曲的最后出現(xiàn),既起到了承前的作用,又使整部作品完美的在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語(yǔ)言中得到最好的升華。作曲家并不拘泥于音調(diào)本身,而是注重于怎樣將作品內(nèi)涵準(zhǔn)確的表達(dá)出來(lái)。從這部作品中我們看出楊曉忠先生所特有的中國(guó)文化底蘊(yùn),和極深的寫(xiě)作功底。也從中懂得了要將民族音樂(lè)特點(diǎn)化為具體的藝術(shù)表現(xiàn)技法,若只是在占有民族民間音樂(lè)資料,收集民族民間形式的階段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努力掌握民族民間音樂(lè)的傳統(tǒng)規(guī)律、深入理解民族音樂(lè)的精神實(shí)質(zhì),從民族性格和審美觀念的角度去領(lǐng)會(huì)我們民族音樂(lè)真正優(yōu)異和獨(dú)到之處,這樣才能自如而準(zhǔn)確的進(jìn)行表現(xiàn)技法的創(chuàng)新。
四、結(jié)語(yǔ)
楊曉忠先生是近年來(lái)活躍在國(guó)內(nèi)外作曲界的一位作曲家,他在創(chuàng)作中把精力轉(zhuǎn)向更為廣闊的創(chuàng)作空間,注重理論性與藝術(shù)性的結(jié)合,把握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觀念的關(guān)系,尋求中國(guó)音樂(lè)元素與西方音樂(lè)美學(xué)觀和創(chuàng)作觀念的融合。他運(yùn)用自己獨(dú)有的對(duì)作品結(jié)構(gòu)和音色音響的掌控和對(duì)民族民間音樂(lè)的深刻領(lǐng)悟;帶著探尋多元文化交匯的通道,創(chuàng)建不同風(fēng)格融合的有機(jī)單元的創(chuàng)作理念而創(chuàng)作出來(lái)的很多作品都獲得了國(guó)內(nèi)外的好評(píng)。2008年10月楊曉忠先生的作品《拂塵Ⅱ》根據(jù)道教里的一件法器——拂塵而創(chuàng)作。獲得了由盧森堡現(xiàn)代音樂(lè)協(xié)會(huì)舉辦的“2008第七屆盧森堡國(guó)際作曲比賽【International Composition Prize—Luxembourg 2008(7th)】的第四名。這是即《花夜》后又一成功的作品。
作品《花夜》的創(chuàng)作是成功的,不論從獨(dú)特的音樂(lè)表現(xiàn)手法還是細(xì)膩、精致的創(chuàng)作技巧上都是我們學(xué)習(xí)借鑒的典范。作品具有深刻的文化內(nèi)涵,顯示了作曲家強(qiáng)烈的藝術(shù)感染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蘊(yùn)。《花夜》這部作品正是在中國(guó)現(xiàn)代音樂(lè)尋求創(chuàng)新時(shí),對(duì)于“中國(guó)現(xiàn)代音樂(lè)”最好的詮釋。音樂(lè)在前,創(chuàng)新為輔,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創(chuàng)作出打動(dòng)人心的作品。我們并不需要過(guò)于華麗的音調(diào),質(zhì)樸的旋律才是我們內(nèi)心的感受。既不是其傳統(tǒng)音樂(lè)的精髓,又展現(xiàn)出現(xiàn)代音樂(lè)創(chuàng)作技法上的突破。既不弘揚(yáng)了幾千年中國(guó)民族民間音樂(lè)的偉大,又促進(jìn)了中國(guó)民族民間音樂(lè)的傳承與發(fā)展。可謂是中國(guó)現(xiàn)代室內(nèi)樂(lè)作品中極具代表性和前瞻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