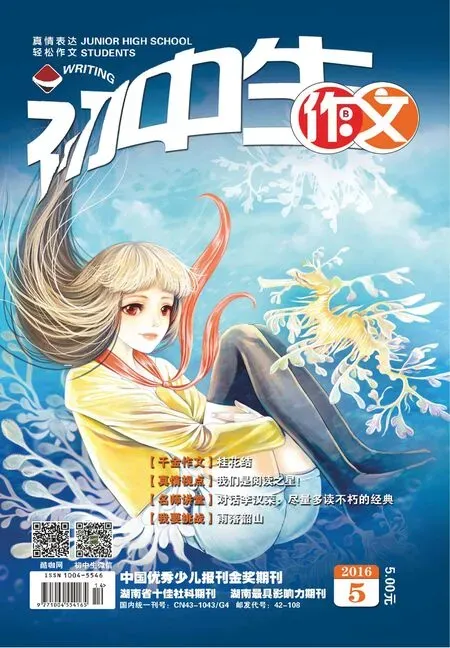細節 決定作文的精彩程度
文/龔 峰
責任編輯:吳新宇
細節 決定作文的精彩程度
文/龔 峰

我在長期的作文教學實踐中,發現很多學生的習作有粗糙、粗略的毛病,該詳寫的地方非常簡單,文中找不到細節描寫。比如寫人物,其舉止行為僅三言兩語,很不到位,以致外在形象模糊,沒有個性特點;心理描寫流于淺表,沒有深處的內在波動。再比如寫景狀物,也不是基于獨到細微的觀察,描寫模式化、機械化。很多學生作文,通篇就是幾條筋,內容空洞,沒有給人留下什么印象。
要想文章精彩傳神,取決于細節。作者所狀摹的物事纖毫畢現、栩栩如生,就會給讀者以如臨其境的“現場感”;刻畫的人物形象鮮活、血肉豐滿、個性彰顯,就會讓人如見其人,如歷其事。如果再有不俗的文采,就會讓人拍案叫絕,嘆賞作者的“神來之筆”。
古人在論述文章的詳略得當時,有兩個精準形象的比喻:“密不透風,疏可跑馬。”所謂“密不透風”,就是在寫與主題密切相關的節點時不惜筆墨,“工筆描繪”(當然,該略寫的地方千萬不能繁瑣,要一筆帶過,惜墨如金)。我們可以從眾多經典作品中得到借鑒與啟示,如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的語言風格就是以極其張揚的細節著稱,洶涌的聯想讓他的感覺達到了“爆炸”的程度。他的中篇小說《紅高粱》,對一片高粱的描寫動輒數百上千字,仿佛像素極高的攝像機,“攝”出的作品當然是精彩絕倫的。
初中語文教材中也有很多注重細節描寫的“案例”,語文老師上課時都會就此詳加分析。我在此再舉幾例,供大家回味感受。
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著顧客。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干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往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輕松似的……
現代著名散文家朱自清的文章細膩、溫婉,一篇寫父親的《背影》角度特別,情感樸實、真摯,感動了幾代人。其成功之處,我以為與精微描摹日常的、能夠喚起共鳴的細節密不可分。他父親已經年邁,體態臃腫,給兒子買橘子已勉為其難,“穿”“爬”“蹣跚”“探身”“攀”“縮”“微傾”“抱”“撲撲”,這一系列動作讓父親的慈愛展露無遺,讓作者潸然淚下的同時也讓讀者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自己的父親。如若換一種粗枝大葉的潦草寫法,“父親去給我買來橘子”,感人之情從何說起?

魯達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那醋缽兒大小拳頭,看著這鄭屠道:“灑家始投老種經略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你是個賣肉的操刀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鎮關西’!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卻便似開了個油醬鋪,咸的、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鄭屠掙不起來,那把尖刀也丟在一邊,口里只叫:“打得好!”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應口!”提起拳頭來就眼眶際眉梢只一拳,打得眼棱縫裂,烏珠迸出,也似開了個彩帛鋪,紅的、黑的、紫的都綻將出來。
《水滸傳》是一部寫豪俠英雄的古典小說,里面的人物大塊吃肉,大碗喝酒,殺富濟貧,快意恩仇。從故事鋪排和人物性格的塑造看,古代章回小說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人物和情節大同小異、不夠細膩的問題,但施耐庵畢竟不是等閑之輩,整部《水滸傳》中熠熠閃光的亮點確實不少。如情節的張弛、敘事節奏的緩急、語言的粗豪潑辣與情節的細微精彩等,《水滸傳》都是我們學習寫作取之不盡的寶庫。
在《魯提轄拳打鎮關西》中,我們印象最深、最解氣過癮的就是那“三拳”。“打”是小說的高潮部分。為了懲治鄭屠這個地痞無賴,憤怒的魯達并未逞一時之勇,來到肉鋪,劈頭蓋臉就揍他一頓,而是“三激”鄭屠,對鄭屠大加戲弄,可見其有膽識、有謀略。而伸張正義、懲治惡人的“三拳”,一拳一個落點,一拳一個比喻,一拳比一拳厲害,則不僅讓人解恨,更在讀者面前刻畫出了一個英勇非凡、武藝高強的“梁山好漢”形象。至此,一位嫉惡如仇、扶危濟困、重義輕財、粗中有細、勇而有謀的肝膽英雄,活生生地展現在我們的面前。
俄一客曰:“蒙賜月明之照,乃爾寂飲。何不呼嫦娥來?”乃以箸擲月中。見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與人等。纖腰秀項,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還乎,而幽我于廣寒乎!”其聲清越,烈如簫管。歌畢,盤旋而起,躍登幾上,驚顧之間,已復為箸。
清代卓越的短篇小說家蒲松齡文筆相當洗練,是惜字如金的典范。當學生學習這篇《嶗山道士》時,會為他神奇的想象大呼過癮。道士投箸作法,在墻上貼一片紙,竟成了一輪皓月;再作法,竟能喚出月中嫦娥來為客人起舞助興。嫦娥的秀美音容、婀娜舞姿栩栩如在目前。作家真是高超的魔術師,不管想象中的人物在遠古還是在未來,和我們的距離有多少光年,都可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這就叫“神來之筆”。我們要用自己的文字再造美輪美奐的情景,必然得仰仗出神入化的細節。
我的短篇小說《元老》塑造了一個韋小寶式的不學無術、看風使舵的市井無賴形象,他叫袁四堂。里面有一段他在學校打鈴的細節特寫,適當地運用了夸張手法,讀者感言“印象最深”,眼睛一閉,就似看見袁四堂在打鈴:
鈴就掛在學校中央的那棵百年老樟樹下,是抗日戰爭時期鬼子留下的炸彈殼。大家看見,袁四堂有時拎著小鬧鐘,有時卷起袖子、手捏鋼管在校園巡弋。他打鈴的姿勢很特別,得進行一個特寫:起床鈴,連敲足有三分鐘,先是春雨潤物,潛入幽夜,愈來愈急驟,鐵騎突出刀槍鳴,銀瓶乍破水漿迸。再又降低八度,輕抹慢捻,師生們被驚破的夢在杳渺低徊的聲波中緩緩彌合,忽然,武松揪住了吊睛白額猛虎的頂花皮,鐵缽大的拳頭猛砸七七四十九拳,你不得不在雷霆檑木中驚坐而起。上課鈴,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以三下為一逗號,節奏鮮明,溫和婉轉。下課鈴,鏜……鏜……鏜!一記銅音畫著無數同心圓蕩漾開去,又一記銅音推波助瀾。吃飯鈴,連續七下,七劍下天山,七飯踢啊七飯踢,同學們敲著瓷碗,在袁四堂奏鳴的鈴聲里如大河之水奪閘而出。
責任編輯:吳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