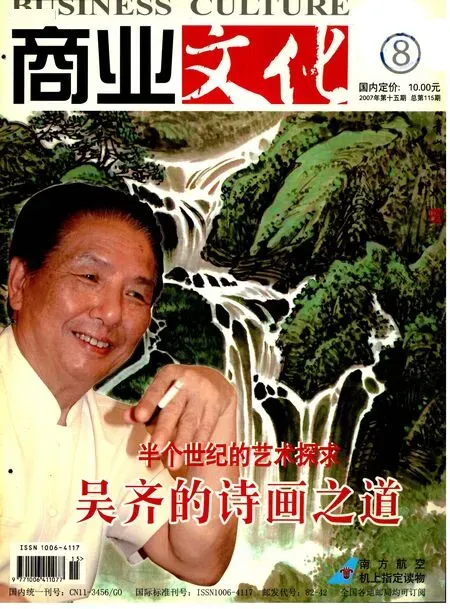中企走出去大道不獨行
文/周 密
Great Article 登壇論道
中企走出去大道不獨行
文/周 密
面對依舊漫長的全球經濟再平衡進程,適應中國經濟新常態,需要探索適應內外形勢變化的機制與模式。增強對國際規則的制訂權,推動跨國經營活動的有序開展和升級,對于中國跨國公司的培育和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過去30年來,全球經濟發生深刻變革,中國參與全球要素資源分配和產業鏈的廣度和深度都有了極大拓展。國際形勢不斷變化,全球經貿合作需求逐漸加強,形式更為豐富。以對外援助開啟的中國跨國經營業務不斷發展,內容日益豐富。對外工程承包、對外勞務合作與對外投資漸次興起、快速發展。外匯儲備從短缺到能夠滿足對外投資需求,再到需要通過投資充分發揮作用。隨著自身實力的增強,中國正在更加主動參與全球未來規則體系的重塑進程,圍繞“一帶一路”提出中國概念和愿景并積極推進,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宏偉中國夢、培育更多世界級跨國公司持續努力。
跨國經營形式單 零星熱點常相聯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與國際市場的聯結較為有限,經濟實力和有效利用全球資源、市場的能力較弱。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外匯儲備剛剛從個位數升至十位數,整整十年,中國外匯儲備都沒有超過100億美元。1989年的外匯儲備僅有55.50億美元。有限的外匯儲備不僅嚴重制約了中國購買國外資源和設備、引進技術的能力,也使得對外投資管理十分嚴格。這一階段中國的國際經濟合作業務以貿易出口和利用外資為重點,而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仍然延續了建國以來以對外援助帶動相關企業“走出去”的做法,對外承包工程和對外勞務合作成為跨國經營的主要形式,對外投資規模有限且較為零星。全球多數地區的開放度和市場購買力較低,僅有少數地區市場發育較為成熟,中國企業國際化剛剛起步,幾種主要跨國經營形式均呈現地區和業務集中、國有企業是市場主要參與者等特點。
在二戰后最嚴重經濟危機、兩次石油危機和兩伊戰爭等沖擊下,全球工程承包市場出現嚴重不景氣,激烈的市場競爭打擊了風光一時的韓國國際工程承包商。在政府指導下,中國承包商開始將市場從中東向亞洲、非洲國家轉移,具有一定技術含量的電站、糖廠和化肥廠等項目開始起步,為后來中國工程企業雄踞發電行業領先地位打下堅實基礎。受交通運輸不發達、全球范圍勞務人員跨境提供服務尚未形成潮流等因素共同影響,勞務與工程、貨物貿易聯系較為緊密,承包項下的對外勞務合作業務是這一階段中國對外勞務合作的主要形式,而中國承包設備出口公司、中國建筑工程公司、中國公路橋梁工程公司和中國土木工程公司等4家國營公司成為率先開展對外承包工程與勞務合作的主力軍。

國有企業是市場主要參與者
成立于1982年的對外經濟貿易部經國務院授權,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歸口管理部門,頒布了《關于在境外開辦非貿易性企業的審批程序和管理辦法的試行規定》。然而,受資源不足、能力較弱和選擇范圍有限等多種因素的共同制約,在1979~1989 的10年間,批準的境外非貿易企業只有645家。少數大型企業成為這一階段對外投資的舞臺主角,投資標的相對較小且對企業國際化發展支撐力有限。由國務院在1979年批準設立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動作頻頻,美國、加拿大、中國香港等經濟較發達國家(地區)均成為中信對外投資的試驗田。1986年,中信加拿大公司與加拿大鮑爾公司以50:50的股權比例共同收購了加拿大塞爾加紙漿廠。1988年,中化集團開始國際化經營試點,首鋼也收購了美國麥斯塔工程設計公司70%的股份。
拔劍四顧心茫然 文化障礙成難關
20世紀90年代,中國開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市場活力快速釋放,資源配置效率顯著提高,企業更為活躍,開始考慮在更廣范圍內尋找發展的穩定支撐。盡管遭遇海灣戰爭、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經濟的強大穩定性和活力仍然支撐了企業走出國門的步伐。前期的積累使得中國外匯儲備顯著增加,自1990年達到110.93億美元后,1996年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1999年更達到1546.75億美元。外匯儲備對跨國經營的制約有所減弱,政府對跨國經營的管理有所放松,企業努力探索增強對資源的掌控能力。然而,企業主導權的增強也加劇了優勝劣汰的進程,面對完全陌生的市場和環境,勇于試水的企業不得不應對較大不確定性帶來的挑戰。
行政松綁后,即便具備較強實力的國有企業在對外投資中依舊步履維艱。1992年,國務院批準擴大首鋼、鞍鋼、大慶等大型企業的投資立項權,授予其自主決定1000萬美元以下的海外投資項目的權利。同年,首鋼以1.2億美元購買瀕臨倒閉的秘魯鐵礦公司98.4%的股權。通過生產組織、人力資源等方面優勢的發揮,首鋼投入資金修復、更新生產設備,使得已近癱瘓的秘魯鐵礦產量快速增長,1993年的產量就達到525.8萬噸,比上年增長84.6%。但是,盡管首鋼在社區建設、環境保護、職工福利等方面投入巨大,國際鐵礦石市場的不景氣和文化的差異在隨后相當長時期內給首鋼帶來巨大挑戰。中國與秘魯在語言、文化上的巨大差異、法律體系的不同、員工對首鋼的不信任、罷工的頻發,使得首鋼這一保障上游資源供給的努力幾近失敗。事實上,盡管迄今已經過20多年的努力,秘魯鐵礦即便已經在生產、物流、本地化管理等諸多方面達到較好配合,罷工仍然是其揮之不去的陰云。市場機制更為靈活,經主管部門的批準,從事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的公司從1990年的91家迅速增至20世紀末的千余家,包括大型工貿集團、大型設計院、外貿公司等大量專業實體加入到對外承包工程行業中,增強了對業主需求的服務能力。越來越多的企業在全球工程和設計行業內承包項下派出仍是對外勞務合作的主體,但其所占比重持續下降。與此同時,普通工人、技工和農民、海員、工程師、醫師、護士和會計師等技能型勞務輸出不斷增加。對外勞務合作公司作為人員派出的主體,加強派出前培訓。這一階段,中國的勞動力具備全球范圍成本優勢,而相對兩個市場”,提升自身國際影響力。為此,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政策環境更為寬松、規范,對外投資管理和服務體系不斷健全,通過信息引導和服務保障支撐企業以多種方式開拓國際市場的努力越來越多。加入WTO為中國融入世界、為保護企業利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國企業因此得以進入其他成員國市場,投資者的基本權益得以保障,中國與全球聯系更為緊密。外匯儲備在2006年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后持續快速增長,2008年達到19460.30億美元,外匯占款更多影較高的收入也吸引了相當規模的技能人員選擇外派勞務工作。

首鋼收購美國麥斯塔工程設計公司70%的股份
戰略開啟強國路 入世打開新空間
20世紀末“走出去”戰略的提出和21世紀初中國入世是中國企業跨國經營進入新階段的明確標志。根據“走出去”戰略,國家引導和鼓勵中國企業積極利用“兩種資源,響金融政策的靈敏性和有效性。中國支持企業開展對外投資不僅具備資金實力,而且也逐漸變得急迫。
對外投資一舉成為最為重要的跨國經營業務形式。企業對外投資的意愿強烈,無論規模、行業、所有制、地域,中國先后超過諸多發達經濟體,成為全球最大的對外投資來源國之一。2004年12月,聯想宣布以12.5億美元的現金和股票收購IBM的全球臺式電腦和筆記本業務,完成了“蛇吞象”的跨國并購創舉,將總部移至美國,成為全球個人電腦的主要提供商之一。10年后,聯想又以23億美元收購IBM的服務器資產,大幅提升了在服務器領域的國際地位。通過有效處理并購后的文化沖突,聯想不僅扭轉了IBM業務部的虧損,更安然應對其他廠商的競爭和消費端市場的疲軟。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行業領域愈發多元化,不僅廣泛進入礦產和能源資源領域,也在服務業等產業形成更強競爭力。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積極“走出去”,把握市場發展機會,通過國際化大幅提高全球競爭力。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在經歷了近20年快速增長后逐漸進入“平臺期”,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增速下滑,新簽合同額逐年減少,來自其他印度和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的承包商,與發達經濟體的承包商分別從產業鏈低端和高端一起擠壓中國企業空間,國內人力成本快速增長,對外承包業務吸引力下降。受此影響,中國對外勞務合作人員的競爭力被大幅削弱,地方政府為降低業務風險收緊了對外勞務合作業務的管理,對外勞務合作業務在市場縫隙中艱難發展。
危機鋪就歐美路 把握機遇書詩篇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經濟危機終結了21世紀以來全球經濟持續增長的上升通道,發達經濟體所受沖擊尤為直接、巨大、反復,全球經濟格局由此產生劇烈調整。危機促進了“20國集團”機制作用的發揮,主要經濟體為應對危機采取了協同的措施,成功遏制了危機的第一波沖擊。然而,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導致歐債危機和財政緊縮引起歐元區的頻頻告急,主要發達市場需求萎縮通過國際市場供需傳導至出口導向型發展中經濟體,引發一波波危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快速推進,中國的外匯儲備在經濟危機爆發后連續突破2萬億、3萬億和4萬億美元,對支持企業跨國經營的需求更強。在歐美經濟受到大幅沖擊時,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發展中企業加快了跨國經營的步伐,開拓歐美市場的經濟活動更加活躍,在自身發展的同時部分減弱了歐美國家受危機沖擊導致的資金不足困難。發達經濟體投資環境較為成熟,但在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初級階段仍多以發揮企業國內優勢、尋求更多資源保障和更低生產制造成本為主。經濟危機爆發后,受投資標的企業價值下降、企業希望通過對外投資提升產業地位和影響力等因素共同作用,中國企業積極把握機遇,對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的投資快速增長。美國、英國、德國都成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重要東道國。萬達先后收購美國第二大院線AMC、英國豪華游艇制造商圣汐公司、西班牙馬德里競技俱樂部;吉利收購沃爾沃公司;三一重工收購德國混凝土制造商普茨邁斯特;萬向收購美國123電池公司。中國企業對歐美的并購廣泛涉及各個行業領域。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企業在走向歐美市場過程中也面臨不少挑戰,以所謂“國家安全”、反壟斷和國有企業等為理由阻止投資的情況多次出現。受法律限制,中國企業曾多次出現未能真正實現其投資目的的情況。
危機應對初期各國擴張性財政政策創造了比危機前更大的市場,為中國對外承包工程企業帶來了更多機會。然而,隨著危機進程的深入發展,各國政府持續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的財力捉襟見肘,而持續超級寬松的貨幣政策事實上造成了企業未來收益的實際價值縮水。對外勞務合作業務發展出現新的特點。多樣化的需求催生多種形式的對外勞務合作,而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增強和國內平均收入的上升繼續減少了勞務輸出的供給量。對外勞務合作供需匹配的難度有所上升,對接雙方需求,推動業務發展需要更完善的制度保障和更深入的市場開放。
“一帶一路”中國夢大國責任莫等閑

中國正站在承前啟后歷史發展的關鍵點,主要經濟體出現歷史罕見的貨幣政策異步,全球需求持續疲軟,危機影響通過貨物貿易傳導至發展中經濟體。中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和“未富先老”的重要挑戰,環境約束不僅落在紙面的減排承諾,更已經影響到外資的布局和人民的健康。面對依舊漫長的全球經濟再平衡進程,適應中國經濟新常態,需要探索適應內外形勢變化的機制與模式。增強對國際規則的制訂權,推動跨國經營活動的有序開展和升級,對于中國跨國公司的培育和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對外投資管理的進一步簡化事實上是向負面清單管理的重要轉變,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促進沿線國家共同努力,不僅有利于中國經濟尋找新的動力,而且有利于幫助相關國家應對危機沖擊,獲得經濟增長新的支撐點。在多邊平臺上推動發達經濟體做出更大開放承諾,實現中國從防守為主向進攻并重的戰略調整,在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轉型升級期有著尤為重要的意義。在區域經貿合作上以戰略重點區域協同推進,有效實現利益鏈條更為緊密下的產業國際轉移。加快與關鍵、重點、潛力較大國家和地區間的雙邊經貿合作,幫助企業增強資金、人力、技術、商品等各類要素資源的整合與配置能力,適應雙方需求。中國需要適應在從資本的凈流入國向凈流出國轉變的歷史性變化,既要繼續大力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國際資本流入,又要加強引導、積極鼓勵“走出去”企業資本回流,加強中國與世界的經貿聯系。對外承包工程也面臨“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推進的重要機遇,沿線各國對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增長,以及亞投行、絲路基金等金融安排為傳統業務發展創造空間,綠色發展拓展了改造和升級的需求。但是,在建筑服務總體供過于求的情況下,需要加快中國承包企業與國際巨頭的合作,增強在技術、資金密集型領域的競爭力;加強與工程所在地或其他發展中國家工程企業間合作,通過產業鏈升級和分工配置降低整體運營成本,減少與當地的直接沖突。服務貿易模式四項下的自然人流動空間廣泛,國家間人力資源供需在總量和結構上仍將處于較為不平衡的狀態,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的各階段都需要更多人員跨境流動,促進服務貿易發展和滿足國內消費者的升級需求也需要更為便利的跨境人員流動。通過協議促使各方保證人員流動合法權益,與東道國政府協同加強對境外中國人的領事保護,完善風險預警機制,適應業主需求加強有針對性的語言、技能培訓,共同維護跨境自然人流動的秩序。

積極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

加快中國承包企業與國際巨頭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