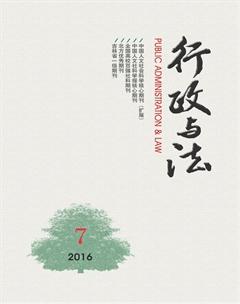論國際法碎片化的成因
摘 要: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知識職業化和科學方法論廣泛應用是國際法碎片化的深層次原因。國際法的建構者從不同傳統中選取一些碎片化的觀念并加以合法化成為國際法知識體系。國際法構建之初的碎片化和不確定性的特點導致了國際法的先天不足和必然的缺陷。
關 鍵 詞:碎片化;理性主義;知識職業化
中圖分類號:D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8207(2016)07-0116-07
收稿日期:2016-03-20
作者簡介:李秀芳(1974—),女,河北邯鄲人,復旦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浙江財經大學講師,研究方向為國際公法。
一、國際法碎片化是知識
職業化的后果
2006年,國際法委員會就國際法碎片化提出報告,認為后現代國際法的特征之一是功能性分隔,這是由社會各領域的專業化和部門自主性造成的。碎片化既是國際法問題,也是國內法現象。與國際社會碎片化相伴隨的是規則或規則復合體、法律制度與法律實踐的專業化和自主性。以前由一般國際法調整的領域現在則由“貿易法”“人權法”“環境法”“海洋法”“歐洲法”甚至是異質和高度專業化的“投資法”和“國際難民法”等專門領域調整。但在進行專業造法和專業制度建構時,各領域往往無視相鄰領域的立法和制度現狀,無視國際法一般原則和實踐,偏離制度與法律的整體視角,從而引發規則或規則體系間的沖突。國際法碎片化的后果之一是產生相互沖突和相互抵觸的規則、原則、制度實踐。[1]
隨著國際性法院、仲裁庭的擴張,隨著全球化深入,國際法碎片化成為無法回避的話題。關于如何克服規范沖突、重疊管轄等問題,學者從國際法制度和體制等方面提出種種對策。[2]筆者認為,理性主義泛濫以及相隨的知識職業化、科學方法論的廣泛應用是國際法碎片化的深層次原因。
能被視為職業的工作往往需要一套專門化的、相對(有時是高度)抽象的、體系性的科學知識。[3]現代職業與工業資本主義崛起有關,與前工業時代的職業有著天壤之別。根據弗萊德森的研究,在前工業時代,大學里培養的職業主要有法律、醫學、神學和不太常見的軍事四個職業,這些職業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自十九世紀起,新興行業引發了職業結構變化,法律、醫學、神學和軍事等古老職業的性質和認同發生變化。新興行業試圖獲得“職業”稱號,因為職業意味著博學、紳士地位,有助于樹立新興職業的地位,對新興職業在市場競爭中獲得政治合法化非常重要。這樣越來越多的行業被納入到“職業”的稱號之下。[4]新興職業者為本職業合法化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在此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職業共同體。所以,職業的特征之一是“共同體”。[5]新興職業者一方面強調自己的工作具有技術倫理和共同體倫理;另一方面竭力證明本職業超越于市場定律,具有客觀理性。這種客觀理性只有經過科學程序才能理解,科學程序是發現自然和社會內在決定因素的途徑。[6]此外,新興職業者挑選觀念,把這些觀念合法化為獨特的專業知識,使之與前工業資本主義的知識有明顯區別。具體來說,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職業知識有如下特征:第一,職業知識是在市場上出售的商品。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職業知識在市場主導的歷史背景下誕生,不可避免地要參與到市場競爭中。為此“職業知識被標準化和編纂,成為職業商品”。[7]“十九世紀中期,資本滋生了一批以出賣建議和專門服務為生的人”。[8]知識產權就是對這些商品的保護手段。第二,職業知識是制度化的知識。為了在市場出售,新興職業者把本職業的知識合法化為獨一無二的專業知識,發展了一系列制度,比如頒發資格證書、組織資格考試、授予文憑、制定正規的職業培訓大綱等。此外,新興職業逐漸壟斷教育體系,使得職業招聘和晉升都以正規的大學教育為標準,使正規的教育優先于傳統的學徒制。[9]第三,職業知識最典型的特征是崇尚理性。啟蒙運動推崇理性主義,不喜歡主觀性和混亂無序。它追求澄明,力圖消除神秘,尋找實在可確定的事實,拒絕用超自然力量來解釋人類社會中的自然現象。[10]理性主義相信外部世界有一種合乎邏輯的秩序,這種秩序不僅人類頭腦可以認識,而且幾乎可以用概念性語言準確表達出來。[11]工業革命以來,理性被應用于更廣泛的領域。[12]總之,理性強調邏輯性、確定性,并試圖用精確的語言表達出來。理性是一種具有科學傾向的程序方法,與現代科學發展、把科學方法適用于技術和社會問題緊密相關。
根據學者研究,科學的英文Science由拉丁語的scientia演變而來,具有“知”或“知識”的意思,幾乎同英語的knowledge是同義詞。后來science逐漸開始使用復數形式,逐漸從單純的“知識”的含義向分化為諸如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各個專業領域科學演變,直到十九世紀,這種用法完全定形。在該演變過程中,業余的“自然哲學家”逐漸轉變為職業的“科學家”。實際上,“科學家”和“物理學家”等詞是在十九世紀中期創制的新詞,這時支撐職業科學家的各種制度也確立起來,并形成了由職業科學家構成的共同體。[13]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各個專業領域樹立了確定性的形象,在當時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以至于“確定性成為十九世紀學術界的共同追求”。[14]自十九世紀中晚期起,人文各領域也以自然科學為榜樣,以確定性為目標,紛紛從之前較為統一的知識體系中分化出來,形成了獨立的專業知識體系和不同學科,同時也形成了不同的職業共同體。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職業知識急劇增長,知識進一步專業化,學科激增,并成為大學中的科目。這些在大學中發展的職業知識不可能“充分達到科學標準,卻采納與自然科學一樣的技術或理性,努力使理性理論成為實踐的基礎,并用‘抽象的象征體系編纂知識”。[15]
理性主義泛濫導致知識的職業化,進而產生了大量互不相容、碎片化、不確定的專業知識體系。羅蘭·斯特龍伯格認為,知識專門化為無數單位,每一個單位都成為一個由自己人組成的小型的、高度組織的世界,其內部成員的知識生活以會議、專業刊物和集體性學術為中心。很大程度上這類群體在各自為政、孤軍作戰,發展自己的亞文化,極端專業化和小集體內部的詞匯阻礙了交流。比如文學經常圍繞著某位作家形成研究會:喬伊斯研究會、約翰遜研究會、蕭伯納研究會。社會學則有功能主義者、行為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存在主義者和象征主義者等學派。經濟學中存在著自由市場經濟學與國家干預的對立。心理學家分化為行為主義者和存在主義的“人道主義者”。[16]西方現代大學所傳播的知識特征之一就是碎片化、形式化、脫離現實性。有學者認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西方學者反抗的原因是“他們對于一個四分五裂而且似乎與現實生活脫節的知識世界困惑”。[17]法律包括國際法僅是人類無數碎片化知識體系的一部分。
理性主義深刻地影響著法學。法學家開始致力于“科學”探索,因為它涉及用與科學框架相符合的方式重新定義學說,也涉及重新定義職業。法律人包括國際法律人開始構建更專業化的部門法律。[18]該構建的結果是“整個法律體系的公法和私法的劃分,以及諸如民法、刑法和行政法等自成一體部門的再劃分”。[19]法律專家成為“崇尚確定性的人”,[20]自然法這類不精確的理念讓他們“大為苦惱”。[21]
二、國際法碎片化形成的認知基礎
工業時代職業知識的專業化首先發端于自然科學,所以有必要理解自然科學不同分支是如何從人類龐大的觀念中挑選觀念、進行合法化、界定專業知識體系,進而導致人類較為整體的知識體系分裂為無數碎片化的現實。路德維希·弗萊克在其科學哲學名著《一個科學事實的起源與發展》中對認知的分析有助于我們理解這個現實。弗萊克認為,為了實現純粹理性,自然科學分支拋棄思維觀念中原始的、直覺類的觀念,僅挑選并合法化能夠被科學方法邏輯證明的“正確”觀念,拋棄“錯誤”的觀念。這個挑選的過程不是客觀的選擇,而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特定思維共同體主觀選擇的結果。在觀念的選擇與合法化過程中思維共同體形成了特有的思維風格。也就是形成共同體特有的術語、思維傾向、概念及理論體系等,而與思維共同體思維風格矛盾的觀念都被斥為錯誤而予以拋棄。這也足以證明,真理是一定歷史和共同體的產物。從歷史的視角來看,真理是一定歷史階段的事件;從共時的視角來看,真理是在特定共同體的思維風格約束下的產物。被特定歷史和特定共同體視為真理的事實,在其他歷史時代或共同體就不一定為真理。卻被共同體成員視為人類思維的全體。[22]比如“地球是平的”“地球是靜止的”“地球由水組成的”等說法,用現代社會接受的信念體系衡量是錯誤的,但在古希臘卻被看成是正確、合理的。[23]
啟蒙以來,理性主義成為思維風格,人們只接受確定的、可證實的觀念,拋棄神秘莫測的、無法精確表述的觀念。弗萊克認為,自然科學家崇尚客觀理性,對主觀、客觀加以區別,試圖構建沒有主觀情感因素的概念,過渡崇尚邏輯和邏輯結論,拋棄原始的、直覺的觀念是錯誤的。[24]自然科學家不僅是錯誤的,還直接造成了人類整體知識的碎片化。因為不同自然科學分支根據理性標準,從人類龐大的知識庫挑選部分觀念進行合法化,形成不同專業知識體系的過程直接撕裂了人類較為整體的知識結構。人文學科模仿自然科學構建的不同專業知識進一步加劇了知識的碎片化。麥金太爾認為,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早期,在蘇格蘭、美國等現代大學和學院中,理性獲得了成就,理性標準獲得大眾的認可。與該理性標準極度不同的觀點被強制從大學和學院中排除。最顯著的是天文學中排除了文藝復興早期和十七世紀的占星學,自然哲學排除了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通過強制排除,自然科學取得了成功,技術獲得了聲望。同樣,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等非自然科學也被簡化為技術和程序,技術性的一致代替了知識的實質內容。分析哲學、語言學和經濟學、技術專家被置于核心地位。根據理性標準挑選和排除觀念后,大學里的教學大綱四分五裂,推薦學生閱讀的書籍分屬互不相容的不同學科。現代人成為相互沖突、不兼容、碎片化知識的接受者。高等教育導致學生陷入無休止、沒有定論的爭論中。[25]比如西方現代正義理論就是從清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不同理念中挑選觀念形成的碎片化觀念的混合物。而且,這些碎片化觀念的混合物還繼承了法國啟蒙運動、蘇格蘭啟蒙運動、十九世紀的經濟自由主義、二十世紀的政治自由主義等不同方面,導致西方現代正義理論的分化和沖突,人們對正義無法形成連貫的思維和判斷方式,社會對何為正義不再有一致的看法。[26]換言之,肇始于十八、十九世紀的知識急劇專業化,是根據理性標準選擇觀念并加以合法化,有的甚至是強制排除得以實現的,這個過程造成了知識的碎片化,割裂了人類整體的知識結構。各自為政的專業知識體系成為現代大學的不同科目。從進入校園初始,學生所接受的就是一個殘缺不全的、碎片化的知識體系。
在法學領域,“法律事實”是由法律職業共同體合法化的社會現實,被合法化為法律事實的社會現象才受法律調節,“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就是其典型表現。可訴性問題、管轄權、政治與法律的區分、法律與道德的區分、法律淵源也是職業法律人構建的事實。這樣法律所能解決的問題被限定在一定范圍內,具有了表面上的確定性和客觀性,共同體的實踐也有了明確的界限。法律分化為不同部門,每個部門法律都形成具有特有思維風格、法律術語、法律問題的職業共同體或次級職業共同體。所以現代法律人非常保守也很敏銳,總是能馬上區分出哪些問題法律可以解決,哪些問題法律無法解決。國際法律人也不例外。國際法律人在挑選、排除、合法化觀念建構國際法專業知識體系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具有獨特思維風格的職業共同體,形成了國際法學科特有的問題、評判專業水平的標準、法律方法和技術、詞匯以及相應的文風。換言之,形成這些法律人共同的“學科感”。[27]大衛·肯尼迪的研究表明,在十九世紀早期,國際法與其他法律沒有區別,沒有形成有別于國內法的法律體系。國際問題與國內問題在律師和法官眼中沒有區別。十九世紀晚期國際法體系看似非常不同了。歐洲的國際法律人開始共有一種法律意識,一種推理的方式,一套論證范疇和學說假設。[28]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以自然科學為榜樣,以理性為標準,經過觀念的挑選、排除、合法化,國際法作為一個新學科誕生了。但被稱為國際法之父的格勞秀斯對現代國際法則毫不關注,國際法也不是他學說的決定性內容。他的學說對現代國際法理論有貢獻,但他僅僅把調整歐洲君主關系的規則看作個體和君主權利義務關系的第二位淵源,而不是單獨的法律分支。[29]瓦泰爾是正式把國際法看作一個法律分支的學者。他在1758年出版的教課書《國際法》中,把國際法作為核心主題。[30]但瓦泰爾的國際法與十九世紀中晚期職業法律人以自然科學為榜樣構建的國際法有很大區別。埃芒紐爾·朱奈特認為,瓦泰爾的《國際法》不僅涉及國家間關系,更有國內法內容,而且國內法所涉事項非常廣泛,包括農業發展;國內貿易;公路、橋梁、運河等公共設施的維護;公共福利;金融、教育、藝術和科學等內容。[31]也就是說,他的國際法包括國家對內、對外關系中所有權利和義務,沒有對公法和國際法作出明顯的劃分。[32]也正因如此,當時關注國家間關系的學者僅被看作介于法律和道德之間的一類人。[33]十九世紀上半葉,英國的奧斯汀在其專著《法理學范圍之限定》中試圖根據科學界定法律。他質疑國際法的科學性,認為國際法僅是實證的道德。[34]為回應奧斯汀對國際法科學性的質疑,當時的國際法律人竭力論證國際的“科學性”,并試圖以當時流行的自然科學標準設立國際法學科。[35]韋斯累克申明自己著書立說的初衷是考慮“國際法在科學中的地位”。[36]
為了實現科學的確定性、精確性,當時的國際法律人根據理性標準進行觀念的選擇和合法化。自然法因為不具有科學的精確性被當時的國際法律人拋棄。奧本海在《國際法科學:任務和方法》中,高揚科學價值,極力否認自然法,認為自然法不過是幻覺。[37]此外,這些法律人還試圖清晰界定國際法與道德、國際法與國際政治、國際法與國內法的界限。發展出國際法的淵源學說,把條約和習慣法定為國際法的主要淵源。甚至認為“習慣法也將隱退,國際法將僅由條約法構成”。[38]根據學者研究,十九世紀,為使國際法符合理性標準,國際法實體性規則急劇減少,僅限于捕獲法、海洋法和外交豁免等領域,國際法發展成為包括主權利益學說、管轄權和國家責任的程序性規則、國家身份和國家承認等以主權為核心的學說體系。在國際法學科形成的同時,國際私法和比較法學科也分別形成,這樣國際法成為單獨學科的事實也愈發明顯,成為大學的研究和教學科目。[39]這樣,國際法逐漸成為一種“思維模式和話語,成為具有權威的法律部門,成為歐洲、北美州和南美洲大學中教授的法律,隨后也成為日本和某些亞洲國家大學中教授的法律。它是一種由逐漸職業化的、自此被稱為‘國際法專家或‘國際主義者的法學家群體討論和傳播的法律。它成為時代的范式,盡管是一種簡化了的形式”。[40]最終,根據理性標準構建起來的新的國際法逐漸替代之前的“道德、宗教、利益規則、羅馬法或皇帝法等綜合性規范體系”,[41]成為調整國家行為的規則體系。
三、自然科學方法的廣泛應用加劇了
國際法知識的碎片化
知識未被大規模職業化之前,人類主要依靠常識和傳統作為行為指導。[42]工業資本時代興起的職業群體,為樹立職業知識在大眾中的權威進行了廣泛的合法化努力,通過教科書等媒介讓大眾相信職業知識是建立在科學方法之上的,具有確定性并能改善人類生活。這樣以自然科學為代表的各種職業知識逐漸替代傳統知識成為大眾的信仰和行為指導。以自然科學為代表的職業知識的方法論是“假說演繹法”。[43]該方法的核心是以假設作為理論或學說構建的出發點。比如有職業群體提出 “吃肉身體健康”的假設,然后圍繞此假設收集數據進行論證,最終得出“吃肉身體健康”的結論。而另一職業群體給出“吃素身體健康”的假設,然后收集相關數據進行論證,最終也能得出“吃素身體健康”的結論。這些建立在不同、互不兼容甚至相互矛盾假設基礎上的理論或學說必然是不完整的、碎片化的。因此,自然科學方法的適用加劇了知識的碎片化。正如吉登斯所言:“從某種意義上講,西方社會學理論的紛繁多樣實際上來源于其方法論的分裂與對立,而方法論上的對立又根源于某種人與社會的不同假設。”[44]如何取舍基于互不兼容假設基礎上的知識或理論,成為現代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這也是現代人感到困惑的問題。
A.P.d'Entrèves認為,近代法理學興起有兩個標志,一個是摒棄自然法,另一個是以科學方法研究法律。[45]法學家往往宣稱他的理論建構是“建立在一個假設的前提上”。[46]現代法學流派或理論紛繁復雜就是因為假設不同,使碎片化成必然。在國際法中,“主權學說”“人權學說”就是建立在不同假設上,進而導致主權和人權成為國際法內具有內在矛盾性的權利。“知識產權”和“健康權”在實踐中的對立就是佐證。如對藥品知識產權的保護導致非洲大量病人得不到及時救助而妨礙了這些人的“健康權”。可見,不同職業群體根據偏好從不同假設出發所構建的理論或學說必然是碎片化的,有的甚至是矛盾的,是不兼容的。
此外,建立在不同假設上的理論或學說的構建不僅引發了知識的碎片化,更增加了知識的不確定性。因為假設會因無法證實、不符合實踐或偶然因素的介入而改變,使得構建的理論或學說有被推翻的可能。比如假設所有天鵝都是白的,但只要發現有一只天鵝是黑的,以該假設構建的理論或學說就會被質疑。因此,“科學家的基本工作便是去正確地選定他的假定,一旦這個假定不管用了,便會有摒棄它以及以更佳假定代替它的問題產生。”[47]
不同職業群體根據理性標準,適用科學方法構建理論或學說的行為割裂了人類整體知識結構,使得碎片化、不確定性成為現代知識的根本特征。根據群體偏好所構建的不同理論或學說,不是人類社會自然發展的結果,有的也無法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在工具主義橫行的現代社會,碎片化、互不兼容的知識理論或學說往往淪落為為同利益服務的工具,合法化決策中的任意性、專斷性成為強者控制弱者的工具。在國際社會,大國為己私利任意創制理論與權利的現象并非少見。最典型的代表是美國創制的所謂“事先防衛的自衛權”“先發制人”等權利和理論,使美國在全球任意、專斷使用武力和暴力合法化。
總之,從認識論角度看,國際法碎片化是啟蒙以來理性主義引發的知識職業化的必然結果,是根據理性排除、選擇、合法化觀念,用科學方法構建理論或學說體系的結果。因此,國際法從構建之初就是碎片化和不確定的,具有先天的不足和必然的缺陷。
隨著國際性法院的擴張以及國際性規范的激增,國際法內部繼續分化為無數亞領域,國際法碎片化進一步深化。解決國際法碎片化問題僅僅從國際法或整個法學內部探討是不夠的,因為它關涉到知識的本質,是認識論上的問題。因此,有學者認為,法律碎片化僅是根本的、多維度全球社會本身碎片化的暫時反映,全球法律碎片化不是法律規范或政策間的沖突,是現有法律無法解決的問題,要求采取新的法律取向。[48]新的法律取向該從何處開始是值得法律人思考的問題。筆者認為,首先,要破除對客觀理性的迷信。“西方社會瀕臨死亡,導致它死亡的主要原因是過于理性化,或者說理智過多,科學和抽象的知識過多,人類失去與自然的聯系,失去與神話和象征的接觸,失去與正確的宗教和語言的聯系。”[49]其次,豐富國際法實體規范。理性主義構建的國際法是極其簡化的規則體系,具有不可通約性,常處于沖突狀態。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主權國家似乎意識到應該確立一些普世的法律標準。”[50]普世的標準不能從職業化、專業化的法律體系中尋找,應當從榮格所說的“健康的原始主義”[51]中尋找;不能僅從西方為中心的倫理價值中尋找,東方傳統規范、倫理道德也可為普世的法律標準設定一些標桿。在價值衡量的諸多維度中,時間是重要的維度。“時間性是社會生活的重要維度,如果社會科學無視時間維度,將付出昂貴的代價。”[52]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應把傳統知識作為行為規范和指導。東西方傳統知識歷經時間的洗禮仍閃耀著光輝,彰顯著特有的價值,是現代人不可忽視的寶貴知識,可為緩解現代知識的碎片化、不確定性作出重大貢獻。
【參考文獻】
[1]Martti Koskenniemi.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R].New York: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2006:11-14.
[2]Andreas Fischer-Lescano and Gunther Teubner.translated by Michelle Everson.Regime-Collisions:The Vain Search for Legal Unity in the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Law[J].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3.999-1046.
[3]理查德·A·波斯納.超越法律[M].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44.
[4]Eliot Freidson.Professional Powers:A Study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Formal Knowledge[M].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22-33.
[5]William Goode.Community within a Community:The Profession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57,22(2):194-200.
[6]Magali Sarfatti Larson.The Production of Expertise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Expert Power[A].in Thomas L.Haskell.The Authority of Experts:Stud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C].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24.
[7]Magali Sarfatti Larson.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A Sociological Analysis[M].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40.
[8]Thomas L.Haskell.Introduction[A].in Thomas L. Haskell.The Authority of Experts:Stud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C].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xii.
[9]Magali Sarfatti Larson.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A Sociological Analysis[M].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14-16.
[10][11][16][17][49][51]羅蘭·斯特龍伯格.西方現代思想史[M].劉北成,趙國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231,181,4,590-612,607,385,420.
[12]Leon P.Baradat.Political Ideologies:Their Origins and Impact(11th ed)[M].Boston:Longman,2012:2-4, 8.
[13][43]野家啟一.庫恩:范式[M].畢小輝,陳化北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6-28,46-49, 56-59.
[14]Edward Mcwhinney.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Western Tradi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M].Dordrecht&Boston&Lancaster: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7:144-145.
[15]Eliot Freidson.Professional Powers:A Study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Formal Knowledge[M].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4.
[18]Emmanuelle Jouannet.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Sutcliffe.The Liberal-Welfarist Law of Nations: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150;Antony Anghie.Imperialism,Sovereign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48-49.
[19]哈羅德·J·伯爾曼.法律與革命(第一卷):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M].賀衛方,高鴻鈞,張志銘,夏勇譯.法律出版社,2008.33.
[20][21][45][46][47]A.P.d'Entrèves.自然法:法律哲學導論[M].李日章譯.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119, 97-101,107,107-108.
[22][24]Ludwik Fleck.translated by Fred Bradley and Robert K.Merton.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M].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22,100-104,48-50.
[23]羅伯特·所羅門.大問題:簡明哲學導論[M].張卜天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204.
[25]Alasdair MacIntyre.Three Rival Versions of Moral Enquiry Encyclopedia,Genealogy, and Tradition[M].Indiana 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0.225-236.
[26]阿拉斯戴爾·麥金太爾.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M].萬俊人,吳海針,王今一譯.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2.
[27]David Kennedy.Adress:Challenging Expert Rule:The Politics of Global Governance[J].Sydney Law Review,2005,27:5-28.
[28][39]David Kennedy.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History of an Illusion[J].QLR,1997,(17):99-138.
[29]Emmanuelle Jouannet.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Sutcliffe.The Liberal-Welfarist Law of Nations: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17.
[30]Emmanuelle Jouannet.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Sutcliffe.The Liberal-Welfarist Law of Nations: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17.
[31]Emmerich de Vattel.translated by Charles G.Fenwick.The Law of Nations or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Law Applied to the Conduct and to the Affairs of Nations and of Sovereigns (Preface and Introduction)[M].Washington D.C.: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1916:3,18.From:Emmanuelle Jouannet.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Sutcliffe.The Liberal-Welfarist Law of Nations: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64-66.
[32]Emmanuelle Jouannet.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Sutcliffe.The Liberal-Welfarist Law of Nations: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65-66.
[33]Irwin Abrams.The Emerg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Societies[J].The Review of Politics,1957,19(3):361-380.
[34]Martti Koskenniemi.The Gentle Civilizer of Nations: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Law:1870-1960[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125-127.
[35]Martti Koskenniemi.From Apology to Utopia: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Legal Argument[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123.
[36]John Westlake.Chapters on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4:vi.From:Antony Anghie.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49.
[37][38]L.Oppenheim.The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Law:Its Task and Method[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08(2):313-356.
[40][41]Emmanuelle Jouannet.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Sutcliffe.The Liberal-Welfarist Law of Nations: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110,19-20.
[42]Thomas L.Haskell. Introduction[A].in Thomas L.Haskell.The Authority of Experts:Stud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C].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 xi.
[44]安東尼·吉登斯.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M].田佑中,劉江濤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2.
[48]Andreas Fischer-Lescano,and Gunther Teubner,translated by Michelle Everson.Regime-Collisions:The Vain Search for Legal Unity in the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Law[J].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3:999-1046.
[50]Sandra.L.Bunn-Livingstone.Juricultural Pluralism Vis-A-Vis Treaty[M].Dordrecht&Boston&Lancaster: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2.303.
[52]Paul Pierson.Politics in Time:History,Institutions,and Social Analys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2.
(責任編輯:王秀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