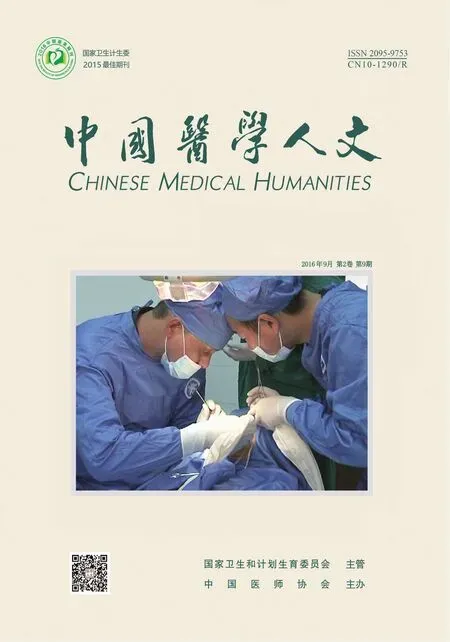西醫東漸中的女性
文/方益昉
西醫東漸中的女性
文/方益昉

伴隨筆者成長的意識形態語境,常將西醫入華路徑,定位于治病救人為輔,傳播福音為主。換句話說,醫學者,宗教伺女是也。雖說此類觀點不乏史實,但全盤認可之,卻又不免平添醫學史研究禁忌,限制學者的理性探索空間。比如,西醫東漸研究大多關注診療貢獻,有關其對中國社會的文明推動,當下學界涉足無多。
一般而言,境內最早的執業西醫,數1834 年到達廣州,畢業于耶魯大學的眼科醫生伯駕博士。如果算上19 世紀初年,十三行“自貿區”華洋結合,共同催生的痘局與痘師體系,“接種牛痘”預防天花烈性傳染,國民受益促進整體健康的預防醫學,西醫東漸領先機械電器輸入為代表的洋務運動,足足提前了幾十個春秋。
與稍晚洋務興國最大的不同是,西醫東漸進程中,華夏女性的獨特角色得以全面體現,她們既是西醫診療的受益者,也是西醫臨床的執業者。這一次,華夏女性沒有與歷史性機遇擦肩而過,她們擺脫了傳統約束的羈絆,在東漸西風中重塑人格價值。
催生醫學女性精英
近代醫學在華傳播,女性貢獻常被忽略,恐怕民國初年《近代中國留學史》難辭其咎。作者舒新城將女性出洋習醫的發端,定格于1914 年的庚款留美,有悖史實。大大低估了清末女性踴躍留洋,海外習醫、海歸行醫的規模。
比如,早在1885 年,寧波籍婦產科醫生金韻梅已經在紐約獲得醫學學位,她是與嚴復等留學歐洲學習先進技術的海軍軍官幾乎同時代出洋留學的知識女性。稍后留學美國習醫的女性,還有福州籍婦產科醫生許金訇,以及九江籍醫生石美玉和康愛德等。可以說,醫學女性的萌芽,沒有在成長節氣中耽擱。
比庚款留洋習醫女性早一步的還包括中國首位哈佛博士趙元任的太太楊步偉。1913年,時值23 歲的“大齡”單身楊小姐獲公費留學日本機會,她無懼世俗閑話,不惜再花費6 年時間專攻醫學,彌補當年痛失留學美國的遺憾。
原來,清末選拔首批庚款生時,有人提議給予女生6 個名額,直接從天津師范和南京旅寧兩所女校,各取前三名學生,免試出國。是年,19 歲的楊小姐雖名列旅寧女校前三甲,卻不得不遵從祖父在家自習的訓話。
“不然比我丈夫還早到美國一年吶”,面對第二批庚款生之一的老公,楊步偉感嘆終生。東洋學成歸來后,她立即開設北京森仁醫院,自任婦產科和小兒專科大夫。正是其舉止言談中洋溢的專業女性特征,深深捕獲了旅美海歸的趙博士。西洋、東洋二股西潮,最終匯流到同一個屋檐下。
以筆者家族的私人檔案為例,那段日子里,女性留學風潮甚至影響到了浙東的沿海小城。與外祖父同齡的7 位叔表兄弟姐妹,清末民初先后留學東洋,家族風氣之開明可見一斑。姊妹學醫歸來后,立即在家鄉從事現代婦產科服務,拯救生靈無數。當地民眾眼見為實,逐步放棄產婆習俗,普遍接受新式婦幼知識。民風漸開成主流,醫學進步融入百姓日常是特征。
值得強調的是,女性西醫人才的本土化培養,其發端與規模,比直接送學生出洋留學更早更具影響力。1879 年起,廣州博濟書院開始招收女生,女學生是婦產學科的主要授課對象,男生不得涉及,以免觸及傳統倫理綱常紅線。為此,博濟書院后期男生孫逸仙提出改革建議,獲當局采納。清末女子西醫學堂涌現,如廣州夏葛女子醫學校(1901年),天津北洋女醫學堂(1907年),北京協和女子醫學校(1908年),廣州赫蓋脫女子醫學專門學校(1909年)等,助職業訓練人才輩出。
各地教會資助留洋的首批醫學女專家,學成海歸后也積極參與培訓國內巾幗專業人員,使之大批成材,得以組建醫療服務先驅團隊。當年的女性醫務人員不僅成為史上婦女獨立行醫的開拓者,也是華夏職業化知識精英女性的先鋒隊,有別于1840 年后,開始活躍在城市洋場娛樂界和產業界,從事低技術含量的職場女性。
促進女性人格獨立
從大局看,上述女性培訓機構順應世界潮流,既呼應了全球各地掀起的女權運動,也為知識女性爭取了職業權利。特別是女性婦產科醫生批量執業,正好契合華夏文化中的性禁忌,即女性私處不得暴露于男性的傳統觀念。一定程度上,傳統文化倒也推動女性醫生群體崛起。晚清時節的沿海中國,前衛知識女性的集體亮相,與世界女權運動的節奏沒有完全脫節。
從女性患者考察,接受西醫診治的女性,在信賴西醫技術有效性的同時,文化上接受和重構了新穎醫患關系。通過遵循西醫診治,將隔帳搭脈等中醫習俗擯棄。追溯起來,這種全新醫患關系,始于19世紀30 年代伯駕來華初年。
耶魯大學醫學院圖書館現存伯駕(Peter Parker,M.D.)在華行醫記錄。諸如,13 歲女孩阿開,右邊太陽穴有巨大肉瘤。1837 年1 月19 日被麻醉后切除,14 天后痊愈。20 歲的楊施,頸部肉瘤下墜至臍部,手術切除后,楊家祖父寫下肺腑感謝狀,“秋菊初綻馥郁,謹以數語感念先生之大德與高技,今鄙孫子女得以康復,愿先生之名留傳千年子孫,愿先生之功德萬年遺福!花縣楊玉德”。
晚期乳腺癌患者占據伯駕醫案很大比例,得益于麻醉技術的及時引進,這批患者從此不必遭受以往醫術火烙乳癌的慘痛折磨。伯駕引進的外科手術,直接面對女性肉體,并未導致“男女授受不親”所宣揚的世風日下,還真堪稱女性福音。
雖說女性病家的康復療效與觀念改變,可以直接帶動親朋鄰里的文明觀感,但畢竟輻射范圍有限。唯有專業醫學女性的日常示范效應,才更具有沖擊固有生活模式的爆發力。比如,金韻梅大夫的女性著裝改良,引領時尚風貌,社會女性群起模仿。許金訇大夫則直接介入政治生活,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國際會議,稱許大夫為近代女性政治家先驅,似也名符其實。
對普通女性有示范性和啟發性的,是女性醫護人員潔身自好,自愿選擇獨身方式的比例相對高,以便最大服務社會,這是史無前例的中國女性獨立精神表達。經濟獨立起來的女性,更有能力自主選擇愛情、婚姻和家庭。1921 年6 月2 日,北京《晨報》刊出《新人物的新式結婚》。清華最年輕的趙元任教授迎娶北京森仁醫院院長楊步偉小姐。“青年導師”胡適證婚,“昨天下午三點鐘東經百二十度平均太陽標準時在北京自主結婚……他們申明,除底下兩個例外,賀禮一概不收。例外一:抽象的好意,例如表示于書信、詩文或音樂等,由送禮者自創的非物質的賀禮;例外二:或由各位用自己的名義捐款給中國科學社”。庚款留學生發起的《科學》雜志,首次從婚禮上募集公益善款。
一定程度上,移風易俗的新式婚禮,也與當年伯駕醫生帶來的理念更新有關。1842 年某日,伯駕醫生的好朋友、欽差大臣林則徐的助理、六品小吏李致祥,在十三行小教堂明媒正娶美國傳教士的女兒蘇珊小姐,堪稱史上首樁有案可稽的跨國婚禮。

西洋儀式結束后,男方在廣州城里安排了傳統拜堂,宴請200 多位賀喜嘉賓。據現已定居阿拉斯加的李氏家族嫡孫記載,當日婚宴僅13道菜,計有“永結同心、百年好合、鴛鴦戲水、紅鑾金鳳、如意吉祥、花好月圓、百子千孫和滿堂吉慶”等冷熱大餐與點心。
倘若此事屬實,相比道光年間農家土豪和氏族大戶的婚慶排場,此番李氏娶親真是既吉利光鮮,又移風易俗。過去幾年,伯駕、李致祥和蘇珊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在語言、文學和宗教諸方面互學溝通,衍生愛慕,完全合乎情理,且相鄰熟視無睹,社會習俗接納。
西風乍起不可收,沿海地區承受住了半個世紀的外來文化沖擊。上海、福州、天津,包括北京,出現培英、慕貞、中西等女校,女學素質教育為開拓女性職業化和專業化路徑夯實平臺。1900 年前后,女校出現在保守的中原地區,放開三寸金蓮就是女校的重要貢獻之一。
毫無疑問,醫學女性,特別是從事婦幼事業為主的女性醫務工作者,在涉及性、生殖、宗教和家庭等概念中,自身腦海首先激蕩,觀念重組,其日常言行自動成為社會時尚典范,推動對產婆、消毒、育兒、婚姻乃至女性獨身等生活習俗和社會模式改革。
也就是說,每次醫學新概念的引進,舊式家庭與傳統社會必將經歷從意識形態沖擊,到事實認可的進步軌跡。醫學女性的歷史貢獻,大大超出醫學范疇。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