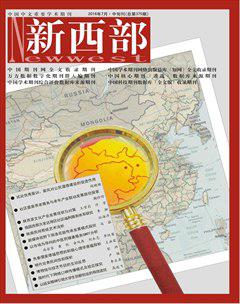先秦儒家德福思想的積極心理學意蘊探析
【摘 要】 本文闡述了積極心理學的思想旨趣,認為二千多年前的先秦儒家的德福思想展現出心理學界新興的研究領域積極心理學的深刻意蘊。在德福思想上,先秦儒家展現出對于主體努力提升人生價值的積極肯定與贊揚,他們非常重視培養積極的情緒感受,普遍重視積極努力的過程而相對輕視結果。先秦儒家德福思想的人文特質,從其積極心理學意蘊來看,能給現代人不少智慧啟迪,展現出深切的人文關懷。
【關鍵詞】 先秦儒家;德福思想;積極心理學
積極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作為心理學界興起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自20世紀末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后,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先秦儒者雖然距今已有二千多年,但其古老的思想不乏永恒的人文精神,先秦儒家早已經在其德福思想中展現出積極心理學的意蘊。正如積極心理學的倡導者美國學者泰勒所說:“雖然積極心理學是1998年才在美國創立的心理學新流派,但其核心元素很多都是來自于中國的哲學思想和世界觀。”[1]
一、積極心理學的思想旨趣
心理學家本來很少集中關注幸福,因為100多年來他們更為關注痛苦,就像積極心理學的開拓者當代認知心理治療的創始人之一馬丁·塞利格曼,他前30年的學術生涯都在研究“抑郁”。在對“習得性無助”的研究中,塞利格曼發現,無論鼠、狗等動物,還是人類,總有大約1/3的人不管經過多少電擊或者難題的困擾都不會放棄。對這個現象的探究最終促使他發起了“積極心理學”運動。
在積極心理學看來,幸福與不幸福的人,真正的區別在于,他們對于世界的主觀體驗與解釋不同,也就存在人生態度上的積極與否的問題。面對同樣的遭遇,幸福的人傾向于積極地、樂觀地解釋世界,從而不斷加固自己的幸福;不幸福的人恰恰相反,他們傾向于消極地、悲觀地解釋世界,進而不斷自我懷疑,從而加固自己的痛苦。明尼蘇達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戴維·賴肯(David Lykken)花了30年的時間,搜集和跟蹤調查4000對從1936年到1955年間出生的雙胞胎的信息。這些雙胞胎都在出生之際就分隔兩地,被不同的家庭撫養,人生遭遇也大相徑庭。但30年后,他們的行為方式和對幸福的體驗仍然驚人的相似。在分析比較了同卵雙胞胎和異卵雙胞胎的數據之后,戴維得出結論:一個人的生活滿意度至少50%取決于基因。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一個幸福的基本線,這個基本線是基因來決定的,無論你在人生中遭遇了什么樣的好事或者壞事,都會很快回到基因設定好的這個基本水平線上。而外部條件,比如收入、婚姻狀態、宗教和教育、家庭壞境等只占到8%,剩下的42%則歸結于人生的遭遇。一般來說,人對于外部環境的變化非常敏感,但一旦這些變化成為常態,人很快就會習慣新的環境,這就是“適應”原則。從生物學角度來理解,神經細胞對新的刺激物非常敏感,但習慣之后就會逐漸降低放電頻率。比如一個人突然中了巨額彩票,財富的暴漲過程會讓他感到非常開心,但一旦適應了奢華的生活,幸福感也很快回落到原來的水平。或者一個人突然癱瘓或遭遇車禍等意外事故,身體疾病或殘疾在一段時間里會讓他非常痛苦,但一旦傷殘成為事實,他會很快恢復到命運轉折之前的幸福水平。所以戴維教授最后得到結論說:“一個人想要變得幸福一點,就像妄圖增高一樣,基本屬于徒勞。”
但是,在戴維教授的理論基礎上,“積極心理學”認為,一個人的幸福受到基因的設定點、客觀環境以及主觀行動的影響。客觀環境指生活中無法改變的事實(如種族、性別、年齡、傷殘)和可以改變的事實(如財富、婚姻狀況、住址)。主觀行動則是個體選擇做的事情,比如冥想、鍛煉、度假等。在這個幸福的影響因素里,基因占50%,客觀環境占10%,主觀行動占40%。這樣的比例分配最重要的是傳達一種態度與旨趣:追求幸福并非捕風捉影,只要有行動、努力以及有效的技巧,便可以長遠地改變自己的幸福程度。腦神經學家也已經證實:大腦是可以改變的。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伴隨著他個人的改變,他的腦細胞或神經元會生出很多分支,在彼此之間創造更多的連接和路徑。與此同時,一些長期不用的連接與路徑也以同樣的速度遭到鏟除。這意味著,你個性的不同層面可以在腦中經歷生長、變化、消失、重建的過程,其中有天性的原因,也有教育、環境和自身努力的原因。天性樂觀者天生就在那個基本水平線上,天性悲觀者通過不同的方法改變大腦的運作,同樣也可以到達那個起點。
就心理學的自身發展來說,傳統心理學過于關注人性的消極方面,致力于消除人的心理問題與疾病,很少探究如何促進普通人的繁榮與發展。積極心理學則試圖扭轉這一趨勢,不僅研究心理問題和疾病,更集中關注人類的優點與積極特質,從積極方面增進普通人的幸福與發展。目前積極心理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人類的積極情緒與體驗、積極的個性特征、積極的社會性關系等在促進個人生存與發展方面的有益作用。這些積極心理學的理論特質與思想傾向在先秦儒家的德福思想中表現地非常突出。
二、先秦儒家德福思想的理論意蘊
在德福思想上,先秦儒家展現出對于主體努力提升人生價值的積極肯定與贊揚。先秦儒家在處理德福關系的問題上展示出限定主體性范圍的清晰視角,故有“在我者”與“在天者”的明確區分。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即得人爵,而棄其天爵” (《孟子·告子上》)。孟子的“天爵”與“人爵”凸顯了其德福思想的重要內容,顯示出對主體性努力結果的明確分析:“天爵”及“在我者”涉及到人的道德修為及德性境界,屬于人的仁義忠信等道德修養維度,而人爵涉及現實的官爵職位等,可代表現實的富貴財富等福報維度。天爵是人的仁義忠信等道德修養的結果,是在“天”所賦予人的一種內在品性下自覺修為的結果,是主體性努力的結果。而人爵涉及現實的官爵職位,突出表現一個人在社會中顯赫的現實職位及其所帶來的名利財富等。這些“人爵”需要適當的機緣條件才能實現,超出個人的努力范圍,是作為當政者的天子等所封賜的,這就涉及到現實的富貴財富維度所帶來的一切。孟子所看到的是,古代是處于理想的狀態下,表現為古人一生致力于修其天爵,由此而自然地獲得人爵,人爵是天爵修養的附屬產物。但現在世風不好,今人修其天爵有極強的目的性,也可以說有虛偽性,是為了得到人爵所帶來的富貴財富等;很多人得到人爵,就放棄了天爵,使天爵成為工具性的存在,如敲門磚似的,敲開門就扔掉了。孟子顯然否定將天爵作為工具性存在的今人做法。所以主體性努力的結果與現實的富貴財富沒有必然的關聯,人們所能夠期望的是修養自身 所帶來的德性境界的提升。
在孟子看來,道德修養境界所能夠帶來的幸福和人們現實所獲得的各方面幸福屬于不同的層次。道德修養境界所能夠帶來的幸福屬于主體不斷努力發掘人的內在層面而得到的結果,人們現實所獲得的各方面幸福屬于與主體努力無關的外在于人的層面。“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盡心上》)。道德修養境界的主體把握權在每個人的內心。只要個體自我好好地去努力修養,就能夠達至,獲得由此帶來的有益自身的結果。在這方面,個體努力程度和道德修為的結果多少是成正比的。如果個體放棄努力,就會失去由此而來的幸福,因為這是“求在我者”,天爵就是在我者。而人爵一類的幸福,個體也可以去努力追求,但得到或得不到,不是由個體所決定的,有很多超出個體之外的因素,孟子歸之于“命”。這方面的追求對于得到沒有必然的幫助,這是求在外者,不是我們本人所能夠完全決定的。可見,孟子的“天爵”與“人爵”、“在我者”與“在外者”的區分更大程度上是從“人事”與“天命”的不同意義上來談論人生所得與人生追求,這是儒家處理道德與幸福關系的一貫理路。在儒家看來,“天爵”、“在我者”更關涉道德修為的維度,這個維度是主體能自由把握的。“人爵”與“在外者”并不必然與主體努力相關,這與道德努力所能達到的范圍并不必然相關。而之所以清晰地劃分這樣兩個層次,儒家是要人致力于主體性的努力,而坦然面對現實生活中的得與失。
先秦儒家非常重視培養積極的情緒感受。孔子強調學之樂趣,我們從熟悉的《學而篇》第一章就可以感受到。“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論語·學而》)孔子贊賞的是愉悅積極地充實生命,在樂的狀態下堅持自己的正大光明的價值追求。所以先秦儒家更強調道德修養所帶來的精神上的愉悅。孔子最喜歡的弟子是顏淵,他多次贊揚顏淵好學,非常欣賞顏淵之樂。孔子說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顏淵之樂與一般人所樂有非常大的不同,不是因為擁有財富、富貴名利之類而快樂,而是在追求理想之道的過程中“志于道”而獲得的精神愉悅。很多人處在艱苦的物質條件下會感覺痛苦不堪,絲毫不覺得有什么幸福,但是顏淵在艱苦的物質條件下卻能保持快樂的狀態,這是孔子所主張的君子應該具有的精神追求。孟子也稱贊顏淵之樂。孟子曰:”顏子當亂世,居于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孟子 ·離婁下》)。這是在個體方面,先秦儒家更多地關注道德修養所帶來的精神愉悅,而不太特意關注形而下的物質生活。并非儒者輕視物質生活,而是在精神追求的過程中會自然而然的忘卻其他。
先秦儒家普遍重視積極努力的過程而相對輕視結果。在德福關系問題上,先秦儒家也確定德福一致的一定范圍性存在。[2]自帛書《周易》經傳出土以來,學界逐漸達成共識,認為今本、帛書《易傳》基本代表了先秦儒家的思想,跟孔子有很大關系。《易傳》中非常顯著地表達了積善成福的思想:“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秧”(《易傳·坤·文言傳》)。這句話突出表現了人們一般所認為的因果報應思想,道德行為與所獲得的結果具有對應關系。如果仔細分析一下,德福的一致性也具有合理性。只是善惡報應的內容非常廣泛,不一定按人們希望的方式呈現,也未必當時當地就能呈現。所以如果把福報的內容無限擴大化,盡量廣的視野,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道德與幸福應該具有一致性。只是對于一般人來說,未必能如人所愿,很多時候會受到自我視野的限制。如一些人想得到財富,就會一心盯著財富的多寡,忽略了其他擁有的幸福。一些人盯著健康或美貌,就對自己不如人的狀態耿耿于懷,很難感受到自己擁有的其他幸福。帛書《易傳·要篇》中孔子也提出:“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這里首先展現出孔子對待占筮的基本態度,同時也顯示出孔子的基本德福觀。儒家并非不求福,不求吉,儒家的求福、求吉有個非常必要的前提就是尊德性、行仁義。所以儒家并不否認德福之間是有一致性的。由此儒家更重視德性境界的修行,而不太關注世俗所沉迷的富貴名利等現實所得所代表的各種福報。
在德福思想上,先秦儒家看到了富貴財富的必要性與有限性。孔子承認富貴財富是人們本性所想要獲得的。他承認“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論語·里仁》)。孔子也不反對人們花費時間精力去追求它。《論語·述而》中孔子講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特別是對于廣大民眾的“民之利”,對于滿足人類基本生存需要的“飲食之利”,以及通過正當方式取得的“利”等的倫理正當性是持肯定態度的,所以孔子提出了“先富后教”等思想(《論語·子路》)。
但是我們更為看重的是孔子在義利觀上的主張——“見利思義”(《論語·憲問》)、“見得思義”(《論語·子張》)。在孔子看來,作為有自覺力的人類,與有益自身的利益相比較,符合道德原則的“義”的價值選擇永遠具有優先性。甚至為了“道”的追求,個體可以無視關系現實福祉的眾多方面。所以孔子多次論述了志于道而無視現實物質條件的君子境界。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論語·學而》),也提出“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主張“君子謀道不謀食”(《論語·衛靈公》)。志于修為自身的君子,也是道德修為之主體,在追求自己理想之道的過程中,并不太在意形而下的現實生活,特別會忽視一般人所具有的衣食需要。
三、先秦儒家德福思想的現代啟示
先秦儒家的德福思想顯示出幸福生活更多地在于奮斗的過程而不是目標的達成。我們從孔顏樂處中可以看到,儒者在追求理想之道的過程中即使客觀條件很惡劣,即使在別人看來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但是他們內心是快樂的,顏子不改其樂。顏子之樂不在于他達到了他理想之道,達到了圣人境界,而在于他不斷的追求,一直處在在努力修養自身道德境界的過程中。所以積極心理學的倡導者泰勒·本——沙哈爾認為幸福的生活應該是快樂和意義的綜合體。幸福不能沒有快樂,同樣幸福也不能缺少意義,幸福必須包含快樂和意義。快樂是主觀感受到的快樂,意義既有自己肯定的意義,也有社會承認的意義。你認為你做有意義的事情,同時你在整個過程中也是感到快樂的,這種生活是幸福的生活。沙哈爾在他的著作《幸福的方法》里詳細闡明了這種觀點。
先秦儒家既看到了衣食富貴的必要性也看到了在價值選擇維度上的有限性。儒家并不否認物質性幸福在人生中的重要性及能給人帶來的積極意義,但他們更為重視的是“義”的價值選擇對人的積極影響。實際上物質幸福與道德幸福本身也應是相互促進,不一定非要對立才可。
在我們這個經濟空前發展、技術日益進步的時代,很多人將財富的積累作為人生的最大目標,所以會很容易高估金錢的力量。并不是說賺錢或擁有財富不能作為人生的一個重要奮斗目標,因為物質上的富有確實可以一定程度上幫助個人體驗到更多的幸福。金錢的保障,可以讓我們更為自由地選擇我們的生活方式,或者讓我們不為賬單而煩惱。而且,賺錢的欲望有時可以成為積極的挑戰,調動一個人的積極性,甚至給我們啟發。但是金錢本身并沒有價值,金錢的價值在于它是實現目標的手段,它可以借助主體的運用給我們帶來豐富的經歷。但是物質財富本身不經過主體的轉化并不能給生命帶來意義或者是精神上的財富。
一些研究顯示,財富與幸福的關聯度并沒有我們想象中那么緊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做的有關幸福的調查中,心理學家發現,幸福和財富的關聯性非常低,除非在一些極其窮困的地區,在很多人基本的生活條件都得不到滿足的條件下,物質與幸福具有緊密相關性。在一些研究案例中,財富與幸福甚至完全不相關。而且在許多國家,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很多中國人的經歷顯示,人們的主觀幸福感并沒有隨著他們財富的增長而普遍地提升。另外,還有一些大家都知道的證據:一些百萬富翁遠沒有人們想象中那么快樂,中彩票也不常使人們幸福,同時也存在一些“快樂的窮人”等。一些研究發現,中巨額彩票的人經常在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就恢復到原來的幸福水平,如果在中彩之前是不幸福的,那在中彩后很快又恢復到不幸福的狀態,如果原先就是快樂的,也會恢復到原先的水平。
強調人生的積極面可以讓人們更多地感受幸福。一個簡單的實驗顯示,閱讀經過篩選后單詞流的積極與否也會影響情緒。當你閱讀一些積極的單詞,比如感激、樂觀、振奮、希望時,會刺激大腦的左前額葉外皮區,釋放大量的血清胺,創造快樂的情緒;但當你閱讀一些消極的單詞,比如憤怒、悲觀、無望時,右腦會產生激素壓力,你會感到胸悶壓抑。“積極心理學”開發了數百種可以增加幸福感的訓練方法,其中最為有效的包括做慈善,記錄快樂的事情,表達感激和樂觀,視覺化最好的自己,應用強項力量進入“流”的狀態,追求更高的人生意義等等。這些行為是經過大腦選擇和決定的,引導你對平日忽略的人和事給予更多的關注,它們直接與“適應原則”沖突,不讓你將生命中的一切視作理所當然,這樣獲得的幸福感往往持續較長時間。而這些增進人生積極面的方式方法都蘊含在先秦儒家的德福思想中。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先秦儒家的德福思想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特質,在現代社會依然有不可忽視的價值,特別是從其積極心理學意蘊來看,能給現代人不少智慧啟迪,展現出深切的人文關懷。
【注 釋】
[1] (以)沙哈爾著;汪冰,劉駿杰譯,汪冰審校.幸福的方法[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
[2] 已有一些研究涉及儒家德福思想的內在復雜性。如王中江從郭店簡《窮達以時》及相關文獻來考察孔子的德福觀,指出孔子得出了與已有的德福一致主張不同的“德福未必一致”的新主張,并且為窮困賦予了不同于世俗的積極意義,認為追求美德和自我完善本身就是幸福和快樂的。參見王中江:“孔子的生活體驗、德福觀及道德自律——從郭店簡《窮達以時》及其相關文獻來考察”,《江漢論壇》,2014年第10期。史懷剛認為孔子雖強調以德求福,但并非單向度的德福因果報應論。參見史懷剛:“鬼神、道德、幸福——孔子、老子、墨子三家幸福觀試較”,《孔子研究:學術版》,2014.6.
【作者簡介】
王洪霞(1983.11-)女,山東臨沂人,哲學博士,浙江財經大學講師,研究方向:中國傳統倫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