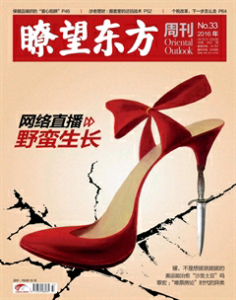老人為何成易騙群體
當(dāng)心理因素和社會環(huán)境疊加時,老人自然成了狼群中的羊
5年前的一天,剛剛退休的何芳珍在單位的老年大學(xué)門口遇到了一位“熱心”的保健品推銷員。兩人一番攀談后,她被帶去參加了一場健康講座,隨后給自己和老伴買了幾萬元的保健品。
彼時,身為醫(yī)生的何芳珍對保健品功效深信不疑,一度還覺得自己找到了對抗疾病的靈藥。不過,一年后她就發(fā)現(xiàn)自己被騙了,“這些產(chǎn)品根本沒什么神奇功效,吃了一年也沒任何用。”
這次經(jīng)歷讓何芳珍備受打擊,也讓她開始關(guān)注老年群體的受騙問題。原本以為自身經(jīng)歷只是個案的她,在過去幾年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老年人被騙已經(jīng)不再是小概率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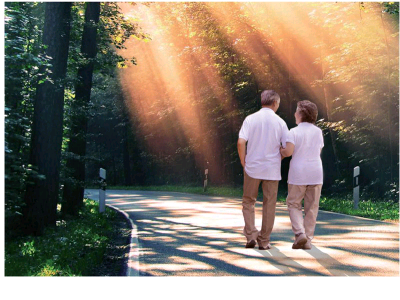
在中國,有一個龐大的群體,盡管可能分布于不同的行業(yè),但其商業(yè)模式就是以騙老人錢來獲取暴利。
“我身邊很多親戚朋友都被騙過。”如今身為華中師范大學(xué)老齡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的何芳珍對《瞭望東方周刊》說,更令人擔(dān)憂的是,這一問題正變得越來越嚴(yán)重,“受騙的老人也越來越多”。
除與健康相關(guān)的產(chǎn)品之外,理財、旅游、收藏領(lǐng)域都已經(jīng)有公司專門開發(fā)出針對老年人的“陷阱”,比如高收益的線下P2P產(chǎn)品,團(tuán)費(fèi)便宜、主打購物的老年旅游團(tuán),以及專門針對老人的藝術(shù)品、紙幣、郵票收藏,等等。
“基本上只要是老人們感興趣的領(lǐng)域都陸續(xù)出現(xiàn)了專門針對他們的騙局,可謂防不勝防。”何芳珍說。
被利用的孤獨感
“很多受騙老人甚至因為孩子的反復(fù)勸阻跟孩子決裂。”鄭州市食藥局食品藥品稽查人員邢杰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他曾多次處理過老人保健品受騙案件。

2011年11月28日,蘭州市西固區(qū)部分受騙老人展示他們加入的空頭協(xié)會“會員證”,聲討保健品詐騙團(tuán)伙。蘭州市城關(guān)區(qū)、七里河區(qū)、西固區(qū)出現(xiàn)多個保健品推銷團(tuán)伙詐騙老人的案件,涉案金額達(dá)數(shù)百萬元
邢杰直言,到食藥局報案的老人中70%都是被子女逼著來的,并非自己想明白了而來,“很多老人一旦上當(dāng)就難以自拔,外界勸說根本無效,直到錢被騙光,騙子不理他們了才會發(fā)現(xiàn)自己上當(dāng)了。”
何芳珍最初也難以理解,那些極其拙劣的騙術(shù),老人們?yōu)楹紊钚挪灰伞5谑占⒎治隽酥T多案例后,她找到了答案,這些騙局無疑都迎合了老人們希望安享晚年的普遍心理。
“老人退休后,家庭負(fù)擔(dān)、工作負(fù)擔(dān)、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大大減輕,身體又或多或少都有些小毛病,加上‘看病難的現(xiàn)實,正好成為滋生保健品或功能器械類騙局的溫床。”何芳珍說。
心理學(xué)專家褚衛(wèi)東則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老年人退休后關(guān)注焦點變窄,除了親情就是健康。而對健康的過度關(guān)注,容易無節(jié)制地購買保健品。再加上對市場上名目繁多的保健品缺乏辨別力,最終就會導(dǎo)致上當(dāng)受騙。”
比如,每月只有4000多元退休金的詭連勝,卻愿意一次購買3000元保健品,而且他在幾個月內(nèi)先后扔進(jìn)去了1.5萬元,幾乎用完了他不多的積蓄。
更重要的是,多數(shù)老人的子女不在身邊,他們實際處于獨自或僅與配偶居住的狀態(tài),也就是俗稱的“空巢老人”。
國家衛(wèi)計委發(fā)布的《中國家庭發(fā)展報告2015年》顯示,空巢老人占老年人總數(shù)的一半,其中獨居老人的占比接近10%,僅與配偶居住的老人占41.9%;預(yù)計到2030年中國的空巢老人家庭占老年人總數(shù)的比例將達(dá)到90%。
這些空巢老人退休后脫離原有的工作環(huán)境,社交圈變小,很容易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孤獨感。
“這種孤獨感以及對子女的牽掛易使老人們產(chǎn)生移情,從而容易對與其子女年齡相仿的年輕人產(chǎn)生好感。”褚衛(wèi)東指出,當(dāng)前涉老騙局中的銷售人員恰以20歲左右的年輕人為主。
年輕的施騙者多能抓住老年人渴望溫情和關(guān)注的心理,通過“貼心周到”的服務(wù)獲取老人的信任,最終誘騙老人購買其產(chǎn)品。這也是他們屢屢得手的關(guān)鍵因素。
愛占小便宜更可怕
當(dāng)然,除了心理上的孤獨感,多數(shù)老人退休后的生活也乏善可陳,容易產(chǎn)生失落感。
這些人在退休前多處于忙碌的工作狀態(tài),為生活奔波;有些人退休前還處在領(lǐng)導(dǎo)崗位,備受尊敬。而一旦離開工作崗位,社會能夠為這些老人提供的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平臺十分有限,老人們因此容易產(chǎn)生較強(qiáng)的心理落差,從而激發(fā)出更強(qiáng)烈的被尊重的心理需求。
這也成為很多施騙者的突破口。
本刊記者“入職”的一家以老人為目標(biāo)客戶的線下P2P公司正是抓住了老人的這種心理,通過舉辦中老年歌舞比賽吸引后者購買潛在風(fēng)險極高的理財產(chǎn)品,甚至還有企業(yè)請老人做形象代言人。
“這些做法恰好迎合了老人們渴望社會尊重的心理,致使老人們漸失防備之心,最終落入圈套。”褚衛(wèi)東說。
不過,在他看來,老人們存在一個更為可怕的心理——愛占小便宜,“這種心理也經(jīng)常被施騙者利用,后者往往以免費(fèi)贈品為餌,獲取老人們的個人信息,最終一步步將老人誘入精心設(shè)計的騙局中。”
“殊不知,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免費(fèi)贈品最后還是由老人們埋單。”何芳珍說,很多老人之所以反復(fù)受騙,原因正在于此,“一袋洗衣粉可能要用幾千元的產(chǎn)品去換。”
本刊記者“入職”的一家保健品銷售公司在向老人兜售產(chǎn)品之前,就免費(fèi)贈送了多件號稱價值不菲的禮品,且規(guī)定老人只有購買產(chǎn)品才能獲得贈品,致使現(xiàn)場出現(xiàn)了搶購“盛況”,一些老人為了多獲得禮品,一次性購買了1.2萬元保健品。
也有一部分老人是出于減輕子女負(fù)擔(dān)的心理,購買保健品或者投資理財。“很多老人認(rèn)為生病不僅會加重子女的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還需要子女照顧。因此不如自己保健好身體,讓子女安心工作。”何芳珍說。
本刊記者接觸到的一位深陷P2P騙局的老人就坦言,自己投資理財主要是想多賺點錢,以減輕子女的生活壓力,甚至可以為子女留下一筆可觀的遺產(chǎn)。
當(dāng)然,從社會角度分析,這些老人多出生于上世紀(jì)50年代前,受歷史條件的限制,文化水平普遍較低,并缺乏健康常識。
據(jù)何芳珍介紹,中國人的健康素養(yǎng)水平僅為6.48%,其中具備基本健康知識及健康理念的人只占14.97%,“這說明中國老人的‘醫(yī)盲比較多,更容易被忽悠。”
誰更容易被騙
在老年群體中,具有某些特質(zhì)的老年人似乎更容易掉進(jìn)施騙者的陷阱。
一般認(rèn)為,受教育程度低的老人更容易受騙。但這并不意味著高學(xué)歷者可以幸免,比如何芳珍。
本刊記者在調(diào)查中曾“入職”一家專門以老年人為目標(biāo)群體銷售功能器材的公司,其負(fù)責(zé)人張偉明表示,這些擁有一定知識背景的老人警惕性通常很高,較為固執(zhí)自負(fù)。這樣的人不容易上鉤,而一旦上鉤就會很舍得花錢,成為穩(wěn)定的“鐵粉”。
此外,作為社區(qū)或圈子中有影響力的“意見領(lǐng)袖”,他們甚至?xí)瘛白詠矸邸币粯酉蚱渌先诵麄鳟a(chǎn)品。
因此,該公司將那些國營單位、研究院所、高校的家屬院作為主攻區(qū)域,重點尋找這類老人。
此外,相較于針對一般老年人的“溫情牌”,這類高知老人更喜歡“尊敬牌”。
張偉明稱,“這些老人以前在單位里多是有身份的人,呼風(fēng)喚雨的,我們必須表現(xiàn)出足夠的尊敬,見面不能稱大爺大媽,而是稱他以前的職務(wù),比如局長、教授、老師等。”
如果做到這些,這類老人就很容易絕對信任公司,從而一步步進(jìn)入公司為其設(shè)計好的陷阱之中。張偉明說,一個退休教授就一次性買了5萬多元的產(chǎn)品,還拉來了好幾個朋友。
褚衛(wèi)東認(rèn)為,從心理學(xué)的角度來說,一般孤僻內(nèi)向、缺少交往對象的老人更容易受騙,“因為這些老人在被關(guān)心、被理解的心理需求獲得滿足后,反而會更容易相信他人。”
找不出破綻的騙局
在一年多的藥品稽查工作中,邢杰接到過幾百起有關(guān)老人買保健品受騙的投訴,其中最可憐的一個孤寡老人,辛苦攢了半輩子的十萬元養(yǎng)老錢被騙光。
這讓他又恨又無奈,“恨的是老人們對這么低端的騙術(shù)毫無辨別能力,無奈的是我們拿這些施騙者基本上沒有辦法,只能眼睜睜看著老人們一次次被騙。”
這與外界的期望完全相反,但卻是不爭的現(xiàn)實。“很多受害者遇到這種事情第一時間想到的是食藥部門,實際上食藥部門只監(jiān)管產(chǎn)品的質(zhì)量問題。”邢杰說,“尷尬就在這兒。”
“我們?nèi)ガF(xiàn)場一查發(fā)現(xiàn),這些公司賣的保健品都是有正規(guī)批號的,沒有任何問題。”邢杰說,這致使食藥部門無法查封產(chǎn)品,更沒有依據(jù)處罰涉事的保健品銷售公司。
這正是何寧、張偉明這類公司的“聰明”之處,它們并不生產(chǎn)產(chǎn)品,而是從正規(guī)廠家采購,“這樣既能做到不違法,也能減少成本投入,但缺點就是能選的產(chǎn)品很有限,市面上所賣的產(chǎn)品重復(fù)性也很高。”
在最被詬病的價格問題上,監(jiān)管部門也無法干涉。
比如何寧公司售賣的1500元一盒的參加茸口服液批發(fā)價在45~50元之間,張偉明公司售賣的2萬元的功能床墊批發(fā)價只有2000元,一瓶售價600多元的保健醋批發(fā)價只有20多元等。
“售賣價格基本都是實際價格的幾十倍,這些騙子公司賺的就是這個錢,但這是一個愿打一個愿挨的交易,政府部門也沒法硬性規(guī)定產(chǎn)品的市場售價。”邢杰說。
這樣的執(zhí)法窘境并非只在保健品受騙案件中存在,包括功能器械、P2P理財、老年旅游、藝術(shù)品投資、紙幣收藏等騙術(shù)都很難找到違法破綻,令監(jiān)管部門無法下手。
在邢杰看來,幾乎所有針對老年人的騙術(shù)最大問題在于虛假宣傳,刻意夸大產(chǎn)品的功效或價值,“比如保健品嚴(yán)格來說是保健食品、不是藥品,不能公開宣傳其療效,只能說有輔助功效。”
但夸張宣傳只是銷售人員的口頭講述,并非貼在產(chǎn)品標(biāo)簽上,這就增加了執(zhí)法部門的取證難度,“我們一到現(xiàn)場,人家就不講了,再者那些受騙的老人也多數(shù)不愿意配合取證。”邢杰說。
“這種情況下,只能從老人身上下功夫,讓他們明白這是一個騙局,自動遠(yuǎn)離。”何芳珍說,但老人一旦步入施騙者的圈套便很難自己走出來,子女要多下功夫。
“如果子女只是一味地訓(xùn)斥老人,不會起作用,可能情況更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真正關(guān)心父母,讓他們不至于孤獨到去銷售保健品的公司那里得到滿足感。”不過,何芳珍也說,這并非易事。
(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