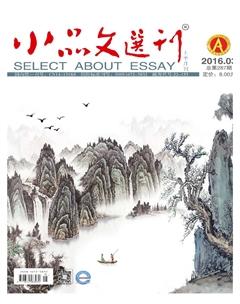中國鮑魚與法國蝸牛
單之薔
燕窩、鮑魚、魚翅、海參是中國人的四大美味。我在宴會上吃過幾回鮑魚,但未留下印象,如今找來一些書,想了解鮑魚究竟味美在何處,結論竟是鮑魚無味。鮑魚的味完全是靠鮑汁慢慢地煨進去的。鮑汁是店家的秘密,大體是用雞、鴨、干貝、火腿等制成的。
魚翅也如此。原料本有些許腥味,需加工成徹底無味的干貨,才能做成魚翅菜。魚翅之味也是外加的翅汁之味。
這些美味不僅無味,而且無用。有人千方百計想從營養學的角度論證它們應當位居中國菜之首,但科學檢驗的結果是:一只鮑魚的營養大抵只相當于一個雞蛋,一碗魚翅約等于一碗粉絲湯。
為什么這些無味、無用的東西成了中國人的“至味”?人們為什么愿意花數百、數千元去吃一只鮑魚或一碗魚翅?
其實,燕窩、鮑魚、魚翅、海參妙就妙在無味和無用上。從哲理的角度看,任何一種味道都是一種規定和限制,都是有限的、相對的,是可以超越的,只有無味才是絕對的,才能成為“至味”,因此大味無味。
無用也很關鍵。無用正是燕窩、鮑魚、魚翅、海參成為頂級菜的奧秘所在。法國有本書———《有閑階級》,書中的一個觀點是:“有閑階級”家中的陳設、所玩賞的東西,一言以蔽之,都是無用的。用文一點的話說,就是沒有功利性,如貴婦養哈巴狗,而不養獵犬或牧羊犬。
雖說燕窩、鮑魚、魚翅、海參無特殊的營養保健功能,但有一種作用卻是暗含的,那就是為人群劃分階層。現代都市不像鄉下,一個人是否有錢、有權很難識別,因此,度假,購物,車、服裝這些暗示支付能力的細節綜合起來,就起到了劃分階層的作用。食品作為劃分階層之用,確實難以找到比燕窩、鮑魚、魚翅、海參更合適的了:稀有而昂貴。
稀有的東西種類很多,但要成為劃分階層的東西,還需要很多條件。這有點像股票,一只股票價格要漲起來,一定得有能夠炒作的題材,要給人以想象的空間。燕窩、鮑魚、魚翅、海參就很符合這些條件。
鯊魚,大海的神秘主人,處于生物鏈的頂端;魚翅,鯊魚的鰭。看過海明威《老人與海》的讀者能體會到,人類如果不和科學技術聯手,要在大海里抓到一條大魚是何其難啊,更何況是鯊魚。那時的魚翅仿佛是虎口拔牙、龍頭割須后的戰利品,因此吃魚翅還不會對鯊魚構成嚴重威脅。燕窩———尤其是來自南洋婆羅洲的金絲燕的燕窩,有許多激發想象力的因子:婆羅洲,能喚起一種異國風情的感覺;金絲燕的唾液(有的說是喉間分泌物),不僅能想象其珍稀,還有一種浪漫的情調。假如燕窩不是小巧玲瓏的金絲燕的唾液(或喉間分泌物),而是黃牛或野豬的,我想無論如何也不會成為名菜。
我發現各民族的頂級名菜,大多是舍近求遠,多是這個民族不熟悉的東西,如中國的鮑魚和法國的蝸牛。原因是它們不僅稀有,而且令人有想象的空間。中國文化的主體本是一種農耕文明,然而我們的四大美味卻全部來自海洋或海島,而號稱擁有海洋文明的西方人的名菜,卻大多來自陸地。如:法國人的美味除了蝸牛,還有一種山菌,價比黃金;德國人的“至味”是一種筍;日本是一個島國,名菜卻不是魚,而是來自中國青藏高原的一種蘑菇———松茸,一根可賣上千日元。
享用稀有資源,以標示身份的等級,這是人類文化的一大弊病。這種文化的要害是越稀有越想占有。正是這種文化吃光了野生的鮑魚和海參,人們不得不求助于人工養殖。如今這種文化在現代科技的配合下又指向了鯊魚。吃魚翅還帶來了是否人道地對待動物、合理地利用資源等問題。我尤為擔心的是,某一天我們會看到一片海域被圍起來,一塊牌子豎起來:鯊魚養殖場,這意味著野生的鯊魚已經瀕臨滅絕。我不認為養殖的鯊魚能替代野生鯊魚:養殖場中一萬條鯊魚也不如大海中的一條鯊魚,因為養殖的鯊魚已經脫離了自然的生物鏈,無法發揮它在原生態系統中的作用。還有,從美的角度看,野生的與家養的也不可同日而語。
我感到奇怪的是:吃魚翅所帶來的生態問題為什么今天才被提出來?如今北京的魚翅店越來越多,每年要吃掉100多萬條鯊魚,而且這個數量還在不斷增加。是否已經到了“救救鯊魚”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