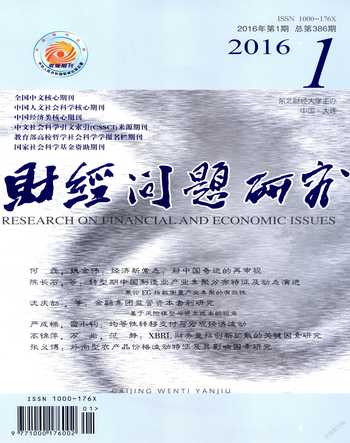經濟新常態:對中國奇跡的再審視
何磊姚金偉
摘 要:中國經濟奇跡能否延續,經濟新常態是關鍵,而經濟新常態則由政治新常態所決定。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基本啟示是,政府主導是中國經濟奇跡的前提。然而政府對經濟的監管,在官僚自利主導下逐漸異化為政府管控,由此造成市場化進程中的機會主義盛行。與中國經濟奇跡相伴而生的是扭曲的經濟結構、不規范的市場以及政府掠奪性行為。中國改革已步入深水區和攻堅期,深化改革所釋放的制度紅利成為下一步發展的關鍵。新一屆政府以作風建設和強力反腐作為突破口,推動政治變革,加速經濟轉軌。與經濟新常態相伴而生的是政治新常態,究其內涵,除了規范市場和強化法治外,服務型政府及專家治國體制均是必要的。一個監管而非管控市場的政府、一個崇尚法治的服務型政府、一個官員精于治理而不背政治包袱的政府,主導著規范而非扭曲的市場經濟,構成了中國經濟新常態的重要內涵。
關鍵詞:中國奇跡;經濟新常態;政治新常態;東亞奇跡;官僚自利
中圖分類號:F12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6)01000307
一、引言:危機與復興
亂而思定,新常態的前奏是經濟危機。“新常態”(New Normal)一詞最早于2009年初為全球最大的債券基金——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提出,旨在概述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經濟特別是發達國家所發生的變化。隨后引起美國各大主流媒體熱議,新常態逐漸成為全球經濟掙脫衰退的心理預期。而肇始于美國次貸危機的全球經濟危機破壞力的確驚人,發達國家經濟體普遍陷入低增長(甚至負增長)和高失業狀態,政局動蕩、社會騷亂不斷。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亦受全球經濟危機的沖擊。然而不同于發達國家經濟體,中國更多地體現了新興國家經濟體的經濟發展特征。中國學者對新常態的最初討論也是針對后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尤其以林毅夫\[1\]和李揚\[2\]為代表。而在2012年政府更迭之際,針對中國本土經濟環境的討論也被賦予了新的內涵,黃益平[3]和姚洋[4]等學者以及中信證券和安信證券等金融機構紛紛預測了中國經濟即將面臨的下行和結構性調整趨勢。眾所周知,中國經濟奇跡得益于政府刺激,特別是政府主導性投資和晉升激勵\[5\]。新一屆政府嚴懲腐敗、嚴抓政府作風建設,地方政府已不能靠GDP“一俊遮百丑”,地方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經濟增長乏力是客觀事實。有論者稱,2015年中國經濟將游走在通縮與擠泡沫的窄道之間\[6\]。中國經濟新常態的言外之意是中國經濟增長形勢不容樂觀。
經濟新常態折射出政治新常態。經濟現象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與政治問題密切關聯,中國尤其如此。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所取得的成就被看做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合法性的堅實來源\[7\]。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內涵看,最高領導人的執政綱領均旨在促進經濟“更好、更快”地增長:鄧小平理論奠定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制度框架,“三個代表”的重要指導思想倡導技術革新和新興產業,科學發展觀要求政府規范經濟增長。伴隨著中國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中國經濟快速推進進程中所積壓的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對經濟增長進行結構性調整勢在必行;而調整結構的前提是給經濟增長降溫,先讓經濟增長緩行。2014年5月,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首提新常態,這是新一屆政府對中國經濟形勢的政治引導。緊接著,在11月舉行的APEC峰會上,習近平對經濟新常態進行了進一步的闡釋:速度上,“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結構上,“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動力上,“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同時,他還進一步指出“政府要簡政放權,為市場進一步釋放活力”\[8\]。經濟新常態意味著新任領導人容忍經濟放緩、堅持改革、堅定轉變發展方式,這是中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論自信的直接體現。與經濟新常態相伴而生的是政治新常態,根本意義而言,一個怎樣的政府引導怎樣的市場經濟構成了中國新常態的討論焦點。
二、中國經濟奇跡:1978—2012年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經濟增長成就斐然,同時也耐人尋味。圖1報告了1978—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狀況。具體而言: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3 650億元激增至2012年的534 123億元,年均增長率為993%;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382元激增至2012年的39 544元,年均增長率為882%。從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經濟增長波動看,“干中學”式的漸進主義路徑著實影響深刻。經濟周期是中國經濟發展進程中“學習式增長”的生動體現,而這同政治更迭密切相關,因而中國的經濟周期研究普遍被看做政治經濟周期。有學者指出,1978年以后中國資本形成總額、投資、信貸、M2和通脹率等宏觀經濟變量同官員的政治換屆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周期性波動,“政府主導經濟增長、政治集權和經濟分權以及政府必要的宏觀調控”共同構成了中國經濟的增長和波動\[9\]。就經濟波動而言,有兩個標志性事件:一是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二是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所導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1992年以前,經濟增長波動劇烈,這同當時計劃指導下的商品經濟體制密切關聯;1993—2007年,中國經濟進入“U型時代”,以1999年為界,經濟增長經歷了不可思議的過山車,市場經濟逐步規范;2008—2012年,在全球經濟危機的沖擊下,經濟增長下調,盡管當時中央政府進行了強力刺激,中國經濟進行結構性調整的時代仍然如期而至。
圖1 中國經濟增長(1978—2012年)
市場經濟是中國經濟奇跡的根源,然而中國的市場卻是在政府管制下所興起的。“雙軌制”是中國市場經濟興起的主導性邏輯,中國的市場既不是完全給定的、更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多重選擇后的結果,這是“讓一部人先富起來”的現實路徑選擇。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是從塑造微觀利益主體開始的,而這些微觀利益主體既包括農村土地改革后所形成的農村商品市場、流動性務工群體和鄉鎮企業等,也包括依靠行政指令和審批特權所興起的各類交易中介和皮包公司,當然更包括財政包干制度下經營性的地方政府、事業單位和軍隊。1978—1992年各類微觀利益主體間的租金爭奪,催生了基本的市場交易和運行機制。然而在這激烈的商品經濟生態中,經濟運行如同“野馬”一般難以駕馭,抽象的政治口號和粗略的政府文件構成了市場運行的支撐,完備的法治和健全的監管是普遍缺失的。在商品經濟的刺激下,社會充滿了活力,但這一切都缺乏有效的規范,因而伴隨著經濟繁榮而來的是各類風波和經濟波動。
當中國的市場化道路面臨巨大的政治壓力而瀕臨險境時,鄧小平南巡無疑挽救了這一切。在“總設計師”的堅持下,政府有效規制的市場經濟成為政治共識。1993—2007年,中國經濟在過山車中逐步形成了穩定的經濟發展方式,這包括吸引外資、政府投資刺激、地區競爭、工業化與城市化“雙輪驅動”等。這一時期,經濟發展成為政府官員更迭的重要考量指標,GDP增長既是政治家實現政治晉升的工具、也是目的;對于地方政府而言,GDP是晉升的手段,而對于中央政府而言,人事任免反而成為經濟增長的手段。以東南亞經濟危機為契機,中央政府迫使地方過熱的經濟實現“軟著陸”,而隨后則又鼓勵了地方經濟發展的熱情。這既是中央政府鞏固執政根基,強化公信力的要求,更是地方政府在分稅制下打破財政困境的現實需要。在這15年中,中國的市場經濟規范逐步確立和完善,政府的有效規制已經具備了駕馭經濟的能力。
然而過快的經濟增長也引發了強烈的不安,這種不安主要倒不是來自對通貨膨脹的憂慮,而是來自對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擔憂。產能過剩使中國經濟備受困擾,尤其以鋼鐵、水泥和玻璃等高耗能、高污染的建材產品等表現最為突出。充滿諷刺的是,恰恰是締造中國經濟奇跡的秘訣,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等問題\[10\]。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強調產業轉型和企業改造以淘汰落后產能,但在地方政府自利和企業游說下,成效并不顯著。為化解產能過剩所帶來的經濟負擔,房地產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這兩類投資行為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伴隨著土地開發的繁榮,落后產能非但沒有得到有效淘汰,相反地,產能過剩進一步加劇。受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影響,中國貿易遭受沉重打擊,而在短期內消費無法獲得顯著提升的情況下,中央政府再次動用強力投資刺激經濟增長,以確保任期內經濟仍維持繁榮。中國經濟增長中的結構性問題不是4萬億元中央政府投資所能有效解決的,兩年后,經濟增長下行趨勢明顯。2008—2012年是中國經濟增長進程中深層次矛盾的凸顯時期,盡管中央政府的強刺激可以使中國經濟順利擺脫全球經濟危機的外部沖擊,但無法有效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缺陷。中國經濟奇跡能否得以延續,取決于中國經濟增長中的深層次矛盾能否得到妥善解決。而這恰恰是經濟新常態的應有之義。
三、經濟新常態的戰略選擇:政治變革與經濟轉軌
中國政府不僅主導了市場經濟進程,更深刻影響了經濟發展模式和方式。新制度主義認為,國家既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造成經濟衰退的根源\[11\]。這尤其適用于中國,根本意義而言,經濟現象是政治互動的結果。中國作為一個轉型國家,政治團結和社會穩定被界定為經濟繁榮的前提,這既源自高層政治家們對“蘇東事件”的震驚,更來自中國歷史和1949年后國家建設道路上的經驗積累和教訓總結。對于轉軌國家而言,經濟繁榮必然帶來腐敗和機會主義;而對于中國而言,龐大的官僚群體首先成為積極的尋租者。截止2013年底,全國公務員總數為1 567萬人,
可參照《中國統計年鑒(2014)》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條目的統計數據。散布在333個地市、2 853個縣區、40 497個鄉鎮;依照當年的全國總人口,官民比高達1∶83。然而公務員僅是財政供養
人口 財政供養人口狹義上主要由三部分組成:1黨政群團干部。供職于黨委、人大、政府、政法機關、政協、民主黨派及群眾團體等公共機構。2事業單位人員。供職于教育、科研和衛生等諸多領域。3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的離退休人員。當然廣義上,還包括軍隊,但一般統計上并不將軍隊涵括其內。參見程文浩,盧大鵬中國財政供養的規模及影響變量——基于十年機構改革的經驗[J]中國社會科學,2010,(2):84-102中的一小部分,據統計,僅到2012年,中國財政供養人口已超過6 000萬,按當年全國總人口計算,中國財政供養比約為1∶235,即大約235個納稅人供養1人\[12\]。官僚自利是官僚制無法克服的局限,特別是在中國經濟騰飛缺乏完善的法治規范和監管約束時,龐大的官僚群體不自覺地成為“謀利型政權經營者”、有些甚至淪為“掠奪者”。由此也造成中國政治生態惡化,四風盛行: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充斥于各機關團體單位之中。新一屆政府上臺伊始,便“約法三章”:政府性樓堂館所一律不得新建,財政供養人員只減不增,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只減不增\[13\]。此后,中央政府嚴抓作風建設,習總書記倡導以“新四風”取代“舊四風”,并掀起了“打老虎”的鐵腕反腐運動。
政治變革是催生經濟轉軌的根本原因。新一屆政府在換屆之際即表示要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深化改革,特別是推進政府機構改革和轉變政府職能。政治變革的核心是改良官僚作風、凈化政治生態、規范權力邊界及行使邏輯。然而,長久以來政府習慣于以非規范性方式刺激經濟發展,借以謀求私利,這尤其以政府性投資和政商關系最具代表性。政府性投資雖然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占比并不大,基本在7%以下,但卻構成了社會性投資的“風向標”:政府性投資銳減,社會性投資相應地會大幅衰退;而政府性投資增加,社會性投資則會激增。對于投資驅動型的經濟增長而言,政府性投資著實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然而中央政府嚴抓作風建設,特別是清查黨政機關的樓堂館所建設違規違法行為,有效抑制了政府性投資的擴張,相應地也帶來社會性投資的銳減。政商關系則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發揮了更微觀的作用:廣義上的政商關系涵括了企業家的政治參與,諸如兼任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或其他行政性職務等;而狹義的政商關系則具體指企業家與政府官員之間權力與金錢互惠性的合作圈子。某種意義上講,政商關系構成了中國市場經濟運行的微觀機制。通過政商關系,企業家可以及時獲得充足的融資和開發項目,政治家則既可以獲得私人收入、又可以獲得形象工程及政治聲譽。然而伴隨著中央政府的強力反腐,諸如“西山會”、“石油幫”等政商圈子被陸續鏟除,而其他的類似小團體也變得異常謹慎,這也有效降低了政商關系在項目開發上的活躍度。新一屆政府的政治變革成效顯著,對經濟增長也產生了顯著性影響。據統計,2013年GDP增長率為77%,2014年GDP增長率進一步下調為74%。經濟增長的放緩是新一屆政府政治變革的結果。
腐敗與經濟發展對于轉型國家而言是一個極大挑戰,這不僅源自腐敗與經濟發展的復雜關系,更來自經濟轉型對政治發展的巨大沖擊。Nathaniel\[14\]認為腐敗是僵化經濟體制的潤滑劑。Huntington\[15\]指出,一個僵化而清廉的政府比一個僵化的、高度集權的腐敗政府更難以推動經濟增長;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過度管制扭曲了經濟發展和資源配置,而腐敗則客觀上可視為對資源扭曲配置的一種糾正。拉美和蘇東等轉型國家的發展經驗均證實了這一點,而這也加深了研究者的困惑。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對腐敗與經濟發展關系的認識也更加清晰。腐敗通常與經濟衰退或低速增長相伴而生,然而在東亞地區,腐敗卻與經濟高速增長同步。就東亞奇跡而言,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中國香港、新加坡和中國臺灣)在經濟騰飛時期也面臨嚴峻的腐敗問題,金權政治、黑金政治、財閥壟斷和黨國資本等盛行。然而腐敗終究不是經濟增長的根源,相反腐敗對制度和公信力的侵蝕,瓦解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根基。因而一旦遭遇東南亞經濟危機的沖擊,這些國家或地區便陷入嚴重的經濟衰退。經濟轉型的根本意義在于,伴隨著新生的經濟結構成長,穩定而有效的運行制度成為經濟長期增長的根源,一旦政治轉型不能提供有效的市場經濟運行框架,不僅經濟增長會遭遇挫折,社會沖突和政治混亂也將不可避免。盡管在經濟騰飛的初期,腐敗作為一種不規范的協調機制可能扮演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這種破壞性力量終不能成為維持經濟增長的長久之計。東亞奇跡的衰落是政治轉型不能適應經濟轉型的結果。當然在這些國家經濟陷入衰退時,政治改革的進程大幅加快,政治發展取得了積極成效,腐敗也得到了有效治理。
當前中國面臨著同樣的轉型困境。中國奇跡是東亞奇跡的延續,中國經濟奇跡受益于東亞奇跡,并以中國特色創造著新的輝煌。東亞經濟騰飛進程中伴隨著顯著的國際分工和地區產業轉移:中國改革開放之際恰逢亞洲“四小龍”承接美國和日本產業轉移后的經濟繁榮期;東南亞經濟危機可視為亞洲“四小龍”經濟繁榮期的終結,但這并未對中國經濟構成根本性破壞;此后,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陸續成為東亞產業轉移的“新寵”,隨著中國日漸融入全球市場,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后,中國更是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保護傘”。就東亞奇跡五國而言,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均沒有超過30年,7%以上的高速增長基本維持在20年左右。然而中國經濟奇跡已保持了35年以上的高速增長,這固然受益于中國龐大的市場,豐富的勞動力、土地和資源等要素供給,但也意味著政府刻意放緩了體制轉型的時刻表。對于中國政府而言,體制轉型的必要性是一個政治共識,但轉型的道路選擇卻是充滿了爭議。自2004年以來,服務型政府轉型逐漸成為政治變革的討論熱點,服務型政府旨在重塑政府形象和結構,擺脫管控型政府和發展型政府的消極框架。然而在政治實踐中,由于高層對政治變革的推動力不夠,再加之地方政府的官僚自利,致使服務型政府逐漸異化為公共服務型政府,政府變革隨后也不了了之\[16\]。既然經濟發展要求政治變革做出充分的反應,與其消極等待,不如有效把握改革的主動權。新一屆政府以政府作風建設和強力反腐作為切入點推進政治變革,順應了中國社會轉型的要求:在政治變革的壓力下,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而伴隨著經濟結構性調整,政治新常態也逐漸催生;經濟新常態與政治新常態相互影響,共同推進中國社會轉型。
四、與經濟新常態相伴而生的政治新常態
那么與經濟新常態相伴而生的政治新常態的內涵又是什么呢?就目前的政治經濟結構調整情況看,起碼包括兩點:第一,強化市場作用,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第二,強化法治規范,推進法治國家建設。市場和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兩大基石,根本上均是對政府行為和邏輯的約束和調整。市場經濟是現代經濟繁榮的基本經濟發展路徑,與市場經濟相對的是計劃經濟。雖然關于市場和計劃的適用范圍和效度上存在爭議,但市場經濟優于計劃經濟對于現代社會而言幾乎成為經濟學常識。Coase\[17\]的工作顯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計劃對于公司內部管理是高效的,但對于國家經濟運行卻是破壞性的。而市場機制,則恰恰有助于國民經濟運行中的資源高效配置,并促進經濟繁榮和國民財富的增長。東亞奇跡和中國奇跡昭示了市場經濟的成功,根本意義而言,經濟奇跡的興起源自市場經濟體制的生成。然而就中國而言,政府管制是客觀事實,甚至于市場的生成本身就是政府主動放松管制的結果。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政府審批和大量指令性計劃仍廣泛存在,市場仍然在政府的管控下發揮作用,而政府的管控本身就大量存在諸如尋租、腐敗等破壞市場機制的力量。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相應地要求政府進一步放松管制和指令,更好地發揮維護和服務市場經濟的作用。
對政府行為的調整,更要求對政府行為邏輯的規范,這就關涉法治的根本意義。法治根本上涉及對政府行為邏輯的規范,即政府權力的行使不能為所欲為,而應服從約束和規范。特別是,政府不能作惡而免責、掠奪而不受懲罰。讓法治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保駕護航”,讓人頗感復雜。因為,在中國市場經濟成長進程中,中國的法治是殘缺不全、甚至相互沖突的;中國的法治體系是逐漸形成的,而不是給定或締造的。當然更重要的是,中國奇跡的約束依靠政治規誡和政治激勵,并非法治。法治的缺失和缺位是造成政府行為異化和墮化的直接原因。當然法治在國家治理機制中的地位偏低及力量偏弱也并非改革開放以后的事情,在建國后前三十年以及建國以前,法治長期被政治所控制和壓制也是客觀事實。當前中國經濟結構性調整離不開法治體系的建設。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依法治國、完善法治體系建設、建設法治國家,順應了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潮流,構成了中國新常態的應有之義。
除此之外,政治新常態還應強調服務型政府轉型以及專家治國體制。服務型政府緣起于20世紀90年代末期的政府機構改革,張康之\[18\]明確提出以服務型政府取代統治型政府和管理型政府,實現政府職能從管控向服務的轉變。隨后學界對服務型政府展開了深入的討論,盡管服務型政府內涵豐富,但它基本涵括了“以人為本的治理理念、依法行政的行為準則、公眾需求導向的服務模式和回應民意的政府責任”\[19\]。學界的討論引起了政界的回應,2004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專題研究班結業式上正式提出了“建設服務型政府”,隨后溫家寶在參加全國人大陜西代表團討論時又予以重申,更是形成了共識。2005年全國人大十屆三次會議上,建設服務型政府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經人大批準而變成國家意志;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更是明確提出“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從而把中國服務型政府的建設提高到體制改革目標的價值層面。在當時,建設服務型政府已成為當代政府改革和政府建設的目標選擇,盡管存在一定的限制性條件,但建設好服務型政府只是時間問題,而不是能不能問題\[20\]。服務型政府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創新,也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它反對官僚本位,強調突出“公民本位”和“社會本位”,這是對政府行為和邏輯的根本性規范。對于政治新常態而言,服務型政府不是一個過時的概念,作為政治變革的路徑選擇,應該得以深入推進和實踐。
專家治國體制的意義在于實現政治家和技術官僚分離,而技術官僚免于政治紛爭、不背政治包袱。中國是世界上具有最古老和最復雜的官僚政治傳統的國家,其高度復雜的、縱橫交錯的制衡體系,維持了長達千年的政治穩定。然而中國官僚體制最大的問題在于政治家與技術官僚不分,即所謂官、吏、僚不分。對于中國當前的干部管理體制而言,專家學者可以成為行政首長,而行政首長也可以被任命為黨委書記,沒有黨委的意見則無法實現干部流動,因而干部時刻處于政治紛爭當中。即便是窗口辦事員、審計師、法官和檢察官等也要具備政治敏感,謹慎處理與黨委委員的關系,在服從現任書記和直系領導的同時,還要善于搞好與接任書記和領導的關系。對于專業性較強的干部而言,一旦時間和精力被政治紛爭所牽涉,必然無法在業務上獲得較大突破,而往往淪為平庸的“吏員”。東亞經濟的巨大成功離不開精于治理的官員,而專家治國論也因此盛行。雖然這些技術官僚在威權政體中的地位低于黨工干部和軍人,但當政權穩定后,政府的專業化工作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緊迫壓力需要技術專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這些技術官僚免于政治紛爭、不背政治包袱,專心于業務領域,特別是在財經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以中國臺灣為例,在中國臺灣財經決策核心最有影響力的數十位技術官僚中,諸如尹仲容、嚴家淦、李國鼎等均對中國臺灣經濟發展發揮過重要作用。最為寶貴的是,政治家和技術官僚有明確的職能分工,政治家為技術官僚提供政治保護,技術官僚“治而不統”,政治家“統而不治”,二者默契合作。特別是二者在政治與行政沖突中所表現出的人格、操守、能力和品性上的體量與包容,構成了東亞奇跡的治理前提,這也是東亞奇跡中技術官僚與威權體制共生的基本前提。
五、總結與討論
中國經濟奇跡還能持續多久?經濟新常態能否支撐新一輪為期三十年的GDP中高速增長呢?雖然東亞奇跡給中國奇跡帶來許多有益的啟發,但中國仍有諸多可以創造的空間。中國模式與東亞模式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相似度也極高。中國模式的內涵可能更豐富、也更復雜。同其他東亞國家所面臨的良好歷史契機相比,中國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面臨著糟糕的內外環境;在惡劣的環境下,中國要贏得更多的國際競爭力及發展機會,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學習成本”:一方面是被嚴重低估的勞動、土地、資源環境、人權和公民權等;一方面是體制性變革的壓力,黨—政關系、央—地關系、政—商關系、官—民關系和城—鄉關系等;一方面是改革進程中的挑戰,如地方保護主義、周期性的經濟波動、過激的民主化訴求、群體性抗爭以及外部沖擊等。在重重困厄之中,政治集權和經濟相對分權的體制結構成為務實的改革選擇: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沖擊必須處于有效的政治控制之下,任何試圖脫離政治控制的活動都將受到更嚴格的管控。政府在中國市場化進程中的強勢地位,同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初始條件是密不可分的,而市場化進程中所出現的沖擊和風波更促使政治高層相信這種強勢干預是必要的。
政府主導市場的改革策略是務實的,但其所滋生的機會主義正在逐步瓦解這種策略背后的合法性。在改革開放初期,盡管經濟增長伴隨著劇烈的波動和混亂,但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們所建立的政權仍然享有絕對的權威,政府的公信力極少遭到質疑,即便是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和文化大革命,人民群眾也并未否定社會主義政權。究其根源,民眾傾向于相信,政府的確會犯錯,但這種錯誤并非是源自領導人的私心私欲,而且這種錯誤隨后會得以有效更正。但伴隨著中國市場化進程的加快,民眾對權力所滋生的腐敗以及政府官僚自利的作風日益不滿,特別是一旦以民眾的切身利益作為經濟發展的代價并且民眾眼見其私人收益被瓜分時,民眾的反抗及群體性抗爭便難以遏制。社會抗爭事件中往往充斥著戲劇性的悖論:恰恰是為了改善當地民眾生活和收入水平的政府行為,招致了民眾的不滿和反抗。究其根源在于政府行為過程中的尋租和設租引起了民眾的強烈不滿,政府的公信力因此衰落。政府主導市場的改革策略最初的政治設想是由政府扮演市場的監管者,但在實踐過程中,政府卻逐漸異化為管控者,市場微觀活動的興起要依靠機會主義的潤滑,機會主義由此大行其道。這不僅破壞了市場機制,更侵蝕了政府公信力,政府也被認為具有更強的掠奪性。
經濟新常態是中國奇跡延續的關鍵,而政治新常態則決定了經濟新常態。深化改革,釋放更多的制度紅利,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過去35年的經濟轉型也為政治變革提供了充足的經驗積累:一個監管而非管控市場的政府、一個崇尚法治的服務型政府、一個官員精于治理而不背政治包袱的政府,主導著規范而非扭曲的市場經濟,構成了中國新常態的重要內涵。2015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期間,提出了“四個全面”,即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這被看做是新時期治國理政的總方略,這也是新常態下中國政治經濟發展和變革的重要路徑選擇。當前,距離鄧小平所設想的第二個“一百年”還有三十多年,經濟新常態關乎國家現代化和民族復興。中國經濟奇跡并未終結,仍將延續,有效的政治變革和經濟結構性調整將掀起新一輪的經濟增長,這是經濟新常態的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1] 林毅夫 林毅夫解讀新常態:經濟增長率會往下調\[N\] 經濟觀察報,2014-10-11
\[2\] 李揚 中國經濟新常態不同于全球經濟新常態\[N\] 人民日報,2015-03-12
[3] 黃益平老經濟、新經濟與增速換檔[R]2015北京大學成都金融論壇,2015
[4] 姚洋2015年中國GDP增速或降至7% 改革紅利繼續釋放[R]中國經濟:2015預測,2015
\[5\] 姚金偉,孟慶國,黃天航 政治商業周期中的制度激勵、外部沖擊與官員晉升邏輯:基于1978—2012年中國分省面板數據的經驗分析\[J\] 公共管理評論,2014,(2):15-31
\[6\] 李迅雷2015年中國經濟:游走在通縮與擠泡沫的窄道之間\[N\]南方周末,2015-01-16
\[7\] Zhao, DX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Performance Legitimation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a\[J\]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9, 53(3):416-433
\[8\] 顧錢江,張正富,王秀瓊習近平首次系統闡述“新常態”\[DB/OL\]新華網2014-11-09,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09/c_1113175964htm
\[9\] Li,TN Chinas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R\] Working Paper,2011
\[10\] 周黎安 晉升博弈中政府官員的激勵與合作——兼論我國地方保護主義和重復建設問題長期存在的原因\[J\] 經濟研究,2004,(6):33-40
\[11\] 道格拉斯·C諾斯 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陳郁,羅華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0
\[12\] 熊劍鋒中國財政供養規模調查\[J\]鳳凰周刊,2013,(10)
\[13\] 中國新聞網李克強矢言反腐,代表新一屆政府約法三章\[DB/OL\]http://wwwchinanewscom/shipin/cnstv/2013/03-17/news186789shtml
\[14\] Nathaniel,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Bureaucratic Corruption\[J\]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64,8(2): 8-14
\[15\] Huntington, SP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16\] 姚金偉,孟慶國 政府轉型與現代治理體系構建:歷史邏輯與實踐反思\[J\] 青海社會科學,2014,(6):28-31
\[17\] Coase,RH 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a, 1937, 4(16): 386-405
\[18\] 張康之 把握服務型政府研究的理論方向\[J\] 人民論壇,2006,(3):12
\[19\] 姜曉萍 構建服務型政府進程中的公民參與\[J\] 社會科學研究,2007,(4):1-7
\[20\] 吳玉宗 服務型政府:緣起和前景\[J\] 社會科學研究,2004,(3):10-13
(責任編輯:劉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