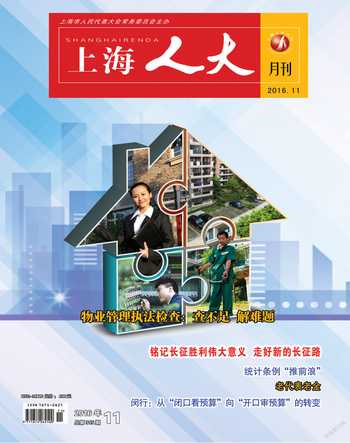淺析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特定問題調查”
武春 武香君
多年來,就全國范圍來說,“特定問題調查”活動開展得特別少,且一直處于探索階段。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完善人大工作機制,通過詢問、質詢、特定問題調查、備案審查等積極回應社會關切。筆者認為,激活“特定問題調查”勢在必行。本文主要指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此項職權存在問題,并提出解決設想和建議。
一、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特定問題調查”法律規定的回顧
1954年憲法賦予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特定問題調查權,并沒有賦予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此項權力。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有特定問題調查權,始于1986年修正地方組織法時增加的規定。當時的地方組織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組織對于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1995年修正地方組織法時將第二十六條改為現行地方組織法第三十一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代會可以組織關于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主席團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書面聯名,可以向本級人大提議組織關于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由主席團提請全體會議決定。調查委員會由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和委員組成,由主席團在代表中提名,提請全體會議通過。調查委員會應當向本級人大提出調查報告。人代會根據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可以作出相應的決議。人代會可以授權它的常委會聽取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人大常委會可以作出相應的決議,報人代會下次會議備案。同時增加第五十二條規定,對人大常委會可以組織關于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作了和人代會類似的規定。
1992年的代表法第十六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各級人大代表有權依法提議組織關于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第二十六條(現行代表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各級人大代表根據本級人大或其常委會的決定,參加關于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
2006年出臺的監督法第七章明確了特定問題調查制度,在地方組織法規定的基礎上,對各級人大常委會的“特定問題調查”進行了細化。第三十九條規定,各級人大常委會對屬于其職權范圍內的事項,需要作出決議、決定,但有關重大事實不清的,可以組織關于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第四十一條規定,調查委員會可以聘請有關專家參加調查工作。與調查的問題有利害關系的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和其他人員不得參加調查委員會。第四十二條規定,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時,有關的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公民都有義務向其提供必要的材料。提供材料的公民要求對材料來源保密的,調查委員會應當予以保密。調查委員會在調查過程中,可以不公布調查的情況和材料。
關于特定問題的調查,地方組織法、監督法、預算法還有三個單獨的個案規定。一是1955年修正地方組織法時增加的第二十六條第五款規定:向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代會提出的罷免案可組織調查委員會。二是監督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行使撤職權可組織調查委員會。三是現行預算法第八十四條(1994年通過的預算法第六十七條)規定:各級人代會和縣級以上人大常委會有權就預算、決算中的特定問題組織調查。
二、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特定問題調查”的特性
關于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特定問題調查”,只有地方組織法、監督法、代表法、預算法這四部法律作了規定,筆者還沒發現其它的法律涉及“特定問題調查”。代表法對“特定問題調查”的規定實際上包含在地方組織法的規定中。筆者認為,地方組織法的規定過于原則,如在什么情況、什么條件下可以啟動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沒有具體要求;監督法的規定相對細化,但也比較原則。從地方組織法和監督法的規定可以看出,“特定問題調查”具有以下特性:
1、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具有臨時性。它不是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常設機構,只是對某一特定事件而需要依法設立的組織,任務完成后將解散。
2、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的提議主體法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主席團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書面聯名,可以向本級人代會提議組織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主任會議或五分之一以上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書面聯名,可以向本級人大常委會提議組織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對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的提議主體的要求比一般議案的提出主體要求高。
3、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的設立主體法定。有權決定設立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的主體只能是人大或其常委會。
4、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的組成人員法定。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組成人員必須是本級人大代表或常委會組成人員。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可以聘請有關專家參加調查工作,但他們不是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組成人員。
5、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如何處理法定。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的任務就是對特定問題進行調查,提出調查報告。由人代會決定設立的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向人代會負責并報告調查結果,由人大常委會決定設立的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向人大常委會負責并報告調查結果。人代會可以授權它的常務委員會聽取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人大或其常委會根據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可以作出相應的決議決定。
三、“特定問題調查”在實施過程中容易引起困惑的幾個問題
1、特定問題界定難,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
地方組織法對在什么情況下可以組織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沒有任何限制條件,可能正因為如此反而導致人大及其常委會忽視了設立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監督法雖然規定人大常委會“對屬于其職權范圍內需要作出決議決定但重大事實不清的事項可以組織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但“有關重大事實不清”在實際操作中也難以把握。再者,“可以組織”畢竟不是“必須組織”,也就是說,也可以不組織。一些地方對“有關重大事實不清”的問題,由人大有關專門委員會或者人大常委會有關工作機構去調查,盡管調查的質量和水平可能不高;一些地方考慮到開展特定問題調查可能會引起一些麻煩,因而不愿意組織。特定問題界定難,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
2、調查時限沒有規定,兼顧質量和時效難度大
由于法律對特定問題調查的時限沒有規定,如果人大及其常委會注重時效性,限定調查委員會在較短的時間完成調查任務,往往可能無法保證調查質量;如果不注重時效,不限定時間,使得調查時間過長,往往又會影響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兼顧調查質量和時效難度大。
3、調查對象如果不配合,缺少法定的制約手段
根據監督法規定,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時,有關的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公民都有義務向其提供必要的材料。但如果調查對象不履行義務,不提供材料,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處理,法律沒有賦予調查委員會必要的制約手段。
四、完善特定問題調查制度的設想及建議
1、要對在什么情況下組織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盡可能作出更加具體的規定
建議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修改完善相關法律,對需要組織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的情況盡可能細化。在現行法律規定的框架下,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應根據本地實際情況,自行制定關于組織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的規定,盡可能或最大限度地具體規定在什么情況下組織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但筆者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由本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或指望上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出一個包攬無余、一勞永逸的規定或辦法,將必須設立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的所有情況都包含在內是不現實的,也是做不到的。筆者認為,需要組織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的問題,應是人大有關專門委員會或者人大常委會有關工作機構承擔不了的問題。如果是人大有關專門委員會或者人大常委會有關工作機構能解決的問題,未必就要啟動“特定問題調查”。
2、有些“特定問題調查”應不限于監督法有關規定
監督法只是規范人大常委會行使監督權的法律,由于人大及其常委會還要行使立法權、重大事項決定權、人事任免權等,行使這些職權當然也可以組織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筆者認為,監督法關于“屬于其職權范圍內需要作出決議決定但重大事實不清的事項可以組織關于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的規定,雖然比較具體,但縮小了地方組織法規定的范圍。有些事項需要設立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但并不在監督法規定的范圍內。如人大常委會在立法過程中,認為有必要,也應設立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因而有些“特定問題調查”可不限于監督法的規定來實施。再者,監督法只是規范人大常委會實施監督權的法律,不是規范人代會實施監督權的法律,因而,人代會為了行使監督權或其它職權需要進行的“特定問題調查”,也未必按監督法的規定落實,但必須遵循地方組織法的規定要求。
3、要明確“特定問題”的調查時限并注重質量
公眾對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的評價,依據往往是調查結果的質量和調查的時效。人大及其常委會每次在組織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的同時,應根據具體情況,對調查時限作出科學合理的規定,既要保證調查的質量,又要注重調查的時效。對此,在省級人大常委會范圍內率先組織開展特定問題調查的江西省人大常委會給我們做了示范。2016年6月8日《江西省人大常委會關于成立食品生產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攤販問題調查委員會的決定》指出:“調查委員會于9月下旬向省人大常委會報告調查情況”。可以看出,在設立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的同時就對調查時限作了具體規定。
4、法律應賦予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相應權力
建議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修改有關法律時,要賦予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一些直接或間接的權力,解決調查對象不履行義務,不提供材料等問題。 (作者單位:武春,安徽省鳳陽縣人大常委會;武香君,安徽省鳳陽縣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