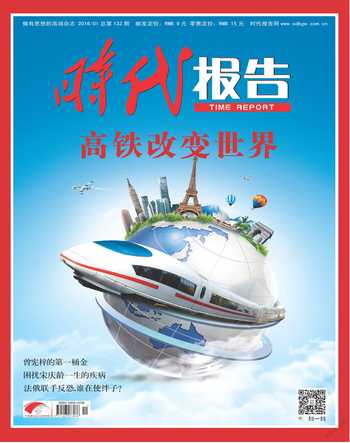一封發錯單位的電報
范慶鋒
雜志社的一位同志找到我,遞給我了一封電報,電報是共青團中央宣傳部發來的。電文說,請通知XXX同志于X月X日到北京某賓館報到,參加首屆全國青年報刊十佳記者頒獎大會。
看看單位,是雜志社,不是報社,看看被通知人的名字,分明和我的姓名一字不差,我有點蒙,到底是讓我去參加會議,還是讓雜志社的某位同志去參加會議?我拿不準。
在此之前,團中央宣傳部和中國青年報刊協會聯合發文要在全國評選十佳青年記者。盡管報社有外界的壓力,但還是把我的情況整理成一份材料報了上去。在我看來,能讓我申報這個榮譽已經很不錯,而且也十分滿意了。同時,能把我的申報材料的內容在自己的媒體上刊出,已經到了我想要的最高的程度。沒有想到我還能入選十佳記者。
這應該是一個意外。
我拿著電報去找總編輯,總編輯看了電報內容后也有點拿不準,對我說:先別對外說,我打電話問問武老師。
總編輯說的武老師叫武志蓮,當時是全國青年報刊協會的副秘書長。總編輯撥通了電話,只聽那頭武老師說,就是他,可能發電報時把單位弄錯了。即令是總編輯電話做了證實,但我還是不敢信以為真。
我忐忑不安地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車。一到達報到地點,只見青年報刊協會的李艷蘭老師正準備出門,因為和她認識,就向前跟她打招呼,問她出去干嘛,她說,我去給你們買明天戴的大紅花。
頒獎會是在記協禮堂舉行的,可能是為了體現對這次評選的重視,頒獎地點選在了中國記協。
參加頒獎會的領導有當時的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徐惟誠、中國記協書記處書記唐非、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袁純清等。
在到達頒獎會現場時,還發生了一件事,讓我至今記憶猶新。
一進入會議室,還沒有落座,一個年輕的工作人員向我走來,對我說:“咱倆是老鄉。”我先是一驚,我跟對方不熟,怎么就成了老鄉?
這時,站在一邊的同志對我說,這是團中央的同志。走過來的年輕人說,我是吉書記的秘書,你不認識我,我認識你。因為你的評審材料我看了很多遍。
和我打招呼的團中央的同志說的吉書記是吉炳軒。當時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他曾在團河南省委任書記,后到地方擔任市委書記,再后來擔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黑龍江省委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時,吉炳軒才到團中央工作半年不到。我連忙問吉書記的近況。那位自稱是吉炳軒書記的秘書說,吉書記去西藏調研,患了高原反應癥,現在正在住院。出于禮貌,我問吉書記在哪家醫院,能不能去看看。秘書說,吉書記有交代,任何人都不讓去看。
首屆全國青年報刊十佳記者當年表彰名單的排序是,《中國青年報》的馬年華、上海《青年報》的王建敏、貴州《青年時代》雜志的盧程、《中國青年報》劉健、《北京青年報》張延平、廣東《少男少女》雜志李國偉,還有我和《中國青年》雜志鄭勇、寧夏《青年生活導報》趙彬和廣東《黃金時代》雜志的溫眉眉。
當時新華社發的通稿說,青年報刊十佳記者是從上百名候選人中產生出來的,“代表了全國愈百家青年報刊的1000多名記者的精神風貌。 他們最大的特點是作風踏實,深入實際,吃苦耐勞,有較高的思想政治素質,有高度的事業心、責任感和良好的職業道德,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某些誘惑面前潔身自好,忠誠于青年報刊高尚的事業”。
按照武志蓮老師的點評,獲得表彰的十個人,各有特色。這里暫時按下不說。
表彰時,把我和劉健、張延平等安排到了第一排的正中間。劉健是當時的中國青年報山東記者站站長,后來調回總社,擔任新聞中心主任,再后來,聽說當了中國青年報的副總編輯。
劉健是從山東《大眾晚報》調入中國青年報山東記者站的。聽說,劉健當時堅持沂蒙山區人身上發生的新聞和北京人身上發生的新聞都同等重要。他堅持這個觀點,曾經和中國青年報社的不少人在內部通訊上進行過論戰,而且長達半年之久。
此后,我到北京工作了一段時間,一個大雪彌漫的中午,我去中國青年報探望前中國青年報總編輯佘世光、王石和青年報刊協會的副秘書長尤畏和武志蓮老師時,還在中國青年報餐廳碰到了劉健。當時,劉健正同聲名鵲起、寫出了《大國寡民》的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躍剛在一邊吃飯,一邊大聲談論問題。
當年參加頒獎的劉健,不知道是聽說還是看到主席臺上座簽排的位置上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徐惟誠正對著他,他把我拉到了他所在的位置上,對我說,咱倆換一下位置,我不想讓徐惟誠給我頒獎。我問他為什么,他說,前不久他才批評了我。對此,我感同身受。于是,我倆調換了一下位置。
有些事情就是那么邪門兒,當主席臺上的領導就坐后,徐惟誠部長的座簽不知怎么就和當時的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后來擔任過山西省委書記的袁純清的位置調換了。結果,給我頒獎的是袁純清,而給劉健頒獎的則是徐惟誠。
在這次表彰會上,徐惟誠代表中宣部發表了講話,他希望“十佳”記者永遠保持謙虛謹慎的優良作風,自覺抵制“有償新聞”的不正之風,一輩子做人民的杰出的新聞工作者。
不料想,那個時候對我來說是新名詞的“有償新聞”,在20年后,讓我曾經服務過的媒體負責人因此而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直至最后被革職。(本文選自作者《白紙黑字——一個新聞記者和眾多高官的恩恩怨怨》一書第十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