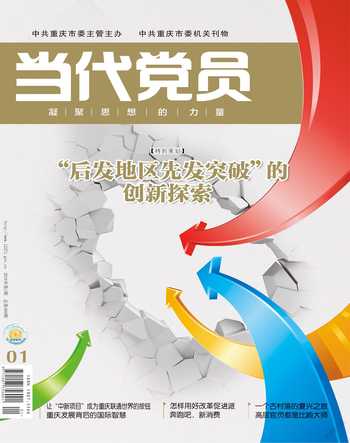重慶蝶變的“重組”動力
王婷
在2015年6月的一次研討會上,重慶市長黃奇帆拋出了一串發(fā)人深省的數(shù)據(jù)——
一臺電腦,如果產值是500美元,其零部件、原材料一般占整個產值的50%,就是250美元;它的零部件、原材料從全世界運到中國沿海,又運出去,整個的物流運輸、倉儲、銷售環(huán)節(jié)占100美元;然后,品牌商的研發(fā)以及售后服務,一般占75美元;所以,500美元中在中國沿海只留下75美元的總裝,占產值的15%左右。
“而在重慶,我們留下了70%的產值。”黃奇帆說。
從15%到70%,重慶是如何做到的?

產業(yè)重組——創(chuàng)新發(fā)展加工貿易模式,構建產業(yè)大集群。
水平分工
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
全球經(jīng)濟低迷期,重慶卻發(fā)現(xiàn)了危中之機——全球電子產品一片凄涼,唯獨筆記本電腦銷量不降反升。
其時,重慶汽摩產業(yè)一業(yè)獨大,占工業(yè)總產值比重近40%。
城市產業(yè)結構單一,意味著城市承擔的風險極大。
汽車城底特律就是例子——其80%以上的財政收入都來源于汽車行業(yè),最終也因汽車產業(yè)不景氣而破產。
產業(yè)結構調整迫在眉睫。
于是,重慶定下目標:把IT業(yè)打造成重慶的第一支柱產業(yè)。
當時,筆記本電腦加工貿易幾乎全部集中在沿海地區(qū),隨著沿海地區(qū)煤、電、土地等成本的提高,社會各界紛紛呼吁將加工貿易轉移到內陸。
但是,沿海地區(qū)20多年來都是采取原料和銷售在國外,加工在國內的兩頭在外水平分工加工貿易模式。
這種加工貿易模式有兩個薄弱點。
第一,產業(yè)鏈短。
一臺電腦從生產到銷售全過程,最終留給加工的成本很少,產業(yè)鏈上豐厚的利潤更多地集中在“前頭”的研發(fā)和“后頭”的銷售,中國參與加工環(huán)節(jié),賺的只是“打工者”的微薄利潤。
第二,兩頭在外,大進大出。
由于筆記本電腦加工原材料、零部件在外,加工完了銷售在外,所以筆記本電腦加工貿易存在著大進大出的物流結構特點。
“產業(yè)轉移可以,這種貿易模式要不得!”黃奇帆很清醒。
況且,從沿海到重慶,還有2000多公里的“冰山”成本。
“冰山”橫亙其間,如何破題?
垂直整合
2008年5月的一天,黃奇帆率團抵達美國洛杉磯。
此行,黃奇帆一行人要拜訪惠普公司總部。
作為世界級的電腦公司,惠普此時也正在尋找一個新的生產基地,以擴大產能。
黃奇帆說明來意:希望惠普落戶重慶。
但是,惠普高層也拋出了問題:物流成本太高。
傳統(tǒng)加工貿易模式是品牌商下單,代工商組裝,全球零部件供應鏈供應。
但是,在黃奇帆看來,按此邏輯,物流成本極高,違反經(jīng)濟規(guī)律。
內陸要搞加工貿易,必須創(chuàng)新。
如果筆記本電腦的各種零部件原材料80%都能在重慶生產,那么,從零部件運到整機廠,運輸成本小,在這個意義上就能一下子跳出兩頭在外的模式,大幅降低物流成本。

黃奇帆拋出一個全新的商業(yè)模式——整機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體化,實現(xiàn)80%的零部件本地造,讓物流成本歸零。
“延伸產業(yè)鏈,把加工貿易的‘微笑曲線’大部分留在重慶。”黃奇帆說。
觀念一出,惠普立即來了興趣。
“你怎么做到80%本地化,現(xiàn)在又沒有零部件廠。”時任惠普公司總裁馬克·赫德問。
“如果你給我4000萬臺,零部件廠商就會蜂擁而來,而且我們的組織效應能夠使他們2—3年出產品。”黃奇帆說。
“如果三年內達不到零部件80%本地化怎么辦?”馬克·赫德問。
“高出的物流成本我們財稅補貼。”黃奇帆說。
如此,重慶對加工貿易價值鏈進行了垂直整合,重組其組織模式。
惠普公司應聲而來。
重組集群
有了惠普這只“母雞”,2009年2月9日,黃奇帆又直奔臺灣拜訪郭臺銘。
作為全球最大電腦零部件供應商、代工商,黃奇帆瞄準了富士康這只“小雞”。
“我不是來招商,而是給你送一單生意。”黃奇帆進門說了第一句話。
郭臺銘立即來了興趣,叫來公司所有副總,會議室瞬間擠滿了人。
原定半個小時的會晤,變成了三個小時。
雙方一拍即合。
2009年8月,重慶和惠普、富士康同時簽約。
短短幾個月時間,重慶又以驚人的速度先后和英業(yè)達、廣達簽約,在重慶設基地。
惠普這只“母雞”就這樣吸引了三只“小雞”——世界級的臺灣電腦加工廠富士康、英業(yè)達、廣達,并形成了4000萬臺筆記本電腦加工的生產線。
富士康、英業(yè)達、廣達同時也是“母雞”,吸引了一大批配套廠商。
全球最大筆記本電腦電池生產商新普來了,臺灣最大材料供應商維鯨來了……
IT零部件供應鏈日漸豐滿,大群“小雞”又將另一只“母雞”吸引了過來。
2010年12月1日,宏碁帶著4000萬臺筆記本電腦項目入駐重慶。
而宏碁作為新的“母雞”,又立即邀約仁寶等四大代工商入渝。
就這樣,新一輪“母雞效應”拉開帷幕……
于是,筆電產業(yè)在重慶實現(xiàn)重組,形成了“5+6+800”的電子產業(yè)集群,實現(xiàn)零部件、原材料80%在本地生產。
“250美元中的200美元”落地重慶。
2010年12月30日,重慶開通了離岸金融結算賬戶。
于是,銷售結算也留在了重慶。
“這樣加起來有350美元了,就占到了500美元的70%。”黃奇帆說。
舉一反三
2013年1月的一天,美國密歇根州首府蘭辛。
重慶直升機產業(yè)投資有限公司完成了對美國恩斯特龍直升機公司的收購。
這注定又將成為重慶發(fā)展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2010年,國務院發(fā)布《關于深化我國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見》。
“通用航空產業(yè)空間10萬億元都不止。”中國直升飛機發(fā)展協(xié)會會長徐昌東說。
得知消息,重慶立即行動。
2012年7月,重慶獲批成為中國第二批、西南第一個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試點城市。
于是,通航產業(yè)開始復制筆電垂直整合產業(yè)發(fā)展模式。
“在世界范圍內重組、利用航空領域的各類優(yōu)勢資源,通過并購、合作等手段,引進先進技術、優(yōu)秀人才,面向國內市場需求開發(fā)新產品。”時任重慶市副市長童小平說。
收購恩斯特龍只是重慶邁出的第一步。
隨后,重慶開始吸引零部件等配套企業(yè)。
一方面,重慶加強招商工作,吸引核心零部件企業(yè)落戶。
另一方面,加強與本地變速箱、發(fā)動機、機載電子等企業(yè)橫向聯(lián)系。
于是,皮拉圖斯、高原國際等整機項目先后落戶重慶,霍尼韋爾、曙光航空等配套商和延伸企業(yè)也紛至沓來。
短短時間,重慶聚集航空相關企業(yè)40多家。
一條集通航研發(fā)、飛機生產、運營服務等于一體的全產業(yè)鏈基本形成。
與此同時,重慶汽車產業(yè)也“重組”推動,形成了“1+10+1000”的產業(yè)集群。
如今,電子信息、汽車、裝備等“6+1”支柱產業(yè)集群發(fā)展迅猛。
優(yōu)進優(yōu)出
2013年10月,韓國大邱。
一條20多公里長的單軌線路似游龍般貫穿城區(qū)。
很少有人知道,大邱的這條單軌線“婆家”是重慶。
六年前,韓國大邱市市長到重慶考察,看到重慶輕軌轉彎半徑小、爬坡能力強,立即表現(xiàn)出濃厚的興趣。
城市風貌和重慶類似,坡地不少,同時擁有270萬人口的大邱也準備修建輕軌。
當時,重慶還有一個強勁的競爭對手:日本日立公司。
重慶第一條輕軌——較新線項目單軌客車生產技術便是從日立公司引進的。
日立既想獲得訂單,又想保住技術,便提出要求:凡聯(lián)合開發(fā)中使用的技術,20年內不能到國外使用。
意思很明顯——別想跟我搶生意。
于是,重慶消化、吸收和自主創(chuàng)新,短短幾年,效果不菲——
建成國內領先的跨座式單軌整車生產基地,具備年產500輛整車的生產能力。
形成整車零部件生產基地。
單軌列車整車和主要系統(tǒng)及總成部件成功實現(xiàn)自主開發(fā),車輛國產化率達95%。
…………
此時,重慶跨座式單軌產業(yè)已形成從系統(tǒng)設計、工程施工、技術研發(fā)、設備生產、營運管理到維修維護的千億級軌道產業(yè)鏈。
經(jīng)過兩年談判,大邱情定重慶。
于是,重慶順利簽下軌道交通跨出國門的第一單。
產業(yè)集群,讓重慶更具競爭力,使對外貿易從“大進大出”轉向“優(yōu)進優(yōu)出”。
“優(yōu)進”即有選擇地進口緊缺先進技術、關鍵設備和重要零部件,“優(yōu)出”即不僅要出口高檔次、高附加值產品,還要推動產品、技術、服務的“全產業(yè)鏈出口”。
于是,重慶乘勝追擊,整合重慶輕軌交通建設公司,為其他城市提供成套解決方案。
巴西圣保羅和印尼萬隆、日惹等城市的單軌交通工程都留下了重慶印跡。
截至2014年,國內外城市有意向建設單軌線路的總長度超過100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