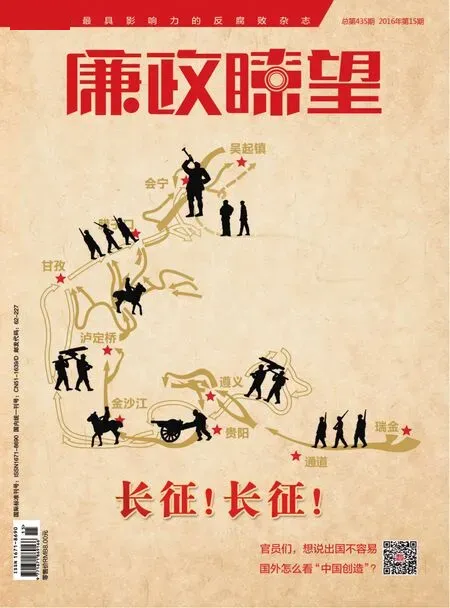父輩們的長征
文_本刊輯
?
父輩們的長征
文_本刊輯
艱苦奮斗、百折不撓

講述人:金一南,64歲,金如柏(時任紅二方面軍宣傳部長)之子——“父親的腳板,是踩著一路硝煙一路犧牲走過來的。”
1983年,父親去世的前一年。病房里,我第一次給父親洗腳,那雙腳板讓我呆住了。一塊塊老皮,洗起來硌手。我不明白,父親這樣的干部,進出辦公室有地毯,上下班有紅旗車,腳上為何如此粗糙?
父親的回答令我心潮難平。他說,紅軍長征時期,有一段連草鞋都沒得穿,腳板上磨出厚厚一層老繭。行軍下來,抬腳一看,厚繭中又嵌進許多沙粒、尖刺。剛開始還往外摳一摳,時間一長也顧不上了。最困難的一段是被分配到機槍連,不但要光腳行軍,還要扛沉重的馬克沁重機槍,走小路或爬無路的山。直到紅六軍團與紅二軍團會合,二軍團的同志才給了草鞋穿。
我一面給父親洗腳,一面抬起頭驚訝地望著他,該怎樣把當年那個赤腳行軍、赤腳沖鋒、赤腳扛馬克沁重機槍的他,與眼前這個被各種現代化醫療設備包圍的他相聯系?該怎么將現在扶著拐杖才能走路的父親,與當年那個闖過圍追堵截、走過萬水千山的父親相對照?
我只想說,他們都不是完人,奮斗過,也挫折過;勝利過,也失敗過。曾經過五關斬六將,也曾經敗走麥城。他們是一批不折不扣的真人。講述人:羅箭,78歲,羅瑞卿(時任紅一軍團保衛局局長)之子——“父親說,他們是長征的幸存者,是革命的幸存者,要記住那些為革命犧牲的人。”

長征時期,父親在保衛局工作,雖然直接參加的戰斗不多,但艱苦的環境都經歷過。像在若爾蓋草地,過去老以為過草地,其實是沼澤地,很多人都陷進去了,還有更大的困難。
聽父親講,過草地之前,戰士在街上買了青稞面,預備了五至七天的糧食,而過草地過了一個多月,糧食很快就吃完了,只能挖草根。有的戰士挖的是毒草根,就中毒死了,有的餓死了,還有一些傷病。沼澤地的蚊子很大,也沒有什么醫藥,還有掉進沼澤地里淹死的。
在沼澤地里,紅軍沒有遭到敵人阻擊,純粹是跟惡劣的環境做斗爭。到了最后,根本不需要找向導,因為后面的人跟著前面犧牲的尸體走就行了。
過雪山的時候,我父親有一匹馬。他身材比較高大,身體也比較好,基本上不騎馬,都給傷病號騎了,小戰士拽著馬尾巴。我父親去世的時候開追悼會,他的很多老部下的子女都來參加。他們說如果沒有羅瑞卿,就沒有他們。
愛兵如子、團結互助

講述人:朱和平,64歲,朱德(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之孫——“爺爺出身于忠厚勤勞的農民家庭,從小過苦日子。當時的紅軍戰士大都是貧苦出身,所以爺爺的愛兵如子,是有生活基礎的。”
紅四方面軍第三次走出草地,臘子口便是他們通往陜北的最后一道難關。
當時,部隊的物質供應十分困難,大部分同志身上穿的還是從蘇區出發時帶的衣服,有的已經爛得不成樣子了。爺爺也和同志們一樣,身上穿的衣服非常單薄。在分配戰利品時,同志們考慮到爺爺的年紀大了,一致要求把那件皮大衣筒子送給他。爺爺說:“這件皮大衣筒子是戰利品,應作公用。先放著,待天冷了時,給站崗的同志用。”
轉眼已是1936年的秋末時節,部隊來到甘南的渭水河邊。這里的天氣變化無常,中午太陽毒熱,夜里寒風刺骨。一天,爺爺辦完公后,去到總部電臺的駐地。
值班室在一家老鄉的舊房子里,墻壁裂了縫,紙裱的窗戶透了幾個孔,直往屋里灌風。值班的報務員正坐在電臺跟前,頭戴耳機,聚精會神地傾聽著黨中央電臺的訊源。他身上穿著單薄的衣服,冷風打來,身子微微顫動……爺爺目睹了這一情景,與報務員聊了幾句,便回去讓人把皮大衣筒子給他送過去。從此,這件皮大衣筒子就成了總部電臺的公用大衣。

講述人:左太北,76歲,左權(時任紅一軍團參謀長)之女——“父親在給奶奶的信中就寫過,要用長征精神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我想,只要長征精神永存,中華民族沒有做不成的事。”
1935年5月紅軍到達瀘沽,準備強渡大渡河。中革軍委決定父親率紅二師五團一部和軍團偵察連向大樹堡前進,擔任佯攻,鉗制和吸引大樹堡對岸之敵,以保證我軍主力經冕寧北進,從安順場搶渡大渡河。過夾金山時,父親病了,聶榮臻也病了,當時部隊只弄來一副擔架,行軍時,他們倆人總是互相推讓。山上白雪紛飛,上山的人都成了雪人。到傍晚,天氣奇冷,父親拄著拐棍,一步一喘地向上攀登。當翻過夾金山,與聶榮臻相遇時,兩人緊緊地握手,激動得熱淚盈眶。
后來,部隊在懋功達維鎮和紅四方面軍會合后,軍委決定將紅一軍團改編番號為第一軍,父親任軍參謀長。不久紅一軍被編入右路軍,擔任前衛的紅一軍奉命最先過草地。父親與同志們一起親嘗百草,找出30余種可食的野草野蘑以作大部隊充饑之用。經過6個艱難的日日夜夜,大家頂風雨、戰嚴寒,忍饑受凍,艱苦跋涉,終于走出了茫茫大草地。
不怕犧牲、勇往直前

講述人:徐文惠,77歲,徐海東(時任紅四方面軍獨立第四師師長等職)之女——“有的叔叔評價父親打起仗來是個兇老頭,打完仗是個好老頭。父親卻說,在戰場上你要不厲害,時機就丟了,是要犧牲人命的。”
1932年冬天,紅四方面軍戰略轉移,當時我父親已經當了師長,就讓他這個師擔任阻擊任務,阻擋國民黨對四方面軍的追擊。我父親這個師準備全方面犧牲,保衛大部隊轉移,所以沒有告訴我父親部隊要往哪轉移。
結果我父親這個師把敵人打退了,還占領了陣地。由于不知道四方面軍的位置,我父親便把四方面軍掉隊的、受傷的,還有地方武裝集結起來,重新組建紅25軍,堅持在鄂豫皖斗爭。
后來,紅25軍部隊打到離西安只有18公里的長安縣城,抓著了縣太爺。父親讓縣太爺給西安城防部隊司令打電話求援。西安方面回話,城防軍全調到西邊阻擊紅軍去了,這時候我父親才獲知毛主席他們的軍隊在哪個方向。
他們在西南公路抓了一個少將參議,從他口中也證實西安城防17路軍和胡宗南的部隊差不多24萬人,調往臘子口方向去阻擊毛主席他們去了。
隨后,在1935年7月,我父親和吳煥先政委在長安縣灃峪口開了個緊急會議,說他們這3000多人準備全部犧牲,也要把國民黨的二十幾萬軍隊吸引到紅25軍方向來,以減輕中央紅軍的壓力。
于是他們不走山區,走大路,專門暴露自己,就是為了讓敵人把槍口對著紅25軍打,讓中央紅軍能夠順利渡過臘子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