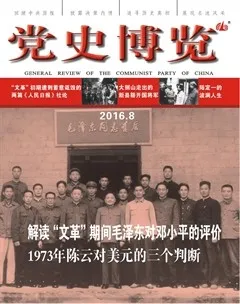博覽之窗
毛澤東:在敵后我們能夠建立大批抗日根據地
抗日戰爭中,毛澤東以其深厚的理論造詣和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對這場關系到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戰爭做出了許多科學的分析和預見。其中主要的四大預見,即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是一種戰略而不是戰術、在敵后能夠建立大批抗日根據地、抗日戰爭是持久戰并要經歷三個階段、中國將在抗日戰爭中實現民族解放,都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
抗日戰爭一開始,毛澤東就在考慮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后深入敵后開展游擊戰時建立自己根據地的問題。他認為:“在敵人后方創設許多抗日根據地是完全可能的,是十分必要的。”并認為根據地“是游擊戰爭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他把建立根據地作為抗日游擊戰爭六個具體戰略問題中的第三個問題提了出來,并做了充分的論證。毛澤東在指導各地游擊戰領導人工作時,總是強調部隊進入敵人后方后要以最快速度創建鞏固的根據地。根據地不僅有游擊隊,還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組織召開群眾團體會議,以充分發動人民群眾,還要大力發展黨組織。他強調,這是我們和歷史上許多流寇主義的農民戰爭的區別。
特別是,毛澤東多次預見我們不僅可以在陜甘寧建立鞏固的抗日根據地,而且預言我們可以在晉察冀等地建立抗日根據地。
(維之摘自《黨的文獻》2015年第5期,李君如文)
王震在“文革”中挽救北京農大
1970年9月,北京農業大學根據上一年中共中央《關于高等院校下放問題的通知》,整體搬遷至延安清泉縣清泉鎮。這以后的兩年是北京農業大學處境最艱難的兩年。由于清泉溝水質含有有害物質等原因,不少教職工因病請假離校,清泉溝校部人員大大減少,學校接近崩潰的邊緣。
1972年10月,周恩來特派王震視察陜北革命老區。王震當時是國務院業務組成員。他任農墾部部長時,對北京農大十分關照,曾在河北涿縣撥出約2萬畝的農場給北京農大作為半農半讀勞動實驗基地。在王震赴陜前夕,當時是國務院業務組列席成員的王觀瀾向他說:“到了陜西,希望您能關心一下農業大學。”王震答應了。幾天后,王震乘汽車來到了延安,召開了部分北京農大教職工座談會,聽取了一些教師的反映。后來他又回到西安,并且接見了北京農大沈其益副校長等人。
據知情人透露,王震回京以后見了周恩來,第一件事就是說北京農大在陜西辦不下去了。周恩來問:“那你說在哪里辦?”王震回答:“可以遷回河北涿縣,那邊有個2萬多畝地的農場,還是我給他們的,他們也可以勞動建校嘛!”周恩來同意了。
至1973年9月,北京農大全部遷回到河北涿縣,并接管了原已移交給4793部隊的農場。
(曉政摘自《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2012年版,歐陽淞、曲青山主編)
“文革”前的全國政協“雙周座談會”
“雙周座談會”是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建立的一種工作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及中央人民政府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界愛國民主人士共商國是的一種方式。座談會每兩周舉行一次,主要目的是溝通思想,就時事政治和統一戰線工作交換意見。從1950年4月“雙談”召開第一次會議到1966年7月停止活動,全國政協舉行“雙周座談會”共計100多次,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1950年4月到1954年6月,共召開55次座談會。這一時期,人民政協代行全國人大職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雙談”主要圍繞《共同綱領》所規定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族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斗”開展活動。結合當時新中國為鞏固新生政權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領域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雙談”主要進行了以下主題的座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運動、亞太地區和平會議籌備情況等。第二個時期:1957年12月到1958年4月,共召開座談會11次。1954年一屆全國人大召開后,全國政協完成了代行全國人大職權的歷史任務。從1957年起,由于“左”的錯誤路線的干擾,“雙談”內容由第一階段討論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轉變為對民主黨派的思想改造,主要是關于反右派斗爭、對右派分子的處理和民主黨派整風問題。第三個時期:1960年2月至1966年7月,共召開座談會50次。這一時期“雙談”討論最為集中的是“神仙會”及“雙百”方針問題,進一步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為右派摘帽問題,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等。
“文革”開始后,政協系統成為“重災區”,“雙周座談會”停止活動。
(義章摘自《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7期,劉維芳文)
胡喬木支持恢復設立國家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立國家主席是1954年憲法做出的規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國家主席受到迫害,其權力被取消、剝奪。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1975年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的職務。1978年憲法繼續沿襲了這個做法。1980年修改憲法時,要不要恢復設立國家主席,成為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對此,中央醞釀了一年多時間,一直沒有做出決斷。
1981年12月4日,彭真致信胡耀邦并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關于國家主席問題,需要中央做最后的決定才能提交修憲會討論。”1982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憲法修改草案,但關于設立國家主席,意見仍不一致。鄧小平主張設,有幾位同志不主張設。當天沒有得出結論,23日繼續討論。
胡喬木認為恢復設立國家主席是關系到國家長治久安的大事,遂于2月22日給胡耀邦、萬里、習仲勛、楊尚昆寫信,請他們在2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發言,大力支持鄧小平的意見,說這是一件關乎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正常化的久遠的大事。此信又加送彭真。
23日,政治局會議意見取得一致,恢復設立國家主席的問題得到解決。
(筱蕾摘自《胡喬木傳》,當代中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胡喬木傳》編寫組著)
被“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利用的“阿里事件”
1962年3月20日,桑給巴爾留學生阿里與蒙古留學生朋友到北京和平飯店買煙,阿里要求購買一條,由于當時煙草消費品供應緊張,加之懷疑外國學生違規倒賣,服務員只允許阿里購買一包,雙方由此發生口角。最后,服務員一方與非洲留學生之間發生了大規模沖突。
正當中方開始著手處理沖突之際,事態迅速升級。21日,受外交學會邀請來華訪問的非洲組委會執行委員、英共黨員霍爾納斯(牙買加人)態度極其強硬地要求中國政府公開道歉賠償。緊接著,非洲學生聯合會主席赫威提出了與霍爾納斯口徑一致的強硬要求。
很快,霍爾納斯進一步向中方施壓。他認為中國政府包庇了真正的罪犯,表示已對雙方的友誼“喪失信心”。同時,公安部門的調查受阻,阿里在霍爾納斯的勸說下拒見公安人員,學校對非洲學生的勸說和解釋工作也遭到非洲學生聯合會的阻斷。
中方開始懷疑非洲留學生事件并非偶然,霍爾納斯的“越俎代庖”以及非洲學生的激烈舉動背后可能是一場國際陰謀。不久,中方的猜測得到了蘇丹和平人士凱爾的印證。凱爾透露霍爾納斯與英國代辦以及蘇聯使館往來密切,常協助蘇聯使館和英國代辦處秘密散發宣傳品,宣揚修正主義觀點并攻擊中方。凱爾的提醒使中方迅速改變了對事件的態度和定性,最后這一事件被認定為“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分子利用打架問題,從中挑撥、公開煽動反華活動,將個別的打架事件升級為中國人和非洲人之間的問題”。
“阿里事件”引發的風波直接導致28名非洲留學生退學。
(逢周摘自《黨史研究與教學》2016年第2期,蔣華杰文)
波蘭“十月事件”引發的一場筆墨官司
1956年10月,波蘭和蘇聯之間爆發了一場異常尖銳的干涉和反干涉的斗爭,雙方險些兵戎相見,史稱波蘭“十月事件”。
事件發生后,中國駐波蘭大使館擔負著跟蹤形勢、調查研究、向中央提出報告和建議的重大任務和責任,使館每周召開各種形式的務虛會,聽取方方面面的反映,分析報刊的報道和文章,綜合各方面的看法和論點,最后形成了使館多數人和新華社駐華沙首席記者謝文清一個人觀點對立的局面。
大使、參贊和與會的多數人認為波蘭“十月事件”的性質是右派翻天,反蘇反社會主義。但謝文清卻不這樣看。他比較了解波蘭社會的情緒和反映,認為波蘭受到了不公正對待,波蘭“十月事件”的性質不是反蘇,而是反對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
在“十月事件”期間,毛澤東多次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或政治局會議,分析波蘭“十月事件”的性質,確定中國的態度和政策。毛澤東在談到駐波蘭大使館發來的電報時,說:“我們大使館的看法不大對頭,他們比較強調波蘭反蘇情緒高漲,很可能從蘇聯駐波蘭大使那里聽來的。我駐波使館另外一些同志覺得波蘭的情況是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結果。這兩種意見,看來后一種意見是對的。”毛澤東的聲音傳到波蘭,打動了波蘭人的心,也為使館和記者之間的筆墨官司畫上了句號。
(村夫摘自《縱橫》2016年第1期,劉彥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