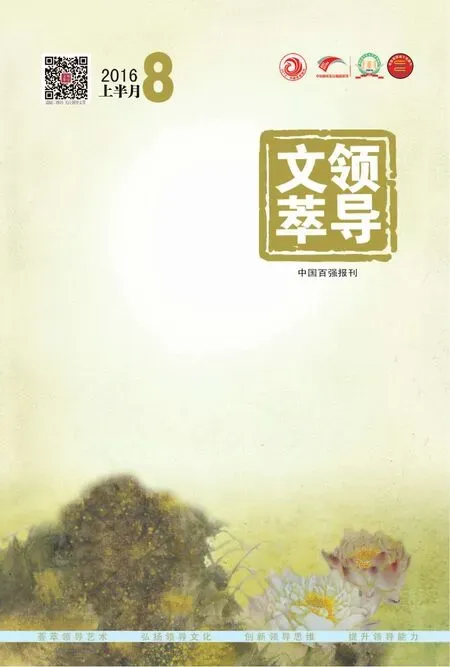70年土地使用權考驗執政智慧
馬光遠
最近,溫州一則關于住宅土地使用權到期,如果要續期,需要繳納高達三分之一房價的費用的報道,引爆人們對房屋土地使用權年限的擔憂。
盡管溫州有關部門事后做了所謂的澄清,“近期媒體報道收取幾十萬元出讓金才能續期是對信息的誤讀”。但從媒體事前的報道,以及溫州國土局有關部門的介紹看,準備收費,而且準備高額收費肯定是真的。
土地使用權的70年大限問題,歷來都被視為是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高懸之劍,如何處理,攸關民眾的切身利益,考驗政府的智慧和執政能力,因而備受關注。溫州的案例再一次給全國的房東敲響了警鐘:一旦到期,我們的房子將如何安放?
對于70年大限之后,土地使用權如何處理,早在《物權法》立法之時就引發了廣泛的爭論。在土地國有的情況下,土地使用權期滿之后是自動續展,還是無償收回,《物權法》最終作了一個妥協各方利益的考慮,“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間屆滿的,自動續期。”為了確保《物權法》早日出臺,就選擇了擱置爭議,模糊處理的立法技術。但事實上,當時占絕大多數的意見建議,土地使用權到期后只交象征性的費用自動續期。
媒體報道的溫州收取高額續費的辦法,意味著《物權法》取得的巨大進步,又倒退回1990年國務院頒布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的規定,這個條例首次規定了“居住用地最高年限為70年”,而且還規定:“土地使用權期滿,土地使用權及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著物所有權由國家無償取得。土地使用者應當交還土地使用證,并依照規定辦理注銷登記。”這個規定,可以說,充分暴露了“公權”和“私權”兩種權利在博弈中的不對等地位,也體現了對私人產權的極其不尊重的立法指導思想。
歷史總是在進步,3年之后出臺的《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相對于這個規定,就有明顯的進步:房產土地使用權到期,房產所有人必須提前一年申請續期,否則土地使用權將會由國家無償收回。從1991年到1994年的《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再到《物權法》,在70年土地使用年限的問題上,最起碼大家就“自動續期”達成了基本的共識,而且即使收費,大家也認為應該是象征性的。媒體曝出來的溫州的做法可以說是置《物權法》與法治的進步于不顧,引發民眾不必要的恐慌,令人匪夷所思。
眾所周知,中國民眾對“70年大限”的恐懼,一是基于對高房價的恐懼,用終其一生的收入購置房產之后,還要在70年后續交高昂的土地出讓金,這無法讓民眾不焦慮;二是基于對公權力的恐懼,在公權和私權沖突的情況下,公權顯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基于這兩點,每一次法律對“70年大限”的完善,都意味著民眾要經受一次精神的折磨和制度性焦慮,這是必然的。
“70年大限”之所以引發焦慮因為這不僅僅是個體的焦慮,而是能夠影響中國社會未來發展的。住宅土地使用權到期后,高價續費,既違背常理,也和基本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馳。如果承認房子是有限的租期,那根本沒有任何理由未來還要征收什么房產稅,如果要征收房產稅,就請把房子的“永久產權屬性”還給房屋業主。溫州這種明顯違背《物權法》基本精神的做法已經透視出地方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試探性舉措”,必須引起人們的警惕。
對于70年后的問題,必須遵照《物權法》關于“自動”續期,以及象征性收費的原則。在這個問題上,想無償收回,讓民眾的房子漂在空中,或者高價續期,再賣一次地皮,都是民眾無法接受,更是中國社會的穩定所不允許的,如果以此來試探,甚至挑戰民意,那意味著突破了某種底線,后果不堪設想。
事實上,一個國家規定什么樣的產權制度,就會出現什么樣的建筑,很難想象,在70年的土地上,能生長出對土地恒久熱愛的公民和百年的建筑,也很難想象,在40年的廠房里,能生長出百年基業的企業。中國人缺乏長遠的打算,中國企業現在很少有百年的戰略,土地使用權的期限,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70年土地使用權考驗執政智慧,應盡快啟動《土地管理法》的修訂,提高土地使用權的期限,并對房屋使用者和買賣者實行區別對待政策;如果仍然要堅持70年的期限,也一定要明確70年后土地續期“象征性繳費”的原則,這既是得民心之舉,更是貫徹物權法的法治原則和精神。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