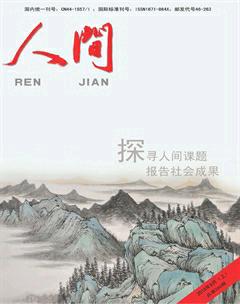上海女傭與城市現代化書寫
——以張愛玲《桂花蒸·阿小悲秋》為例
高麗君
(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北京 100024)
上海女傭與城市現代化書寫
——以張愛玲《桂花蒸·阿小悲秋》為例
高麗君
(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北京 100024)
張愛玲在《桂花蒸·阿小悲秋》中描寫了上海娘姨丁阿小日常瑣碎而艱辛的生活,從側面反映了上海城市現代化進程對其生活的多方面的影響,探討了上海女傭與城市現代化之間的復雜關系,引人思考。
女傭;都市;阿小;張愛玲
女傭敘事在中國文學中一直是比較普遍和常見的,盡管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稱呼、不同的故事,但都或多或少通過對女傭的描寫展現其所處時代的社會狀況、日常風景,從而表現一個時代的變遷及其深層的歷史內涵。其中,張愛玲的《桂花蒸·阿小悲秋》是比較特殊的專門描寫上海女傭的作品,以其女性特有的敏感以及上海生活的切身經驗,為我們展現了上海娘姨丁阿小瑣碎而又艱辛的日常生活,也從側面反映了城市現代化進程對其生活的影響以及背后隱含的深層含義。
一、城市現代化與女性自由獨立意識
從晚清上海開埠以來,越來越多鄉間婦女進入到城市中,尋找生存的機會。而“女傭”因其工作的簡單,成為當時鄉間婦女的最普遍的選擇。根據當時資料記載,“合城內外,洋場南北,歲有百金,家三四口者,無不雇傭傭婦,大抵皆自鄉間來,”“婦女貪上海租界傭價之昂,趨之若鶩,甚有棄家者”。[1]程乃珊在《上海灘的姨娘》一文中,曾經詳細介紹了上海女傭的歷史背景與工作性質,她寫道,“要說上海最早的職業婦女,當推上海的保姆,舊時稱娘姨;這支氣勢浩蕩的勞動娘子大軍,相信其歷史,遠要悠長過上海的紡織女工和有‘湖絲阿姐'之稱的繅絲女工。”[2]根據程乃珊的介紹,與封建時代的婢女、丫鬟賣身為奴不同,早期的上海女傭有著自由的身份,因而她們可以“有東家不打打西家之工的自由選擇”。她們靠著自己的辛勤勞動獲得薪酬,從而不僅能夠養活自己,甚至還能贍養家人,尤其是一些在外國人家“走做”的娘姨,其高額的月薪遠遠超過家里的男人。
張愛玲筆下的丁阿小就是一個在外國人家“走做”的娘姨,所謂“走做”就是我們現在常見的鐘點工,由于西方人比較講究隱私,不喜歡有陌生人闖入自家的感覺,所以通常請的娘姨都是不包食宿的,因此這類娘姨的薪資都會比較高,她們會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日常工作的質量上,較少參與東家的私人生活。隨著城市的進一步發展,這種靈活的工作方式也越來越為上海的白領階級所接納。從職業層面考察,這些進入城市的上海娘姨職業化程度越來越高,而且她們已經能夠擺脫對男性的依賴,獲得了經濟上的獨立,自己養活自己,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可以說,正是由于城市現代化帶來的商業環境以及城市自由思想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得自由獨立的意識在上海女傭心中滋生,這可以說是一種女性進步,也是城市現代化的進步。像阿小這樣的女傭除了認真完成每日的基本工作,還會根據東家指示不斷嘗試新鮮事物。根據工作的需要甚至學會了第二語言——英語,能夠幫助東家應付電話及訪客。她雖然有丈夫,但是兩人聚少離多,平時都是她一個人帶著孩子生活。在都市生活的巨大壓力下,即使生活如此艱辛,即使地位如此卑微,阿小依然沒有喪失尊嚴與責任感。在這里,我們仿佛看到的是一個現代社會的女秘書及單身母親的奮斗史。所以說城市的現代化,為上海的娘姨們提供了一個更為自由開放的工作環境以及生存空間,而脫胎于鄉村的上海女傭也在城市現代化的進程中獲得了女性意識的解放。
二、城市現代化對日常生活模式的影響
從這些娘姨們進入城市開始,她們的生活便日益受到城市生活模式的熏染。“城市是成長過程的結果,而不是瞬間的產物。”[3]她們出于職業需要,不斷適應東家的生活節奏,接觸更多的現代化生活模式。從飲食、服飾、語言等基本生活所需,到消費、休閑等其他的生活方式,都能看到城市現代化的痕跡。例如,在《桂花蒸·阿小悲秋》中,阿小也會幻想如果自己再年輕一些,可以像秀琴一樣做女大學生的打扮;她寧可用缺了角的小粉鏡子梳妝,也不再像古時候的女子一樣在水里照自己的影子;她學著用英文給東家的客人回電話,努力嘗試著翻譯每一段留言。她雖然做著料理衣食、服侍起居、端茶送水這些在鄉間常做的事務,但是很快便儒染了城里的氣息和做派。甚至閑暇之時,也會去電影院看電影以作消遣。她們一方面孜孜不倦地學習著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掌握各種都市生活的本領,另一方面也樂此不疲地享受著現代器物的帶來的新鮮與便利。在這方面,阿小可以說更多的體現了上海姨娘的一種智慧,她能夠比較游刃有余地承擔東家哥兒達的要求和刁難,也能夠準確地拿捏揣摩哥兒達的意思,從而圓滿地完成自己的任務。從女性婚姻角度來看,阿小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被看作是勇于反抗宗族禮法的。她從鄉村進入城市,和做裁縫的男人同居,并沒有舉行象征結婚的儀式——“花燭”。雖然阿小的反叛并不像二三十年代知識女性那樣歇斯底里,甚至她自己僅僅是需要找人搭伙過日子,并沒有反叛封建禮教的意識,但是她確確實實地踏出了封建牢籠的第一步,這是實實在在的。
當然,城市現代化的確在不斷改變上海女傭的日常生活,而女傭因其職業性質能夠進入生活中較為恒常的日常面,而張愛玲以其女性的敏感,借女傭視角能夠窺見都市生活的內部。都市生活確實為女傭帶來了極大的解放,但是這種解放也毫無意外地摻雜著其消極的一方面。由于城鄉經濟社會的巨大差異,往往會給這些來自鄉間的沒有什么文化的婦女造成一種極度的心理不平衡性,甚至現代都市的物質化、商業化與畸形的道德觀也往往會滲透到女傭們的人格建構中。阿小雖然盡心盡力完成工作,但她很愛面子,虛榮心很強,甚至會嫉妒同鄉小姐妹的生活;她用粗俗的鄉村野話罵不上進的兒子百順,卻又寄希望兒子將來能夠有體面的工作;她圓滑地處理與東家的關系,隱藏自己的情緒,在東家面前滿臉堆笑,在背后卻又是嚼舌根,罵東家們“作臟”。阿小的一系列表現正是在都市社會的物欲輾壓之下,內心受到劇烈沖擊從而產生的一種不平衡性。魯迅先生曾經在《阿金》一文中,寫了那種比較極端的畸形人格。由于受到都市商業環境的長期浸染,阿金釋放了被壓抑的野性,她自私自利,利益至上,在里弄街巷談論兩性關系,有著多個姘頭。正如阮蘭芳所說,阿金身上帶著更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里,新舊混雜,歐美商業經濟與中國傳統封建文化的嫁接使得各種新型人格帶著分裂錯位、畸形融合的特征。”[4]阿金更多體現了現代都市影響下道德淪喪的一面。
三、現代都市夾縫中女傭的尷尬處境
張愛玲生于城市長于城市,都市環境的長期浸潤以及對城市的喜愛與習慣,使得她有著天然的都市感。都市日常生活的經驗構成其筆下主要的內容,能夠深入到世俗飲食男女內心深處,來關照都市,表現世間人生百態。正如李今所說,“她的寫俗是為了透視人的本性與日常生活的邏輯,把形而下的俗事作為形而上的問題而進行理性思考。[5]
在《桂花蒸·阿小悲秋》中,阿小是在外國人哥兒達家做幫傭,然而她常常出入的地方是公寓的后陽臺和廚房。對當時上海大部分女傭來說,雖然她們能夠使用到更多諸如冰箱、咖啡機等現代化家用設備,能夠看電影以作消遣,但是從本質上來說她們卻并未與現代都市完全融合。我們能夠從她們所處的空間,看到更多她們與東家的階級差異,她們雖然擺脫了鄉村的空間束縛,然而在都市中依然處于一種邊緣的狀態。她們在這繁華的都市中,求得一席安身之處,在都市夾縫中努力地生存著。對阿小而言,做好本職工作,拿到薪資養活家庭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她們更多地關注自身的生存困境,“戰時自來水限制”,“公寓里每天只有一個鐘頭有自來水”,“多余的面包票”,“戶口粉戶口糖”。[6]張愛玲為我們展示了一個變化動蕩的亂世中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與“悲愁”。所以說,縱觀全文,阿小“悲秋”不僅僅是個人生存艱難的寫照,而是超越個人上升到時代、歷史的大悲。
總之,女傭書寫可以看作是對“鄉下人進城”模式的延續和超越,都市的現代化與鄉村的落后愚昧已經不再是作家關注的焦點,作家的筆觸更多的觸及現代都市中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分析女傭這類普通的底層女性是如何適應都市,如何在都市的大環境中自我建構。可以說,在當代,現代都市與女傭的故事依然在繼續,依然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1]李長莉.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生活與倫理的近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2]程乃珊.上海灘的娘姨[J].文史博覽.2005年。
[3]孫遜、楊劍龍主編.閱讀城市::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4頁。
[4]阮蘭芳.向都市遷徙的女性部落——有關上海女傭的三個文本考察[J]. 文藝理論與批評.2012年。
[5]李今.日常生活意識和都市市民的哲學——試論海派小說的精神特征[J].文學評論.1999年第6 期。
[6]張愛玲.張愛玲全集:紅玫瑰與白玫瑰[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年。
I207.42
A
1671-864X(2016)09-0014-02
高麗君(1990.10--);性別女,籍貫:山東臨沂,學歷:碩士在讀,畢業于(或者在讀與)中國傳媒大學;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