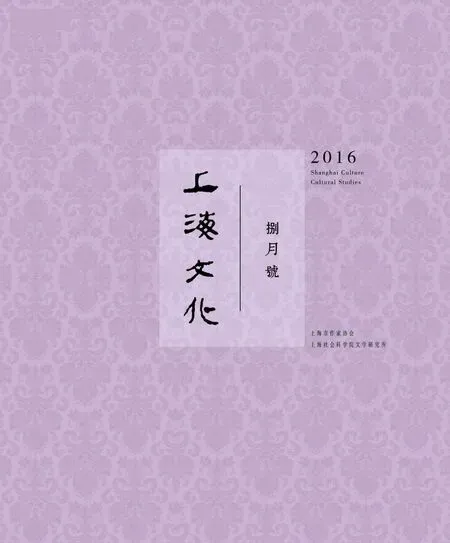中國畫的“死”與“生”
——以姜永安的水墨創作為中心
劉旭光
中國畫的“死”與“生”
——以姜永安的水墨創作為中心
劉旭光*
中國畫的觀念在過去100年中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在藝術探索上也經歷了復雜而多變的實踐演進,糾纏在革命與傳統、東方與西方、現代與古典、現實與理想之間,其審美特性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其間,曾經由于趨向西方的寫實化而喪失民族特性,但最終,以姜永安為代表的當代國畫家,在審美現代性與民族傳統的筆墨觀念和審美特性中,找到了融合點,創造出了既富于筆墨意蘊,又具有高度寫實性的水墨藝術,從而起死回生。
中國畫 水墨 筆墨 姜永安 寫實
從1918年陳獨秀與美學家呂澂在《新青年》上號召“美術革命”,到現在已近百年,在這100年間,我們的民族繪畫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無論是藝術語言還是藝術觀念,無論是繪畫藝術的功能還是觀看藝術作品的方式,都發生了驚人的變革。百年之間,中國畫糾纏在革命與傳統、東方與西方、現代與古典、現實與理想之間,觀念沖突之大,風格變化之烈,令人驚訝。問題是,經歷百年變革,我們得到了什么?
2013年,國畫家姜永安完成了他的作品《成長》,這似乎就是革命后的國畫所取得的成就。但問題是,這還是“國畫”嗎?

姜永安,2013,《成長》
“國畫”這個詞產生于20世紀初期,它的對立面是西方繪畫,如油畫、水彩、水粉等作品,但這個詞沒有明確的內涵,似乎凡中華民族的繪畫作品,都應當叫“國畫”,比如文人畫、工筆畫、壁畫、年畫、界畫等等,相對于“西洋畫”,這都應叫“國畫”。但在實際的應用中,這個概念的內涵又有所收縮,大概指以水墨絹紙為載體的民族藝術,特別是以筆墨為主導的山水畫和以線條為主導的人物畫,以及工筆畫與寫意花鳥畫,實際上狹義的中國畫就是文人畫,但是這個概念的狹義應用不斷地受到挑戰。挑戰的背景是:中國畫在百年之中的變革,一個目的是為了能在造型與表現性上和西畫比肩,另一個目的,就是革文人畫的命,擴大“中國畫”內涵。這兩個目的既有交集,又各有所向。
姜永安的這件作品還算是“國畫”嗎?
這張畫從材料的角度講,當然是國畫:宣紙、毛筆和水墨這都是真正中國的材料,但拋卻材料的考量,這件作品如果還是“國畫”,那就意味著,它應當具有我們在說“國畫”這個詞時所預設的那種風格與美感。這張畫有一種靈動、飄逸的韻味,這種味道源自“水”與“墨”、“紙”之間的相互作用,寫意繪畫所側重的筆墨功夫,墨色的層次與變化,墨與水之間的渲暈,留白的應用,對線條的簡潔、準確與流暢的呈現,特別是對“意”的捕捉與傳達,都體現出對以文人畫為基礎的寫意美術的承續,它有一種可以被稱為“中國式的”審美感受:含蓄,雋永,言有盡而意無窮!
然而姜永安的這張畫,還有一種超越于寫意精神之上的新的氣質,超越于我們對于中國畫的預期而發生了。
傳統的中國人物畫,簡約者不求形似,但求“氣韻”,以線條勾勒出五官輪廓,也以線條勾勒衣服與身體的形狀,于簡略中現“神氣”;精細者能根據面部固有之凹凸和結構關系,淡墨勾勒后積染賦色,雖無明暗塊面變化,但也能得其形似。但姜永安畫面中的人物不是以線條的方式勾出輪廓,而是通過墨塊與留白完成塊面造型,然后借助水墨之交融所產生的層次感,以及墨色五分所構成的明暗變化,完成富于立體感的,甚至是塑造感的形象。
這個形象令人震撼,筆墨交融之處,墨法豐富而多變,韻味實足,筆法精致,線條準確生動。同時,筆墨塑造出了一個具有心理真實感的意象,從而把筆墨的藝術語言的美感與真實感交織在一起,達到虛實相生之境。“虛”在于由水墨變化和留白所營造出的空靈之感,“實”在于水墨塑造出的富于真實感的形象。同時,對于形象之神韻的呈現,對于情感狀態的呈現,生動細膩,畫面中有一種源自令人驚嘆的造型能力所造成的強烈視覺沖擊,水墨的寫意性與造型的精準交相輝映,這顯然呈現出古人未達之風貌。這似乎就是中國畫革命的結果。
1918年在陳獨秀呼吁美術革命的時候,他認為革命的理由是國畫沒有寫實性。這個觀點康有為及其信徒徐悲鴻都堅信不已。1918年之后,劉海粟東渡師法印象派、徐悲鴻西渡攻晚期古典主義油畫,兩人歸國后以西式的藝術觀念重新建構中國的美術體制,強調造型能力在美術中的基礎作用,強調色彩與明暗的表達;與此同時,魯迅等人倡導能夠反映人生、反映社會的美術,要求美術能介入生活,而不僅僅是審美的,這就要求繪畫在題材與藝術語言上的改變。這些主張對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國畫造成了強烈影響,當一批受過西式造型藝術訓練的油畫家由于現實的諸多因素拿起毛筆畫“國畫”的時候,國畫的風貌為之一變。變化之一,由于良好的素描與速寫能力,使得畫家們能夠描繪出準確而生動的形象;變化之二,由于具備了造型能力,畫家們可以去寫生,可以對外部自然進行準確的摹寫;變化之三,“色彩”這個傳統國畫相對較弱的部分,受到西方印象派的影響而趨于強化,并進入到國畫之中。這三個變化,形成了國畫領域中的文化激進主義,以中西合璧為旨,實際上創造出一種新的美術形式。
但這種變化對于“國畫”意味著什么呢?這構成了中國畫在觀念上最核心的問題——洋化了的國畫還是國畫嗎?在這種變革求新的同時,有一批傳統文人畫家還在堅守,最初是任伯年、虛谷、蒲華、吳昌碩等人以傳統的技法,在題材與筆法上稍作更新,以海派之名恪守傳統國畫之旨,之后有金城、陳師曾、吳湖帆、張大千、黃賓虹、齊白石等人,堅守與弘揚國粹,以文化保守主義的姿態,師古法,體己心,仿古而不泥于古,堅持文人畫傳統。
當然還有一批國畫家,去發現國畫中的富于現代性的部分,與西方的現代藝術觀念結合在一起,加以弘揚與改造,創造出具有現代性的美術,比如林風眠、朱德群等,但這些現代美術作品實際上沒有被納入到“國畫”的體制中來。
有人變革,有人堅守,有人折中,有人立足現代而融會中西,所有這些探索都是在“國畫”這個框架中完成的,這種創作上的多元探索必然反映為觀念上的多元甚至混亂。俞劍華在20世紀40年代曾經概括過人們對于傳統國畫的不滿:“一、以國畫為出世而非入世也。二、以國畫為臨摹而非寫生也。三、以中國畫為崇古而非進化也。四、以中國畫為不合時代也。五、以中國畫不合西法也。”①俞劍華:《國畫研究》,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頁。這五條意見大概可以涵蓋激進的批判立場的主要依據,這種批判自陳獨秀、康有為起,經徐悲鴻、江豐,再到吳冠中、李小山,綿延近百年,構成了對于“國畫”的總體性否定,但這種否定卻沒有精細劃定“國畫”的內涵與外延。
文化保守主義者當然不會認同這種否定,黃賓虹在給傅雷的信中疾呼:“畫有民族性,無時代性。雖因時代改變外貌,而精神不移。今非注重筆墨,即民族性之喪失,況因時代參入不東不西之雜作。”②黃賓虹:《黃賓虹藝術隨筆》,盧輔圣編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231頁。——純粹的民族性,是對國畫的最主要的辯護辭。但這一辯護并不有力,堅守筆墨,會最終把國畫定格為“老人墨戲”。問題是,觀眾看不懂筆墨,除了那些程式化的意象,觀眾還要求藝術有更多的內涵。不能滿足這兩點,國畫必將淪為同仁圈子的游戲與文人自我標榜的手段。在這一點上,陳獨秀是對的,俞劍華所概括出的那五條意見是必須要正面回答的!但黃賓虹文化保守主義的合理性在于:如果放棄了筆墨傳統,國畫和水彩畫又有什么區別?
這種紛繁的探索與觀念沖突在新中國成立之后被強制性地打斷并掩蓋起來,徐悲鴻建立在西方造型觀念之上的國畫觀,借助于中央美術學院的引領作用而成為正統,在新社會對于繪畫的現實需要面前,國畫家們不得不走向寫實性,走向寫生,走向對社會場景的呈現。從學科體制上,國畫成為繪畫專業的一個方向,而西方的造型觀念與方法,如素描、速寫、色彩、透視等課程成為所有繪畫專業的基礎。山水畫在李可染、張仃等人手中為之一變,對畫面構成的經營與結實的造型結合在一起,再佐以明暗處理與光影效果,加上自然寫生,形成一種新的山水風貌,這種山水畫可以為黨的文宣工作所用,可以對時代的境況有所反映,這就正面應答了俞劍華所概括出的那五條批判意見,從而使國畫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獲得存在與發展的合理性。這種新國畫或許也還在筆墨的傳統語境中,但如果把這些創作放在文人畫的歷史傳統中,可以坦率地說——意境全無。
人物畫的發展顯然更直接地走向對造型能力的追求,走向寫實性。徐悲鴻、方增先等人的國畫人物畫,實際上是用毛筆完成的“速寫”與“慢寫”,雖然有扎實的造型能力支撐,雖然保留了傳統的經營布局,但是這種人物畫更像是速寫與水彩的結合,實有余,韻全無。
很難評價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到80年代的中國畫。如果說它在“進步”,那么進步的指向顯然是“造型能力”,以及對社會生活的反映。這種創作強化了國畫的技術性,卻不再是個體心靈的自由呈現,不是寫意,不可“澄懷味道”,不是“臥游”的對象,更不是寫胸中逸氣,民族繪畫的審美精神,一變而為寫實精神,雖然面貌一新,但離“國畫”之旨已遠,因此,人們更愿意稱之為“水墨”,或者“彩墨”,而非“國畫”。這似乎意味著,“國畫”已死!
但是從國畫向水墨的轉變,顯然創造出了一種更加新穎,更具有創造性,更具有當代性的藝術形式——水墨。
水墨的誕生,意味著“文人畫家”的退場和“國畫藝術家”的誕生,這種變革有一個顯見的好處——國畫藝術家的專業化!不同于以文人士大夫為主體的傳統國畫,在新的藝術體制中培養出來的國畫家,在其訓練過程中,擺脫了文人身份而專業化了。國畫的學習者們接受傳統的國畫教育,他們在臨摹古畫、書法的學習中,在對傳統國畫形式的學習中,構成他們的專業性,但他們又接受西方的造型藝術訓練。他們有不錯的素描功底,有良好的速寫能力;他們也學習過基本的油畫技能,對于色彩以及肌理與質感有深入的體悟;他們有近代之前的國畫家所不具有的造型能力。同時,他們又學習文人畫之外的中國美術、壁畫、巖彩、民間美術,凡是這塊大地上發生過的美術形式,他們都不拒絕,他們所理解的國畫,早已超越了文人畫的狹小范圍。更為重要的是,當代美術學院體制培養出的國畫家,具有現代甚至后現代的形式感,他們不斷地嘗試新材料、新技術,追求新的表達效果,他們的藝術語言極其豐富,他們不拘泥于任何一種形式,同時他們又以一種真正的后現代狀態,不斷地把諸種藝術語言混合在一起,手段豐富,效果新奇。由他們所創作出的“國畫”,以畫面效果為指歸,不拘泥于材質,不拒絕諸種藝術語言,隨物賦彩,隨心所欲。應當說,在經過近60年的積累之后,一種新的“中國畫”似乎已經孕育成型了,它以中國諸種民族藝術形式為主導,雜糅種種藝術語言,有強烈的民族意味,卻又與傳統截然不同,這里包含著一種真正令人期待的新藝術樣態與新美感的萌芽。
這就意味著中國畫在兩個層面上實現了突破:一是造型能力,二是材質技法。這兩個層面的突破匯集在“水墨”這個范疇之中,水墨的誕生,還意味著對于水墨這種媒介形式的更深入的探索與開拓。傳統國畫對于筆墨的執著,實際上轉化為現代國畫家對于水墨的堅守。
水墨有自己獨特的藝術語言,如何掌控和使用這種語言,是需要專門探索的。對水墨語言的探索,構成了這門藝術的自律性。水墨本身是一種藝術語言,無論畫什么,筆力墨色,以及筆墨之和,永遠是水墨藝術的藝術性所在。水墨無關時代。對于藝術語言的探索,藝術在技藝與風格方面的創造,有一種超越性——它無關城堡上旗幟的顏色,也無關世間冷暖,藝術家可以把藝術技藝與藝術語言的追求烏托邦化,變成一種宗教般的執著與追求,無關世事,有益精神。
從藝術自律性角度來看待水墨,意味著水墨創作在題材上是自由的,它究竟呈現出的是山水,是現代都市,還是古典人物,這無關緊要。即便用水墨來描繪現代人的欲望情調,也應無所掛礙,水墨無關時代。但另一個方面,水墨又體現出強烈的時代性。每一個時代都有與時代的社會形態相關的形式感、節奏感、美感。特別是,人的情感及其結構本身也是社會歷史的產物,宋人觀看山水的方式與我們的時代是不一樣的,元人觀看藝術作品的方式也與我們不同,因而何必執著于宋元或者明清?模仿永遠不是藝術,既然水墨藝術面對的時代的眼睛與心靈,都會發生改變,為了能夠讓這些時代之眼在水墨藝術中獲得愉悅,就應當引領與滿足這種時代之眼。
用水墨這種民族性的媒介,去呈現與表現當代生活、當代心靈,這當然可以。水墨創作真正困難的,或者真正具有藝術性的部分在于:找到水墨最獨特的話語方式,找到水墨最適合的表現領域,以自我之聲,說屬我之事,水墨將因此而解放,也將因此而自律。對水墨媒介的這種自律與自覺正是姜永安創作的意義所在,但對于水墨這種民族性媒介的堅守還不能算是對于國畫的傳承。我們回到姜永安的創作,再來看看這些作品在什么意義上克服了國畫的局限,使國畫跟上時代的要求,在什么意義上,這些作品又是國畫精神的傳承?
姜永安的水墨畫顯然有一種強烈的反映現實的能力,水墨的自由使得它可以介入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而不需要像傳統國畫一樣囿于固有的意象系統與符號系統,這是國畫的真正解放。而水墨同樣具有反映與介入現實所需要的表現力,比如姜永安創作的《中國“慰安婦”寫真》,這種表現力顯然是傳統國畫所達不到的。

姜永安,2014,《傷逝的肖像·中國“慰安婦”寫真》
國畫創作的方法在這些作品中顯然有重大的變化,古人的創作方法,無非是以下幾條經驗:第一,“師古人”。這是最便捷之路。師古的好處在于通過對古人的模仿,以一位大師為追隨的對象,可以用最集中最直接的方式,達到與大師同樣的高度。藝術中的復古主義與古典主義的合理之處就在于:它可以讓一位初入門者很快達到一個相對高的水準,攀上巨人之肩,當然會有不同眼界。雖然“筆墨”可仿,“功夫”難得,但只要有恒毅之心,倒也可成一家,雖然不見個性,但易見成效。第二,“師自然”。用古人的話說是“搜盡奇峰打草稿”。盡管古人說這句話的本意或許與我們現代的理解還有不同,但是從近代以來的繪畫觀則直接把這個觀念與西畫的寫生觀結合起來。通過對自然的臨摹,可以間接地解決師古觀帶來的程式化、僵化,解決創造性不足的問題,自然的形式永遠超出人的想象,跟隨自然的腳步,體味自然的四時變化,然后把觀察與體悟的結果訴諸筆端,通過寫實性來彌補傳統國畫創作程式化的問題,創造出與古人不同的國畫景致。這種觀念由于現代以來的現實主義美學的勝利而得到強化,也由于學國畫者往往也受一些西畫的造型能力的訓練,因而有比古人更強的寫生能力而得到廣泛應用。然而,自然是沒有靈魂的,對于繪畫而言,自然是一個有待填充的空白,只有把精神性因素賦予自然,自然才能成為“美的”。因而,單純地跟隨自然,是無能的表現。自然所呈現出的,必須被心靈點化之后,才能成為“屬于藝術的自然”。第三,“師心”。“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我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一畫論”,這些古人的名言,表明古人知道,無論是自然還是前人,都只是創作的手段,藝術的目的是“我”,而“適我無非新”,要出新,只能返身而誠,回到自我當中去。化千里河山于咫尺,盡四時變化與一方,以須臾納無限,以沉靜納生成,創造出一方心靈之境,這才是國畫藝術的真諦,它需要以師古的方式掌握技法,以師自然的方法獲得素材,但真正重要的是,它需要一顆自由與飽含深情的心靈來掌控兩者。這是中國畫的詩性與哲性之所在。但“師心”的困境在于,胡思亂想與肆意放縱是不是師心?
這三種創作方法如果能夠融合,當然最好,但師古難出新;寫生如果沒有造型能力作為支撐,實際上無法實現;師心之法,前提是創作者具有筆墨技法和寫生造型能力,能夠心手相應,從而實現自由表現。從以上三個角度看姜永安的創作方法,實際上是把寫生與造型放在了最基礎的部分,而把師古隱含在筆墨之中,最終實現自由表現心靈,而不僅僅是摹寫對象。
水墨在姜永安的作品中所體現出的表現力和創作力,顯然已經把古人拋在身后,讓水墨畫成為反映時代的手段,并且,從造型能力的角度來說,卓絕而完美。這是新創作,這是新藝術,那么,這是不是“新國畫”?
從材質與技法的角度來說,當然是國畫,傳統國畫對于水墨的應用與技法上的探索,被繼承在這些作品中,在師古方面,當代國畫家并不遜于任何時代,由于復制技術與圖像顯現技術的應用,當代國畫家們甚至比古人更了解他們自己。從作品所呈現出的造型能力來說,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一點是,必須承認,即便是傳統的國畫,也不排斥精準的造型,“真”一直是古人的理想,只是不易達到罷了。從這個意義上,造型能力應當是國畫應當達到的,而不是要排斥的,是否具有造型能力,恰恰是專業性與業余愛好的分水嶺。從意蘊與意境的角度來說,筆墨功夫所體現出的“境界”在當代水墨藝術中要不要去表現,這是個矛盾焦點,吳冠中強調造型能力與畫面效果,所以他認為“筆墨等于零”,這個觀點從爭論的角度來說,實際上犯了大忌,筆墨這種基礎性的技藝,可以超越,但不可以被否定和放棄。從筆墨的角度來說,當代的水墨藝術在墨法上不遜古人,甚至別開生面,當代國畫家為了追求墨色的特殊效果,可以往墨中填加其他物質,這一點無可非議,古人也是填加的,只不過他們可加的東西少。但對于筆法,這恰恰是水墨藝術的弱項。由于國畫的專業化,對造型和繪畫能力的要求提高了,但對書法的要求放松了,甚至可以這樣說,在當代的國畫發展中,書法與國畫分離了,但這也不應當成為否定水墨的理由,因為在宋代之前,國畫和書法本身就是分離的,它們的結合也只是在文人畫這個狹小的領域中。分離意味著繪畫性的強化,國畫首先是“畫”,這種分離,雖然可惜,但結果可喜。
最后,關于意蘊與美感——水墨的特質,在于含蓄而雋永,它有層次,但不結實,它有實在的造型能力,卻又營造出虛幻的效果,輕盈而通透,朦朧而沖淡,虛實相生,言有盡而意無窮,這種美感,不正是中國的山水畫與寫意畫的目的嗎?在下面這張人物畫中,不正是包含了“國畫”這個詞所應具有的美感與意蘊嗎?

姜永安,2013,《顧城》
過去100年關于國畫的所有指責,都在這些作品中被超越了,這當然不是一個人的功勞,而是數代人的努力,也是文化選擇的發展方向所決定的,姜永安們,以及他們的前輩與后賢的努力,使得國畫如鳳凰浴火般重生,雖然沖突和爭議不斷,但筆者相信,這正是中國畫的方向與未來。國畫在百年之中,經歷數次革命,這些創作或許就是革命的成果。
責任編輯:沈潔
*劉旭光,男,1974年生,博士。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上海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執行院長,主要從事藝術學理論與美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