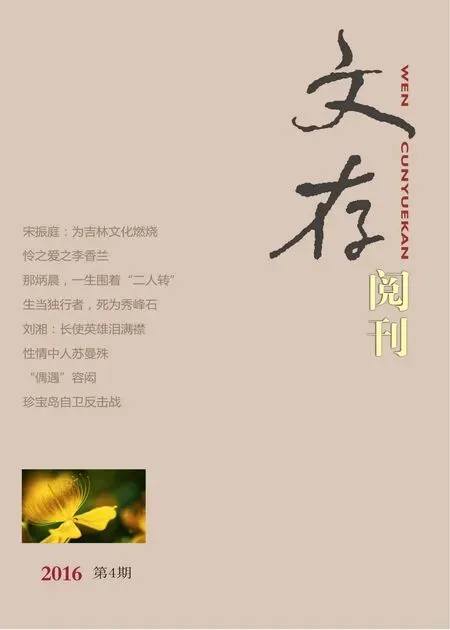宋振庭為吉林文化燃燒
鮑盛華
宋振庭為吉林文化燃燒
鮑盛華

一
當公元2015年秋被稱為“東北最美高鐵”的長吉琿線路開通之后,每天數列火車呼嘯而來,穿過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首府——延吉。這個東北亞的金三角地帶,讓人首先想到的是充滿朝鮮族風情的舞蹈、歌唱、冷面、咸菜,或者是金達萊花漫山開遍、迎風招展,又或者是由于剛剛聽到此地在古時開發之初,因地勢原因,煙霧籠罩,久久不散,故稱為“煙集崗”,后轉音而為延吉的典故,便想象其地煙氣岡岡的樣子。
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的是,接近一百年前的1921年,正是東北初春時節,冬雪尚未完全化盡,還零星地覆蓋著山背面的某段道路,一個提升并厚重了新中國建立后吉林文化起點的人誕生于此。
宋振庭,一個有著文人風骨、士人情懷的高級官員,一個被大師名宿驚為“東北竟有此等人物”的博覽群書式的人杰,一個深邃多思、表達靈動的思想大將,一個頗有個性、激情澎湃的關東漢子,一個重情重義、令人神交久矣的師長、朋友,一個因文氣盛、因傷人而思悔的老人……
如果沒有他,你可能欣賞不到有著鄉土鄉音,藝術表現力、感染力很強,創作了諸多經典曲目的劇種——吉劇;如果沒有他,眾多國寶珍奇可能還在流浪、漂泊,或者跟隨了別的主人,吉林地域文化的高度會因為缺少遠見卓識而受到損傷,吉林省博物館也不會因館藏之豐擁有如今在全國所處前列的地位;如果沒有他,吉林省圖書館就不會那么快地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建成并開館,如今也不會有四十多萬冊(件)古籍在這里安家,歷史的述說會更多地與東北的這一文化邊地擦肩而過;如果沒有他,全國知名大型刊物《社會科學戰線》的創辦就會受到影響,就不一定會因其中許多文章引發廣泛關注;如果沒有他,被稱為“民國四公子”的張伯駒能否改變人生后二十年的經歷,在那個天翻地覆的年代,能否還依然從容、淡定,從事他喜愛的事業,實屬未知……
這一切,從1921年開始。
皮匠出身的父親崇尚讀書,完全靠自學達到看書讀報的能力。識文斷字,讓那個年代的人打開的是另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剛好,他們正逢白話文運動,文字從原來的古文中跳躍著、奔跑著,來到每一個普通人的面前,這已經不再是過去的貴族們專屬的文化世界。中國人因為白話文的普及,接受著最廣泛的啟蒙。童年的宋振庭被父親送去讀書,讀書時稚嫩的童聲是他留給自己的最長久的老家的記憶。然而,日本人的侵略打破了一個孩子平靜的讀書生活。“九一八”事變后,由于父親為抗聯募捐鞋子,被當作反動分子抓起來,欲殺頭示眾。老百姓因其父平時為人為事所感,到日本軍營請愿,才免于一死。從此,全家被驅出延吉,開始了流亡的生活。
然而,無論走到哪里,宋振庭都沒有忘記讀書。1936年夏,他隨其兄流亡到了北平。讀書不輟的念頭讓他到處尋訪,終于就讀于六部口北方中學。正是在這個時候,宋振庭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同年,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年,宋振庭與同學結伴,來到他心目中向往的圣地延安,并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轉年夏天,他獲得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延安馬列學院哲學研究室研究員,從此,他由學生轉變為學人。
1939年,宋振庭被派到抗日前線,先后任華北聯合大學教員、教育科長、哲學教研室主任。哲學,成為他人生的思想主題。十八歲就當了一所大學的教育科長,從學人變成了長官,沒有深厚的學識底蘊是不可想象的。這次人生轉折,與華北聯大校長成仿吾有關,成校長聽說了一個叫宋振庭的人,知識淵博,頗有思想、主張,經過一番考察,點名讓他來到聯大。到聯大后,宋振庭與后來大名鼎鼎的張春橋住在一個房間,此時的張春橋也是聯大的一個科長。
1942年冬,宋振庭到晉察冀邊區曲陽縣委任干事。一年后又到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黨校學習,參加整風、審干。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青春正盛的宋振庭不安分起來,像當年南宋的陸游一般,作學問的同時被舞刀弄劍所吸引,誓要到前線殺敵報國。二十二歲的他,腰上別一支盒子槍,參加抗戰,打游擊。他摸過炮樓,打過偷襲戰,也被追擊,打過突圍戰。一次突圍時跳崖,奇跡般活了下來,在一個山洞里困守多日,組織以為他犧牲了,還給他開過追悼會。
由于文字和文化方面的影響,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他被派回東北,任《東北日報》社編輯、第一版主編。
1951年8月,宋振庭被調往省城出任吉林省政府黨組成員、省政府文化處長。從這之后,宋振庭真正成了一位文化官員,直至1985年去世。這期間,從1952年末至1966 年8月,歷任中共吉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文教部長、宣傳部長、省委常委等職。1977年10月被任命為吉林省革委會副主任、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1979年3月后調任中共中央黨校教育長。1983年10月任中共中央黨校顧問。
二
新中國成立后,宋振庭開啟的不是官員大佬的日子,而是“邁步從頭越”,又開始了讀書學習的工作和生活。新時期“一代文官”的情境與情懷不斷呈現出來。
“凡是人類能知道的我都想知道”,馬克思對自己的女兒所說的這一句話,也與宋振庭的性格完全契合。把這句話作為人生的信條也是宋振庭與馬克思的隔空對話。用“拼命”二字形容宋振庭的讀書狀態一點兒也不為過。除上班處理公務以外,他晚上讀,周末讀,身邊永遠是用書壘砌的書墻。他記憶力好,讀書的速度也快,一本書,幾個小時就能讀完。他涉獵之廣,讓人嘆為觀止,經濟、社會、政治、文學、歷史、哲學、音樂、曲藝、書畫、宗教、考古、中醫、圍棋……沒有他不感興趣的,而對特別偏好的書,則是一遍遍反復翻閱,一本《紅樓夢》讀過多遍。他對自己的興趣做如下評述:“每天早晨打開收音機,沒有一個節目是我不感興趣的。土壤、肥料、沙漠、海洋,祖國各地,世界紀游,我哪一個都愛聽。”“打獵、射擊、騎馬、射箭、劃船,我都要學一下。”
他不視己高,不以官居,低頭向于省吾、羅繼祖、張松如、楊公驥等當時在吉林省工作的著名學者求教,并彼此引為知己。
他可以講瓷。1978年夏天,他在濟南大明湖參觀一次瓷器展覽。在展柜前,他給隨行人員充當講解員,從白瓷講到青瓷、彩瓷,從硬瓷講到軟瓷,從商代講到清代,還詳細講解了宋代的官窯、汝窯、哥窯、定窯。館內講解員聞聲過來討教。
他能說魚。1981年夏天,宋振庭在青島療養,妻子買回一條魚,他從魚的做法說起,一直談到某些傳統飯店的歷史,以及中國的八大菜系,清朝的“滿漢全席”。
他會談佛。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宋振庭因健康原因在北京住院,正好趙樸初也在同一個醫院治療。閑暇無事,宋振庭與趙樸初聊天,談到了佛學,結果滔滔不絕。過后趙樸初與朋友說,真想不到,在老干部中還有對佛學如此深通的人。一位宋振庭身邊學者曾做過這樣的描述:長春護國般若寺里的澍培,是近代佛學界頗具影響的法師,法華宗(又稱天臺宗)的大家,此人在佛學界甚有地位。他對宋振庭,從客客氣氣、敬而遠之,彼此對坐幾個小時喝了幾壺茶而不說一句話,到相互交流、探討、爭論、敞開心扉。1979年,宋振庭調中央黨校工作,行前去向他告別,離情別緒,場面依依。

1980年5月,宋振庭與畫家吳作人(右)在北京。
他懂曲藝。一次,北方昆曲劇院彩排《牡丹亭》,請宋振庭觀摩,結果與演員們交流的時候,他竟能大段大段地背杜麗娘的唱詞,令在場人員十分驚嘆。
他喜歡繪畫。1961年夏天,傅抱石和關山月來吉林寫生。此時的宋振庭是吉林省委宣傳部長,他對兩位藝術家的到來給予了熱情的接待。對于書畫藝術的交流和長談,讓傅抱石把宋振庭驚為天人。宋振庭對兩位藝術家畫作的評價,讓傅抱石抱拳作揖,說,你把我最近的苦惱的問題點出來了,你是我的老師。據說,傅抱石事后對關山月說,想不到東北還有這么一個人,地方官里還有這樣懂藝術的人!
三
籌建省博物館是宋振庭接手的吉林省文化事業前無古人的大事。
雖然長春曾是偽滿洲國的都城,溥儀的宮中確實也珍寶滿屋,但絕大部分文物都隨著這中國最后一個皇帝成為囚徒,被運至蘇聯,又返回遼寧,吉林省并未沾光。溥儀沒有來得及帶走的,以及之前偽皇宮中被偷盜出的,也基本都已經流散民間,下落不明。對于手中沒“貨”的吉林省來說,建設博物館意味著從頭開始。
宋振庭先從資金入手,沒有真金白銀,做不了博物館。他協調財政部門每年必須撥出足夠的專款用于文物收藏。很多文物界的人士一聽說是從吉林來的人,都高看一眼,他們知道,這個省重視,有足夠的財力支持,要拿出好東西來。
為了快速搜集到有價值的文物,宋振庭沒有坐在辦公室批公文、發指示、聽匯報,而是無數次帶著省博物館的業務人員去北京琉璃廠及全國各地鑒選文物。當時,國內文物市場對張大千、溥心畬、王一亭等畫家的作品并不太認,所以這幾個畫家的作品價格相當低廉,少有問津。而且,當時張大千人在臺灣,由于政治的原因,其作品更是沒有人敢過問。宋振庭卻對身邊的人分析說,張大千的藝術在將來會有讓你們想象不到的大價錢。他堅信這些作品將來一定升值,讓博物館抓住時機,大批購進。目的是買斷他們的作品,如果有人想要了解、研究張大千、溥心畬、扇畫藝術、書札,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到吉林省博物館來。結果,大量的張大千、溥心畬作品和歷代名人書畫成扇、書札冊頁來到長春,被收藏、厚待。其中齊白石、張大千、溥心畬等人的作品都在百件以上,省博物館成為大陸收藏張大千、溥心畬繪畫最多的單位,扇面成扇作品達一千多件,名列全國博物館收藏扇畫作品前列。1952年春節,吉林省博物館正式宣告成立,1957年正式向廣大觀眾開放。其剛剛亮相,就引起國內同行的矚目。
這正是踐行了宋振庭給博物館確定的書畫征集、收藏理念:“兼容并蓄、各家備格、成龍配套、自成體系”。在這一理念的引導下,更多的珍貴文物迎風踏浪,向吉林省博物館奔涌而來。一批流落民間的宮廷收藏被征集回來了。1962年征集到金代張瑀的《文姬歸漢圖》。1963年征集到董其昌的青綠山水《晝錦堂圖并書記》。此外,還陸續征集到元朝張渥的《臨李龍眠九歌圖》,特別是北宋蘇軾的《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二賦卷,清朝丁觀鵬摹《張勝溫法界源流圖》等許多書畫名跡。短短幾年,在宋振庭的主持下,省博物館就積累了萬余件書畫精品,它們光彩照人,艷麗無雙,支撐起吉林文化的嶄新高度。
如今,在吉林省博物館有一件金末元初著名畫家何澄所作的《歸莊圖》卷,是何澄傳世作品的孤本,在美術史上占據重要地位,是極為罕見的故宮流散書畫中的珍品,價值連城。這件畫作其實是宋振庭當年與妻子變賣手表等家用在北京買來自己收藏的。北京有關單位聽說了,曾以兩件宋畫為代價,希望換得此畫。但為了豐富吉林省博物館的館藏,宋振庭毫不猶豫地拿出來,獻給了吉林省博物館。
1958年,周恩來總理在一次全國的會議上對來自東北的干部說:各地都有地方戲,你們啥也沒有。
總理的批評使宋振庭觸動很大。他向省委請纓想要開創一個新的地方劇種——吉劇。省委同意后,宋振庭找來編劇、唱腔設計、導演等一大幫人,并把自己的家完全開放,每天晚上在這里吹拉彈唱。在鬧醒了六七十個夜晚之后,他們本著“不離基地、采擷眾華、融合提煉、自成一家”的指導思想,一個新的地方劇種——吉劇披著濃重的鄉音、帶著濃厚的鄉情,走上濃彩的舞臺。《桃李梅》《包公賠情》《燕青賣線》等經典曲目一個接著一個地被創作出來。劇目進京演出,得到周恩來總理的首肯和曹禺等戲劇名家的贊譽。
周總理并不知道,他看到的吉劇《桃李梅》,是宋振庭連續多日反復琢磨后,夜里睡不著覺的時候,躺在床上突發靈感得來的創意。即,用桃花、李花、梅花三種花隱喻三種不同性格的女性的命運,從而編排出的戲。后來,全國竟有十幾個劇種,根據其原有的故事情節,創排過這個劇目。如今,在吉林省吉劇院,《桃李梅》還在被不停地復排,其主角也經過了代際的傳遞。吉林省戲曲劇院的大劇場如今就叫作“桃李梅劇場”。
1985年2月,吉林省圖書館《圖書館學研究》發表了一篇悼念宋振庭的文章,題目是《沉痛悼念本刊顧問宋振庭教授》,文中說,“五十年代,省館在長春籌建之初,宋老即對我館的古籍收藏作過許多指示,‘文革’后,在赴京之前一直敦促我館加速整理線裝書、舊日文書和積壓報刊。多次要求我們盡快搬掉這‘三座大山’以期早日與讀者見面。”“本刊草創之初,曾得到宋老的大力支持,他在接受邀請,擔任本刊顧問,并就本刊的辦刊思想,編輯方針等問題寫信給編輯部,使本刊獲益匪淺。”
像對待省博物館一樣,作為一個愛書如命的書生,宋振庭對省圖的建設關愛有加,使得圖書館圖書收藏經費充裕。老一輩的圖書館人一提起當年,馬上腰身一聳,臉上現出自信和自豪。他們說,那時候到外地去搜集古書,一聽說是吉林省圖書館的,馬上受到不一樣的待遇,因為人家知道,吉林省圖書館有錢,腰桿直溜。讓圖書館人腰桿直溜的宋振庭使吉林省圖書館的藏書在館藏是零的前提下,迅速躥升到全國的前列,如今其古籍圖書已經多達四十萬冊(件)左右。也正是因為經費有保障,南宋刻本《昭明文選》六十卷六十四冊(全)在上世紀收入館藏,已經成為鎮館之寶。
1978年5月,宋振庭覺得應該有一本刊物承載思想解放之花,吉林省應該在文化的更高層面上有所作為,從而不疏于時代,甚至能夠引領時代,深刻的思想是給這個時代最好的禮物。最終,與時任吉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佟冬共同創辦《社會科學戰線》。刊物一經問世,就鮮明地打出“創新”與“學術”的旗幟,集聚國內學術界眾多精英人物,以厚重的篇幅、開放的視野、鮮明的特色,在國內期刊界迅速崛起,成為引導和推動中國學術創新和發展的代表性刊物。
想想那個一窮二白的年代,想想那個甚至還在刀耕火種的歲月,不禁令人感慨,吉林有幸遇見宋振庭,讓其文化的起點和品格有了高層次、大氣魄,有了自身的特色,有了一飛沖天的理想,有了腳踏實地的情懷。
四
1960年前后,有“民國四公子”之稱的張伯駒頭上被戴了一頂帽子:右派。當這個最初僅是無形的、思想和精神層面上的稱呼真正落下來的時候,人們的物質生活、人們的美滿家庭、人們無限憧憬的美好未來,就馬上受到巨大的影響,倉皇起來,迷惑起來,暗淡起來。就算精神上有著強大的支撐點,能夠不俗、不惡、不卑,也一樣不能逃脫明天無望、暫無歸途的窘迫。而那個年代可能最珍貴的是,內心中還能不離不棄自己的一方精神家園,甚至還能帶著這一方精神家園,遠游天際。張伯駒正是心懷這一方精神家園,呼應著宋振庭的召喚。
當時,已經被扣上右派帽子的張伯駒不宜在北京更多逗留,把心情交給遠方的長春可能是最好的選擇。宋振庭給予了最熱烈的回應,發信主動邀請,希望張伯駒能夠攜家眷同來。張伯駒感受到了這個昔日苦寒之地傳遞出來的溫暖,遂乘火車出山海關,直入東北腹地長春。讓張伯駒更感意外的是,這位吉林的文化大員不僅熱情地接待了他,而且執弟子禮,以師視之。不僅如此,經省委同意,宋振庭還安排張伯駒任吉林省博物館第一副館長,并安排其夫人潘素到吉林藝術學院入職。
如此安排,這里面有宋振庭對文化本身的尊重,像張伯駒這樣的鑒藏大家在文化人的眼里,是一等一的寶貝;有宋振庭的濃厚感情和膽識,安排這樣的位置給一個右派,一定暗藏著某種政治的風險;有宋振庭對吉林文化建設的期許和愿望,讓張伯駒就任一個省級博物館的副館長,其實對于張伯駒來說,根本就不算什么,然而對吉林文化的未來卻可能發生重大的推動作用。因此,宋振庭直言不諱:張伯駒要留下,我們底子太薄,文風不盛,和經濟建設不相稱,要有文風,就要有人才,生活上要多照顧,可以給個研究員或副研究員,工薪不要太低。
來到東北的張伯駒當然會給吉林的文化帶來讓人難以想象的絢麗。到省博物館工作后,張伯駒很快組織了一個類似周末沙龍的聚會,來的人都是全國收藏鑒賞界有頭有臉的人物。這讓長春的天空一時間飄浮起文化的五彩祥云。圍繞著文物收藏和文化建設,大家各抒己見,品頭論足。宋振庭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與此同時,宋振庭不失時機地邀請吉林大學于省吾、羅繼祖、裘伯弓、單慶麟等教授以及長春應化所的阮鴻儀等先生,就省博物館的書畫征集、陳列展覽等項工作建言獻策。

宋振庭與潘素等共賞張伯駒作畫
與宋振庭的多次交流、交心,也讓張伯駒從內心深處完完全全地認可了這個新中國并不多見的文官,認可了這個懂自己、懂文化的人。人生得遇知己,難也;人生得遇如此知己,運也!張伯駒很快熱愛上了這里的人,這里的天空,這里的文化事業。在宋振庭印刷好的白紙居多的文化書頁里,張伯駒毫不吝嗇地書寫著屬于自己的篇章。他慷慨地無償捐獻了數十件家藏珍品給省博物館,較有代表性的有元代仇遠的《自書詩》卷、顏輝的《煮茶圖》卷、宋代趙伯嘯的《白云仙喬圖》卷、元代趙子昂的《篆書千字文》卷、明代薛素素《墨蘭圖》軸、唐人寫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唐人楷書冊等等。甚至,他把離京時雖經鄧拓挽留卻無法舍得的《百花圖》也捐獻了出來。《百花圖》是宋代楊婕妤的作品,被認為是現存最早的女畫家之作,價值已經不是金錢所能衡量。及至今天,吉林省博物館的專家仍然自信滿滿,《百花圖》仍是吉林藏畫中最有分量的宋畫。不僅自己捐,張伯駒還動員周末聚會的朋友們捐。據載,僅1963年到1964年9月一年多的時間,吉林省博物館就征集到書畫精品二十多件。
不止對張伯駒,對其他的藝術家,對年輕人,宋振庭都有著春風般的溫暖。吉林省著名畫家許占志回憶說,他年輕的時候,一個偶然的機會,參加了一個畫展,宋振庭看到了他的畫作,立即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然后向有關部門點名,要看許占志當場作畫。幾天后,許占志當著宋振庭的面,潑灑乾坤,宋振庭則看得津津有味。正是宋振庭的慧眼識珠,許占志很快從年輕人中脫穎而出。
原吉林省吉劇團的老同志回憶說,當時為了創排吉劇,一批大學畢業生來到長春工作。宋振庭親自到火車站接他們,然后還把他們領到家里吃飯。
人,其實是文化的全部。宋振庭就像癡迷他的書籍一樣,也對這些文化的建設者們給予了他人生中最多的尊重和熱愛。
五
其實最早他并不叫宋振庭這個名字。他的原名是宋詩達,他還用過星公、史星生、林青等筆名。有這么多的筆名,一個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他一生筆耕不輟。
他被稱為“著名的雜文家”,其雜文被評價為“針砭時弊,嬉笑怒罵,縱橫揮灑,膾炙人口”。且看他給《文史知識》寫的一篇發刊詞中的幾個段落:
記得列寧有一次在波蘭的火車上,和一個波蘭的知識分子對面坐著談話,他問那個波蘭人關于波蘭作家顯克微支的事。但讓列寧吃驚的是,那個波蘭人竟然不知道顯克微支是誰。正像美國人不知道華盛頓、林肯、富蘭克林,英國人不知道莎士比亞,中國人不知道魯迅是誰一樣。列寧對這件事非常吃驚。
在十月革命后,列寧下過這樣的斷語:“在一個文盲眾多的國家里,絕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他在《共青團的任務》等文章中多次說,如果不了解整個歷史的優秀文化成果,侈談什么共產主義文化,那是十足的胡說八道(大意)。
人們也許馬上問我:目前的中國不就是一個文盲眾多的國家么?據各處農村的統計,農村大部地區文盲占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我們不一樣在搞社會主義么?那么列寧這個話是否是普遍真理呢?
我說,正因為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正因為我們吃了偌大的苦頭,才更證明列寧的這句話是真說對了。
你不信么?你認為一個占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文盲國家能搞社會主義么?那么我問你以下這些事情是怎么發生的?
像我們這樣一個有十億人口的大國,竟然有那么好多年,天天批“唯生產力論”,天天在報刊、廣播、講話、開會中說,知識就是“罪惡”,知識就是“私有財產”,知識愈多愈“可惡”,知識分子就是“臭老九”,愈無知識愈好,交白卷的是大英雄,燒書的,打砸搶的,搞流氓活動的是“革命行動”。這一切為什么會發生?
再比如:為什么上幾億人口一下子變成了狂熱的宗教徒:早請示,晚匯報,背語錄,喊“最!最!最!”在那些日子里,我們整個民族一下子就象瘋狂了一般沉浸在造神運動中?
文章邏輯清晰,層層遞進;語言簡潔有力,鏗鏘傳神。多年來,他把自己的思想傳遞到手中變成握筆的力量,共出版《新哲學講話》、《什么是辯證法》、《怎樣自修哲學》、《星公雜文集》、《宋振庭雜文集》等多部作品。

1983年,宋振庭與夫人宮敏章。
“文革”中,宋振庭被下放到農村,別人下放可能成了遭罪,他卻用來進行藝術的追求。由于有了時間,他拿起畫筆,描繪心中的自然情景、思想萬物,其用筆往往豪放大膽,張力四現,用墨更是淋漓酣暢,筆意昂然。后出版《宋振庭畫集》。
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下,宋振庭在一些政治運動中,說了一些過頭話,做過一些過頭的事,錯待過一些人。晚年,他為自己的過失真誠地道歉。在寫給夏衍的信中,他這樣說道:“在長影反右,庭實主其事,整了人,傷了朋友,嗣后歷次運動,傷人更多,實為平生一大憾事。”“對此往事,庭逢人即講,逢文即寫,我整人,人亦整我,結果是整得兩敗俱傷,真是一場慘痛教訓。”寫這封信的時候,宋振庭已經六十三歲。“病廢之余,黃泉在望,惟此一念在懷,吐之而后快,此信上達,庭之心事畢矣。”可見,宋振庭對以往的過失,進行過深刻的反思。宋振庭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是屬于文化的,從一開始就熱烈地燃燒。這種燃燒加重了“煙集崗”的濃度,讓他的老家為他取得的成就驕傲自豪。當小小少年流亡到北京街頭的時候,他的文化屬性與抵御外侮迅速結合,救國圖存成為他人生的主題。然而戰火沒有擋住他思想的光亮,被慧眼識珠者選送到華北聯合大學從事哲學理論研究。在短暫的戰場烽火之后,文字的魅力再一次把他喚回到文化宣傳工作上來。繼而回到他的故鄉,當了一段父母官。最終,新中國建設中文化的力量促使他進入地方官員的高級別層面,并把自己對文化的理解徹底點燃,然后盡情地在文化的大地上放起大火。這種力量,只屬于宋振庭。
像北方大地上一株高大的柳樹,他往往最早聽懂春風的心思,而暗暗釋放出綠意,隨風的搖擺其實是向周圍的萬事萬物揮手示意。他的樹干非常粗壯、堅硬、挺拔,他的絲絳卻柔和、體貼、敏銳。他要告訴你態度,他能聽懂你話語。
他是千年士人藏俠氣,他是一代文官宋振庭。
(作者/《光明日報》吉林記者站站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