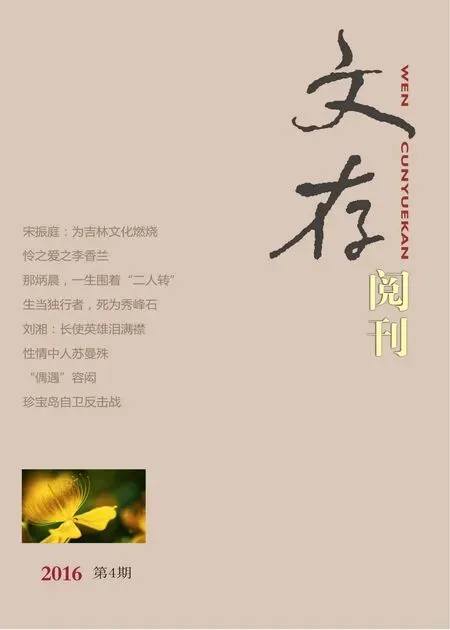孤山林逋活在自己的天地里
老克
孤山林逋活在自己的天地里
老克

杭州西湖孤山林逋草屋及梅妻鶴子雕塑
那天剛到杭州西湖邊,天上就下起了小雪。遠遠看去,湖上游船的人就像張岱《湖心亭看雪》中描寫的:舟中人兩三粒而已。雪花這玩意兒很神奇,天空一旦有雪花飛舞,眼前的西湖,高大的樹木,甚至路邊的草地,仿佛都詩情畫意起來。
早就聽說過“梅妻鶴子”林逋的故事,但來杭州許多次,從來沒有去過放鶴亭和他的墓地。我們對許多事物的認識,總是隨著歲月的沉淀來領悟一些東西,不過選擇一個下雪的日子來孤山尋找他的遺跡,也算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孤山位于西湖的里湖與外湖之間,它其實不高(海拔只有三十八米),卻是湖中最大的天然島嶼。我們在西湖孤山附近先找到梅鶴軒,問了一位賣旅游紀念品的小伙子,林逋墓在哪里?沒想到他一臉茫然。這也難怪,如今的人可能更多關注雷峰塔、白娘子,對林逋這樣一個宋代的隱逸詩人很少去關心。
在旁邊的月波亭,我們見到一位吹葫蘆絲的老者,就冒昧地向他打聽林逋墓,這位面帶笑容的老人有點耳背,聽不清我問什么,但已明白我們在問路,就非常熱情給我們介紹附近的景點,其中就提到放鶴亭——老人告訴我,前面右轉沿著孤山后的山路就可找到。
孤山后山路真的很美,沿著長長的石板路,左邊是大片的草坪和層層疊疊的樹木,右邊是西湖,湖里是大片大片的殘荷,給人以蕭簡枯瘦的美感,畫面背景是遠遠的山巒和保俶塔,更給人宋元古畫的感覺。要是換上我年輕的時候,對眼前的風景肯定會無動于衷,甚至遇到這種下雪天還會唉聲嘆氣地抱怨,如今多了些讀書和生活的閱歷,才會對這種“蕭簡、枯瘦、高古”有了莫名的感傷。
在草坪上,有一座石碑,上面雕刻著一匹瘦馬,讓人聯想起馬致遠的那匹“古道西風瘦馬”,尤其是在風雪之中,讓人會有“瘦馬在走動”的錯覺。在另一處草坪上,一尊魯迅先生的雕像,這是我看到的最為溫柔的魯迅,而不是“橫眉冷對”的魯迅。
沿著孤山山麓往右走,盡頭處忽然開朗,出現在眼前的是兩棵巨大的樟樹,樹后面就是傳說中的放鶴亭。不知為什么,畫面一旦有了古樹做背景,馬上又有了古意森森的感覺。
眼前的放鶴亭最初建于元代,當時是杭州地方官員陳子安為紀念林逋而建。歷史上為什么有許多文人、官員,心甘情愿做林逋的粉絲?恐怕還是與他“性孤高自好,喜恬淡,不趨榮利”有關。記得那天我們在仔細觀看那塊《舞鶴賦》刻石時,旁邊有兩位中年男女正在舞劍,好像為我們的閱讀伴舞。這篇賦是南北朝詩人鮑照所作,明代很牛的書法家董其昌所書,全賦四百六十六字,描繪了鶴的美妙和能歌善舞的才華。
歷史上留下林逋的文字記載少之又少,這肯定與他生前做人有意低調有關,以致讓我寫這篇文章時有點埋怨此公。我只知道他是杭州人,自幼資質聰慧,刻苦好學,通曉經史百家,善于繪畫,長于行草。按理說如此下工夫讀書,藝術上又全面打通的人,本應是求功名的人選。可讓人掉眼鏡的是,此人對求功名一點興趣也沒有。
世界上許多事情不是孤立的,我們現在光知道他在四十歲后隱居西湖孤山二十年,但對他之前曾經放游江湖二十年的經歷,卻了解非常少。這些天讀了他的一些詩詞,才知道他的人生大致走向。
林逋年輕時也是自結詩社,廣交文友,用現在的話就是典型的文學青年。他除了主要在歷陽、曹州活動,還游歷過江南許多地方,比如蕪湖、金陵、姑蘇等地,他的足跡涉及山東、安徽、江西、江蘇、浙江。
他年輕時遠游,也和許多讀書人一樣,希望為世所用,有所作為。但出游的路并不平坦,理想也無處實現,加上他自己也有些俠氣和狂態,難免有些磕磕碰碰。其實交朋友也是對等的,林逋當時不出名,交往的多半不是出名的人,也許這種長年累月的遠游讓他疲倦,也許他經過讀書修煉后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詩人慢慢地有了歸隱之心。
四十歲那年,林逋就在孤山放鶴亭附近弄間草屋,編竹為籬,過上了隱居的生活。他特別喜歡梅花,在山麓上屋前屋后種滿了梅花,據說有三百六十株。不過,林逋種梅花也不完全是風雅,他的生活來源主要是靠賣掉梅子,種點菜。雖然生活簡樸,但畢竟是他想要的生活。每逢梅花開放的季節,林逋就整日與花為伍,飲酒作詩,欣賞梅花的不同姿態,活在屬于自己的天地里。我相信只有真正用生命碰撞的人,才會出真正的好作品。就像林逋那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的詠梅名句,傳神地寫出了梅花清幽香逸的姿態,至今寫梅花好像還沒有人超過他的意境。

杭州西湖孤山放鶴亭
我曾陪外地朋友在夜晚去過南京東郊的梅花谷,那真是一種奇妙的感受,走在梅樹中間,雖然不同品種的梅花在夜色里看不清楚,但卻讓你真真切切感到香氣一陣陣襲來——真是偷襲啊,你不注意時它就來撩你,你刻意去嗅它又調皮地躲你,就像一個懷春的女子跟你躲貓貓。
林逋歸隱后,對許多事情就完全想明白了,如果說當年他在外游歷時還刻意結交當地文化名流,甚至見不到還有點糾結,而現在就是徹底放下了,他真的是以隱居為樂,把孤山當成自己人生的桃花源。
他一生喜歡養鶴,也許鶴的潔身自好,就是他自己的性格化身。張岱為我們描繪了這樣的畫面:林逋經常駕一小船,遍游西湖的寺廟,與高僧詩友往來。若是有訪客來山中茅屋,童子就會把鶴放飛天空,他遠遠看見就會駕小船返回。因為他一生不娶不仕,狂喜歡梅與鶴,這就是“梅妻鶴子”的由來。
林逋多才多藝,喜好讀書寫字,琴棋書畫無所不能,尤其是書法和繪畫都達到很高的境界,他自己也承認:“逋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和著棋。”讀書人不能擔糞可能是真,不能著棋就是謙虛了。
林逋最為人稱道的還是詩歌,他的詩作留存不多,但每篇總是很獨特,眼光、境界都與別人不一樣。難怪連大家蘇東坡也毫不吝嗇對他的詩、書及人品的贊美:“平生高節已難續,將死微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書,更肯悲吟白頭曲。”
有那么多的文人對他贊美,很大程度上他是玩真的,不玩虛的。因為歷史上借歸隱之名,沽名釣譽的人太多,而像他這樣隱居山里二十年,甘于清貧,身無長物,不入城門半步的人還真不多。不過,我這樣寫,大家也不要把林逋想象成是一根筋的人,在有些問題上他也是很通達的,比如他自己不愿做官,但并不反對自己侄兒做官,他自己歸隱山林,也不是完全閉門不見任何人。他歸隱前的詩就在民間很有名氣,只是沒有被官方認可,歸隱后經皇帝賜號,來訪的官員和文人更是很多,當然,他也是有選擇的。
林逋的思想挺復雜,主流是儒家思想,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也占很大比重,用現在的話就是“儒釋道”的全面打通。他對禪學也有研究,交往的文友也沒有門戶之見,官員、文人、和尚、道士、農夫等,善于學習,化為我用才是真學問。
林逋生前什么都不要,不仕不娶,連寫好的詩都隨手扔掉,現在僅存的詩作也是別人偷偷記下來的。沒想到壓根兒不想成名的人,死后卻有那么多人記住他。盡管如此,還是有人攻擊他是另一種形式的沽名釣譽,這只能歸結是醬缸文化式的嫉妒。試想一下,一個人連自己用心血創作的詩作都不愿意留下來,又靠什么來“沽名釣譽”?
不過,近些年又冒出“林逋其實是有妻子和小孩”的結論,其源頭是有個叫林洪的人,此人在《山家清供》中稱“和靖先生”為“令翁”(林逋生活在北宋,林洪生活在南宋末年,兩人相差二百多年)。后來這個冒牌兒子林洪,又在他的另一部筆記《山家清事·種梅養鶴圖說》中,搖身一變,成了林逋的七世孫。一會兒是小二百歲的兒子,一會又是相差七世的孫子,可見無論哪個朝代,總會有這樣恬不知恥的小丑。
離開放鶴亭沿著山坡往上走,就到了林逋的墓地。說實話,在爬那個臺階時,我真有“近墓情更怯”的感覺。這是一個不大的院子,里面長滿樹木,靠墻邊的臘梅樹已開出梅花。不知為什么,我去過許多墓地,而林逋的墓地給人的感覺非常肅穆、清秀,讓人很是親切。
林逋清貧一生,四壁蕭然。張岱在《西湖夢尋》中說,南宋滅亡后,有盜墓賊挖開林逋的墳墓,只找到一個端硯和一支玉簪。相傳林逋死后,山坡上他親手種植的梅樹,居然漫山遍野又為他重新綻放了一次。花若有情,人何以堪?不過林逋死后,最可憐的是他生前馴養的鶴,不吃不喝,最后竟在墓前哀鳴而死。后人將它葬于主人的墓側,取名為“鶴冢”。
那天,我們很想去找到那個“鶴冢”,無奈當時天空的雪越下越大,我們只能把那本寫有林逋的書放在墓碑前,鞠躬祭拜了一下。那天,我們在林逋墓前坐了好久,不為別的,就是想多陪他一會兒。真的,當時看著天空漫天飛舞的雪花,真是有電影大片的感覺。當時只覺得鼻子酸酸的,內心有流淚的沖動:我們在風雪天追隨到這里,不為別的,就是因為對死者有那么點惺惺相惜,就是想表達對古人隱逸精神的敬意!
后來,我們還爬到山上,居高臨下看到林逋墓地,它正在靜靜地面對雪花飛舞的西湖,山上的臘梅已經含苞待放,湖上是一片殘荷迷蒙。據說,也有人曾買了鶴到這里放生,就是想讓它來陪陪孤獨寂寞的林逋,那天我們雖然沒有看到鶴的蹤影,但在內心仿佛聽到天空中鶴的聲聲哀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