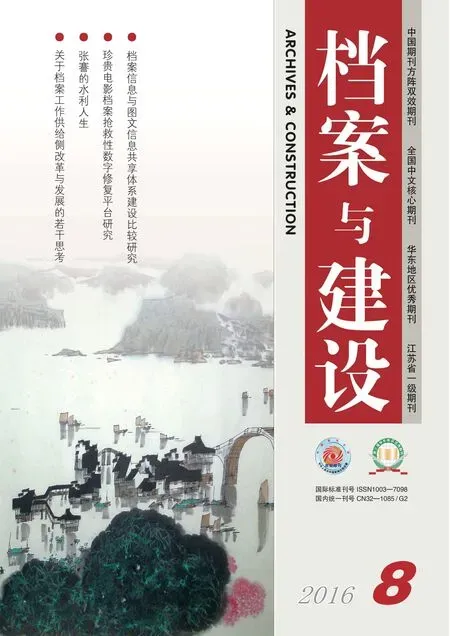護送阿英一行由葉旅到粟師
范學貴(上海市徐匯區吳中東路500弄83號104室,上海,200235)
護送阿英一行由葉旅到粟師
范學貴
(上海市徐匯區吳中東路500弄83號104室,上海,200235)

1946年的阿英
張胤,新四軍老戰士張巖之子,北京退休干部。他手頭正在忙著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在家整理父親身前留下的遺物,重溫老爺子往日戰斗歷程。我們之間常常通過微信聊天,有時聊得很晚,研究討論新四軍抗日的故事。
張巖,1920年4月26日生,江蘇省金壇人。1938年6月入伍,11月參加中國共產黨。1939年1月1日從皖南新四軍軍部教導隊學習結業后回新四軍一支隊,歷任指導員、教導員、團政治處主任,南京市公安學校教育長,上海市公安學校教育長,在華東政法學院負責教務。1991年司法部批準離休。獲司法部頒發一級金星榮譽勛章。2008年因病去世。
6月9日,微信聊天中,張胤發來《閑話當年送阿英》文稿,計10頁。這是他父親張巖生前寫的一篇回憶錄,寫于阿英去世4年之后的1981年。張巖在11月17日從《報刊文摘》上看到《著名文學家阿英遺產訴訟案始末》,聯想到1942年6月奉新四軍一旅旅長葉飛之命,將阿英等一批由上海撤向蘇北的文化人,從如西送到呂四粟裕所在一師師部的全過程。閱后,筆者就抑制不住內心的沖動。
抗日戰爭期間,關于上海文化人遷往香港、武漢、延安,保留下不少文字、影像,記錄真實而詳盡。而關于上海文化人遷往蘇北抗日根據地,卻鮮為人知。
筆者立即著手查閱,方知上海文化人遷往香港及內地有兩次。一次是1937年底1938年初,因日本入侵,上海文化人大批遷往香港,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第二次是堅守上海“孤島”(租界)進行抗日救亡活動的文化人,于1941年12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有組織、有計劃地轉移,有的去大后方,有的去新四軍蘇北抗日根據地。
1941.12.,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占領上海租界。中共組織決定,對在上海孤島堅持斗爭的一批文化人必須加以保護,迅速轉移。阿英在上海印刷書籍,宣傳八路軍、新四軍抗日的“風雨書屋”遭到查封,人員被逮捕,阿英本人受到通緝。黨通知其火速撤離。阿英于1941年冬,攜夫人希嫄(林莉)和子女錢毅、錢瓔乘船離開上海,動身前往蘇北抗日根據地。一路之上,穿越敵占區,迂回曲折,暗夜潛行,諸凡海陸河川,行程半年多才到達新四軍軍部。
作家、文學評論家阿英即錢杏村(邨),原名錢德富,筆名有魏如晦、錢德賦、錢兼吾、張若英、錢宗杏、阮無名、鷹隼等。他1900年2月6日出生于安徽蕪湖。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6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27年大革命失敗,逃亡武漢,同年8月到上海,與蔣光慈發起組織“太陽社”,編輯《太陽月刊》《海風周報》等。1930年任“左聯”常委、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常委兼宣傳部長。1933年任上海地下黨電影領導小組成員。抗戰期間,從事文藝救亡活動,任《救亡日報》編委、《文獻》雜志主編。到蘇北后,參加新四軍,從事領導革命文藝工作、宣傳工作和統戰工作。建國后任天津市文化局長、華北文聯主席、全國文聯副秘書長等職。他著作豐饒,涉獵面廣,小說、散文、戲劇、翻譯俄文高爾基作品。主要從事文學史、文學評論撰寫。其中出版成書的有70余種。1977年6月13日因病辭世。
組織上把文化界這樣重量級的人物交給張巖護送,無疑是對他的信任、重托。張巖在留下的文稿字里行間,都顯出認真、負責、細心、踏實和干練。
張巖在文中寫道:“初夏之夜,在蘇中平原上,由如(皋)西到黃海之濱的海門呂四一線上,一支奇特的隊伍在迤邐前進著。這支隊伍,不到兩百人,先頭是武裝部隊,武裝部隊的后面是幾十名背著背包跨包的徒手軍人,再后面是幾位穿長衫便服的男子,男子的后面是好幾部獨輪小車,……而是載的女性嬌娃和個別兒童。在獨輪車后面是事務長炊事班,后面是武裝后衛。”阿英當時筆名魏如晦,他及其家人和他從上海帶來的幾位男女文化人,在這次護送中代號為“魏班”。
阿英著有《敵后日記》,1980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想這本書中定會查到與護送相關的文字,可以求證。去上海圖書館查閱,總算查到了。
1980年9月30日,陽翰笙為阿英《敵后日記》作序中說,這部日記是阿英從1941年離開“孤島”上海進入蘇中抗日民主根據地開始記述,不僅僅記錄了阿英的戰斗生活,而且也記錄了新四軍同蘇中人民與日本侵略者所進行的偉大斗爭,可以說是那個年代、那個地區軍民英勇斗爭的側記。筆者尋覓得與護送相關聯的內容在日記第一卷,日期為1942年5月31日起,至6月12日止(全卷于7月16日結束)。這卷名“廟灣紀程”。阿英在此卷小序交代:余自5月31日,離泰州前來軍部。于地區則經泰興、如西、南通、東臺、興化、鹽城、建陽始抵阜寧,凡經九縣,……于部隊,則師部、一旅、二旅、三旅、五團、六團、二旅特務營、供給部,凡八個單位。因日記在9月21日在阜寧整理,明代阜寧稱謂廟灣,為防倭重鎮,所以定此卷名“廟灣紀程”。
《敵后日記》載:阿英一行從泰州出發,一路找鄉保長、找民伕帶路、作向導。敵偽電光四射,村莊狗吠不止,天上霏雨陣陣,穿越偽軍經常活動地帶界溝,一路情況緊張,始終持槍在手,隨時準備戰斗。在東姚家埭遇二團偵察員,獲(旅)司令部、政治部就在大洋北石莊,見新四軍第一師副師長兼第一旅旅長和政委葉飛,葉告之軍部迭有電至催行,當商定暫在如西埋伏,俟上海人(40多人)至即起程。據可靠情報,泰州、揚州開來敵千人,與山東敵偽夾擊“掃蕩”蘇中。次日,旅部疏散,準備戰斗,派一排人送至師部。又獲悉,敵即“掃蕩”,魏先生(阿英)今晚和教導隊(張巖所在部隊)隊員同行,葉飛給函沿途各站招待。當晚行30里,仍在如西,就寢時,已近晨四時矣。
張巖所說大獨輪車現在已經絕跡。大、小獨輪車共同點:①選料全部用堅硬的雜樹。②裝配不用一鉚一釘,全用隼頭套裝。③外形都有獨輪,都有車脊。④推車人的肩上,都拉開一根牽繩,捆綁在左右車臂上,手扶著左右兩根車臂推車,車輪滾動,車體向前推進。不同點:①大車車輪直徑約1米,小車直徑約60厘米。②大車前后都伸出左右兩臂,小車只有體后左右兩臂。大車體前拉車人主要起方向盤作用,體后推車人起舵手作用。③大車必須在車脊兩邊柵欄平面上坐人或裝物,可以把物裝得擋住體后推車人視線。小車車脊兩邊可一邊或兩邊坐人,或一邊坐人、裝物,一邊空著,推車人前面重載量大,可配一名輔助背牽工,輕載時單獨一人推車就行。④大車體積約小車的三至四倍,載重量大于五六倍。⑤大車為防備車輪落入缺口過不去,特地在車把手前裝置一只小輪,萬一落入缺口時,前后兩個人四手往上一提,可借助小輪滾動,帶動大輪爬上路平面繼續前進。小車落入缺口只需輔助工回過頭來拉一把就可以了,筆者也見到裝置小輪的。張巖說,據說這就是當年諸葛亮的所謂“木牛流馬”之類。
張巖寫道:“今天從地圖上看,從如西到呂四,不過兩百幾十里的路程,乘汽車只要幾個小時就可到達。可是當年這支隊伍,卻是擔驚受險走了半個多月,才安然到達。”一支以文化人為核心的隊伍,在敵人據點林立的夾縫中穿插,竟毫發無損地完成任務。
滴水見世界。通過張巖回憶護送魏班,可以觀察理解阿英進入蘇北抗日根據地的艱難。
一九四二年的初夏,我奉旅首長之命,去鹽城軍部上干隊學習,旅首長要我順便完成一項任務,一是帶四十幾位男女連級干部到呂四一師師部(粟裕師);一是由三軍分區(通、如、靖、泰)派一副營長(楊文斌同志)率一個連歸我指揮,護送魏如暉先生及其家人和由其從上海帶來的幾位男女文化人到師部。我因是學習,我隨身的柏殼槍交給了旅部,旅部給了我一份由如西到呂四的一線軍用地圖,給了我一名偵察員。我的名義是干部隊隊長,指定干部隊中一位女同志趙柏英為支部書記、住隊部。旅發給伙食費,干部隊組成經委會,伙食自理(“魏班”的伙食我想不起是怎樣安排照顧的了)。就這樣,我們就由如西出發了。

張巖
一九四二年的初夏,正處在日本鬼子大掃蕩、汪精衛搞清鄉的前夕,敵人的重點是在四軍分區我一師師部的所在地。至于敵人的小的掃蕩行動,則是敵后各個我區經常遇到的事。在三軍分區,對民情、地理我都熟悉,沒有軍用地圖也沒關系;一進入如東四軍分區轄境,我各方面生疏,軍用地圖又僅只有一條路線上的幾份,在敵人據點林立中,我們這隊伍又絕不能遇上戰斗,只能邊摸清敵情邊前進,這就苦壞了我今天要叫他大哥的忠心耿耿的偵察員同志;每到一宿營地,他不能休息,他要繼向前面去偵察敵情回來報告后才能休息一下。因為是在敵人據點空隙間穿插前進,途中還要過敵人的幾條封鎖線,我不能有絲毫莽撞盲動。加之“魏班”是不能像我們一樣龍騰虎躍來個常行軍一夜六十里,加個急翻一番一百二十里的。如果那樣,他們不用講一個夜晚,就是兩三個小時,男的起馬大部分垮下,三五天不能走動,女的雖坐在小車上(也有不坐車的女同志),車行也不可能過速,何況還有孩童,所以敵情、我情加在一道,一夜只能走三十多里。一到宿營地,布崗派哨是楊文斌同志,分配房子是趙柏英同志,我是立即打開地圖,考慮前進道路,交給偵察員同志任務。我感頭痛的是,要找好幾部小車。一車兩人,后推前背,在生疏地區,這是多煩難啊。車人找齊后,第二天天晚出發,為了速度,不能雙坐,一車只能坐一位女性。還要關照對車軸部位要勤澆水,不使出聲響。有一次,我費盡了力也沒能找齊車工,少一個背纖的。偏偏坐上這部車的是一位生得嬌弱的名叫蘇英的女孩兒家。車推動時,她發現她坐的車只有后面推車人,車前面卻少一個背纖人,急得她直叫:“我的車沒有背纖的!我的車沒有背纖的!我當時內心是不高興的,我想,我一個營干,自己背著背包跨包地圖行軍,身后沒一個隨員可支配,到達宿營地,我還要忙這忙那,費盡了力,也沒能找足民工,你卻還要直叫喚,我不睬你。今天想來,這絕不能怪她,一個上海剛去的女孩兒家,又生得嬌弱,她會知道,沒背纖的,她的車速就不如其他車輛,這是危險的。好得行進速度不快。
到了北新橋,了解到環境平靜,決定休息一天。北新橋是一個小鄉鎮,一條東西街,街中段有幾家店。魏先生住在街中間坐北朝南一家米店里。我住在他東隔壁。楊文斌同志住在米店正對面坐南朝北的小酒店里。酒店的曲尺柜臺在西邊,橫頭朝街,豎柜朝店堂。清晨,我去看魏先生,魏先生雖途中痕累卻起得很早,一張小長桌放在店堂中間,桌上放有文房四寶。魏先生坐在一張長條凳上坐北面南在寫毛筆字。魏先生字寫得很大,比大姆指面還大得多。魏先生問我多少歲了。我講二十二歲。魏先生講我很干練,這樣的年紀能負這樣的責任,很有才干。魏的妻子在一旁也幫腔講我能干。我講我那里有什么才干,不過勉力盡責。我用眼睛看著默立在魏身后比我小四歲的他的大兒子。我講大公子在魏的培養下才是有才干的人呢。魏謙遜地講,他很老實,那里比得上你。——解放后,我偶爾看到了阿英前輩悼錢毅同志的文章,我知道了錢毅同志已成為我軍前線記者,犧牲了,留有詩文集。我一面內心哀傷錢毅同志,另一面也自慚一無所長,終不成材。
在北新橋休息的這一天,除大家稍事整理外,還改善了一下伙食,吃了一塊錢一只大碗口大的海里捉來的大螃蟹。
在阿英日記中記載著這天是6月7日,阿英久不理發,往修發鋪剪發。午飯后,張(巖)隊長約去浴室洗浴。
張巖回憶錄繼續寫道:
第二天,決定早飯后白天行軍。早飯后,突然“砰”一聲槍響,我急忙出去,看到魏先生住店的街沿下倒著一個臂挎竹籃的中年農民,已經死去。是楊文斌同志的小通訊員在對面柜臺上擦拭步槍,槍膛里有子彈走了火;此時魏先生正從樓上往下走,走到樓梯中間,槍口如高了一點,子彈就會打到魏先生的身上。我對楊文斌同志講,把通訊員立即捆起來。一打聽,這里是南通縣轄,縣政府離這里不遠。我立即派偵察員同志找縣政府報告情況(我記得魏班也有同志一道去的)。不多久,縣長梁靈光首長親自來了。我把我們的任務向梁縣長作了回報,在途中出了這樣的人命。我又把魏先生向梁縣長作了介紹。梁縣長一口就講,你們還是繼續走路,這事由他解決。我當然如獲大赦,感激不盡。我們出發了,沒想到楊文斌到把通訊員放開了,連到路上再放開也沒等得及。這也難怪,他必須有通訊員通訊。
只一天白天行軍,又進入敵情緊張環境,仍只好夜間行進,走呀走,走到我所帶地圖的外面去了。這可更傷腦筋了。完全成了聾子、瞎子,也就更感負擔重。這時干部隊里有同志卻鬧起伙食來了。我真焦急。是啊,這樣地行進,怎談得上改善伙食呢。我寫了一信,向三旅求援(陶勇旅),派偵察員出去找三旅部隊。好了,偵察員回來報告,三旅旅部在六甲鎮。在接近六甲鎮的那天白天行進在南北向的長堤上,我才有心境欣賞了一下高堤兩側的啟海風光。
到了六甲鎮,梅嘉生參謀長接待了我們,把我們當友鄰客待,并備了飯菜特請魏如暉先生,我也叨光作了陪。晚上又邀我們全部人員參加他們打下三陽鎮、繳到鬼子平射炮的祝捷大會。
到了六甲鎮,阿英日記上寫著:
六月九日,星期二,晴。
昨夜偵察員自六甲鎮回,知三旅實未移動。
故晨五時起床后,即向六甲進發,凡十二里,到達。
到鎮二里前,即見軍用電桿。可見此地情況,較之如西,實為安定。惟中有斷者,不知何故。
一里半,入哨線。
……
返寓所,三旅劉光勝旅長、梅嘉生參謀長來訪。堅約至旅部,乃隨之去。旅部在吾寓門面河對岸,一大典當中,渡一高橋即達。
晤吉洛(姬鵬飛)政治部主任,談連隊文化教育問題甚久。
得知最近七團在斜橋與鬼子戰,得一大勝利,鬼子四十余人全部被殲滅,便遺體亦無法搶回。日兵視搶奪遺體為重要事件,今不得奪回,在蘇中區實為初次。又奪得新式平射炮一尊,亦為四軍之新紀錄。故今晚在此地舉行晚會。師服務團并全部開來,參加演劇。
吉主任等留住此一日,晚上參與大會,允之。
……
十二時,旅部約午飯,與希嫄及毅、瓔兩兒去。
歸后小眠,夢未熟,張如復引師服務團領隊沈亞威及兩組長來見,談師旅兩服務團諸多問題,久久始去。
……
六時,祝捷大會開會。余到后,始知今晚開會性質,除祝捷外,又增入歡迎余之意義。
到會者,凡干部、士兵、民眾,共約二千余人。
大會堅約余講演,不得已,只得對此戰役,加以歷史意義之評判,并申說建立蘇中區文化新運動之必要。劉、梅、吉亦均有講演。
九時,會完,由劉旅長對此役英勇戰士,予以獎品。并以此役勝利品二事,贈予紀念。其一,為筷篋,系日本天皇贈予有功戰士者。篋類紅木制,抽蓋,內儲烏木筷一雙。抽板刻“支那戰事紀念”六楷書,綠粉涂色。反面得者自刻其姓名,大約系班排長之類。其二,為一鋁制大肥皂篋。
會議進行中,民眾鳴鞭鼓樂,結隊送紀念旗及慰勞品至,情形甚是熱鬧,殊令人興奮。
旋為歌詠,游藝節目,余因未食晚飯,遂先歸。
飯后與毅兒同去觀劇。
旋返寓所就寢,蚊蟲甚擾人。
張巖回憶錄后面寫道:
我們安然到達師部,我向鐘期光主任回報干部隊伙食有結余,繳公。鐘主任叫買東西分給大家。由趙柏英同志負責買了毛巾等每人一份。楊文斌同志帶著他部隊回三軍分區。楊文斌同志,外省人,年齡同我相仿,有上下也差不了多少;長得富厚,性情也溫和厚道,一路上也虧他配合得很好。至于我,未能去軍部,因為鬼子的大掃蕩已經開始了,去軍部的路已經不通了。
10日,阿英日記上寫著步行12里到達呂四鎮,街市十字形,商業繁榮又較六甲鎮為甚。午后,接師部關系,再行12里到達三甲鎮,師部即駐此。小休時許,鐘主任期光來,引至一旅店下榻。
11日,阿英到師部拜訪夏征農秘書。請夏陪同去拜訪粟裕師長。粟師長備飯宴請。午后獲悉蘇英上海家里不佳,蘇英偕弟天澤暫回。晚飯后,夏征農說,四分區“掃蕩”即將開始,各據點鬼子集結待發。粟師長請阿英決定。為免遭意外,阿英決定不宜久留,明晨出發。因此,阿英連夜寫三封信。一封介紹天澤、高洋、蘇英至鐘主任處,解決他們返滬問題,并領取路費;一封寫給葉副師長,交護送隊楊(文斌)副營,托其帶回如西;一封寫給廷驤、劉瓊,交天澤帶回上海。
張巖奉一旅(葉飛旅)首長之命,護送“魏班”到一師(粟裕師)的任務,連頭帶尾耗時13天,順利完成了。張巖在40年之后寫的回憶錄仍然十分清晰。他在文稿結束時,還留下一段無限深情的內心獨白:
……錢毅同志,早已戰場犧牲。阿英前輩逝世了,林莉也逝世了,阿英前輩的遺屬,卻相互訴訟了四年之久,曲折已有公論,作為故人,怎不哀傷故人。
阿英與張巖、楊文斌兩同志在一師告別后,他和家人、戰友從呂四出發,冒著艱險日夜兼程,風雨晦暝,下入黃海,搏擊波濤,再入江河港汊,于7月14日到達阜寧,下榻侉周政治部招待所,在戰友亞農、楊帆陪同下,前往陳毅代軍長處報到。在亭子港,剛落成尚不過一周的兩間茅草房子內,見到陳毅及夫人張茜,只見窗明幾凈,長棹滿陳書籍,內心贊賞“真儒將也”!
陳毅見親自點名的阿英到來,設晚宴,夫人張茜作陪。劉少奇去了山東未能見到。席間談興正濃,陳毅說,十多年前就讀過阿英的文章,表示要再集中更多一些文化人,重整軍區文化的決心。
陳毅憑著睿智目光、戰略智慧,通過各種渠道,在蘇北集中了大批來自上海、香港、重慶、桂林的專家學者。經濟學家薛暮橋、孫冶方,國際問題專家錢俊瑞,作家貝葉、黃源,教育家白桃,醫學專家沈其震,自然科學家孫克定,名記者范長江,作曲家賀綠汀、孟波、何士德,畫家胡考……陳毅為他們設置文化村,建立了文化工作委員會,創辦報紙、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