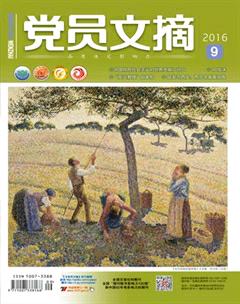“炭火教授”趙家和
鄧暉+周華+李曉
編者按:
這是一次等待了四年的采訪。
2012年,記者偶然得知,“一位清華大學(xué)退休老教授”傾畢生積蓄1500余萬(wàn)元捐助西部貧困孩子,即使在他身患重病期間,為了省錢也要堅(jiān)持吃便宜藥。
他是誰(shuí)?為什么這么做?職業(yè)敏感激發(fā)起記者“追”下去的沖動(dòng)。可幾次溝通,清華校方均因尊重老教授生前“不要張揚(yáng)”的遺愿而婉拒了記者。
功夫不負(fù)苦心人。四年,記者沒有放下寫這位老教授的執(zhí)念,老教授的“接棒者”也覺得,應(yīng)該把他的故事講給更多的人。
趙家和,清華大學(xué)經(jīng)濟(jì)管理學(xué)院教授。今年,是這位老教授,這位平凡的共產(chǎn)黨員捐資助學(xué)十周年,讓我們一起認(rèn)識(shí)他,記住他。
一縷暖陽(yáng)照在臉上,趙家和享受了一個(gè)“最幸福”的下午。
窗外,綠意蔥蘢,清風(fēng)微拂,小鳥“撲棱棱”飛過——這是他出生、求學(xué)、執(zhí)教,依偎了78載的清華園。
淡淡的笑意,在寫滿皺紋的清瘦面龐上化開。“推我出去看看。”趙家和輕聲對(duì)護(hù)工說。癌細(xì)胞早已轉(zhuǎn)移到了腦部,可這位一輩子為人師表的教授,對(duì)待身邊的每個(gè)人,依然端方、謙和。
幾個(gè)月后,他走了。什么都沒留下,就連最后飽受病痛折磨的身體也被捐獻(xiàn)了。那是2012年7月22日。
又一個(gè)月后,蘭州。一路夜車,一群高中生奔波而至。第一次見到這位在“最要?jiǎng)艜r(shí)拉了自己一把”的“趙爺爺”,他已定格在追思會(huì)上的遺像里。
很長(zhǎng)時(shí)間,“一位清華退休老教授”是趙家和的代稱。從2006年開始,這個(gè)一直在教學(xué)生追求“邊際效用最大化”的金融學(xué)教授,默默做了一筆大“投資”:傾畢生投資所得1500余萬(wàn)元資助西部貧困高中生,卻決不允許泄露半點(diǎn)兒他的個(gè)人信息。
不輕易折斷、熱值高、雜質(zhì)低,是人們判斷一塊好木炭的標(biāo)準(zhǔn)。而趙家和,這位有著51年黨齡的平凡共產(chǎn)黨員,就這樣做了一輩子“雪中炭火”。
清華園外,一套十幾年未曾變樣的住所,是趙家和的家。房間里,最值錢的物件——那臺(tái)幾年前學(xué)生送來的液晶電視,已然顯得笨拙。
滿頭白發(fā)的吳嘉真坐在那把老舊的轉(zhuǎn)椅里,安詳而沉靜。微風(fēng)不時(shí)將紗簾撩起,記憶中的影像一個(gè)個(gè)閃回,但幾乎有關(guān)丈夫趙家和的一切,都離不開教書、講課、討論問題,離不開學(xué)生……
趙家和當(dāng)了一輩子老師。可別人教書,是學(xué)一門、教一門;他一教,就跨了工、理、文三個(gè)學(xué)科。
1955年,獲得清華大學(xué)第一屆“優(yōu)良畢業(yè)生”獎(jiǎng)?wù)拢瑹o(wú)線電系畢業(yè)的趙家和留校任教。起初,他從事本學(xué)科教學(xué);1977年,籌建電化教育中心;1979年,到科研處搞管理;1985年,年過半百的他再次“轉(zhuǎn)行”,籌建改革開放后清華大學(xué)第一個(gè)文科學(xué)院——經(jīng)濟(jì)管理學(xué)院。
三次調(diào)動(dòng),都是因?yàn)閷W(xué)校籌建新專業(yè)或新機(jī)構(gòu),需要去開墾拓荒。但,每次轉(zhuǎn)行談何容易,干不好,還丟了老本行,豈不得不償失?
“趙老師有過猶豫嗎?”吳嘉真慢慢搖頭,“沒覺得”。
“干一行、愛一行、精一行”,很多人這樣概括趙家和,而在“行勝于言”的清華園里,平凡的趙老師,卻有著令人佩服的不平凡。
“開會(huì),懂就說一二三,不明白就直截了當(dāng)問。”85歲的邵斌是和趙家和一起開創(chuàng)經(jīng)管學(xué)院的“老戰(zhàn)友”。他眼中的趙家和“從沒半句廢話,卻總能說到點(diǎn)子上”。在那個(gè)“兩手空空”的年代,全院只有一個(gè)系,院辦公室四張辦公桌,這邊坐兩位副院長(zhǎng),那邊坐書記和副書記,一個(gè)個(gè)與中國(guó)經(jīng)管教育息息相關(guān)的決策就在這狹小空間里產(chǎn)生,而其中不少“好主意”都是趙家和提出來的:他主張加強(qiáng)金融專業(yè),為國(guó)家對(duì)外開放輸送人才;他建議多開些公司財(cái)務(wù)類課程,這是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條件下急需的;金融系的整個(gè)教學(xué)大綱,具體到上什么課、講什么、誰(shuí)來講都是由他主筆起草的——此后的事實(shí)證明,他這些“急國(guó)家所急”的判斷是正確的。
趙家和在名利面前常常“畏縮”,連辦公室都給自己選了間“暗房”,卻對(duì)分不清“分內(nèi)”還是“分外”的工作兢兢業(yè)業(yè)、無(wú)怨無(wú)悔。
“以他的聰明,留在無(wú)線電系,奔個(gè)院士不是沒可能。可讓轉(zhuǎn)他就轉(zhuǎn),一點(diǎn)折扣都不打。”邵斌感慨,這樣的人太難得。“他就像炭火一樣,在每一個(gè)需要的地方燃燒,恪盡職守,無(wú)聲無(wú)息”。
1998年,趙家和退休了。他去了美國(guó),應(yīng)邀擔(dān)任德克薩斯州立大學(xué)客座教授,講授中國(guó)經(jīng)濟(jì)改革實(shí)踐。大家以為,趙老師頤養(yǎng)天年的好日子開始了。
但三年后,不顧美方一再挽留,趙家和放棄待遇豐厚的工作,執(zhí)意回國(guó)。好友問他為什么突然要回來,趙家和答:“信美然非吾土,田園將蕪胡不歸。”
此時(shí),誰(shuí)也不知道趙家和心里暗藏著怎樣的“玄機(jī)”。
2001年6月,剛剛回國(guó)的趙家和把在美國(guó)講學(xué)積攢下的20多萬(wàn)美元,交給了從事金融投資的學(xué)生劉迅打理。自己繼續(xù)在外講學(xué)、給商業(yè)機(jī)構(gòu)做顧問,馬不停蹄。
此時(shí),趙家和賬戶上的資產(chǎn)一筆筆累積著,美元、人民幣、外匯券……“可他從沒問過投資收益怎么樣。”這讓劉迅頗有壓力,“也許老師是要做個(gè)大項(xiàng)目?也許是犧牲當(dāng)期消費(fèi),獲取長(zhǎng)遠(yuǎn)利益?”
直到2005年的一天,劉迅的疑問突然有了答案。“那天我在電話里隨口告訴趙老師,賬戶里的錢已經(jīng)超過500萬(wàn)元人民幣了。趙老師沉吟片刻,重重地說:‘嗯,可以做點(diǎn)事了。”
做什么事?劉迅并沒有猜到,但接下來的“劇情”讓他感受到老師的嚴(yán)謹(jǐn)、扎實(shí)——在怎樣賺錢上從未表現(xiàn)出半點(diǎn)“理性經(jīng)濟(jì)人”特質(zhì)的趙老師,在如何花錢上拿出了看家本領(lǐng)。做了一輩子“雪中炭”,72歲的趙家和再次點(diǎn)燃自己,他要把能量輻射到更廣闊的大地上。這一次,不再是組織安排,而是醞釀已久的自主選擇——捐資助學(xué)。
先搞實(shí)地調(diào)研。為了解貧寒學(xué)子的生活狀況,趙家和搭公共汽車,一趟趟跑到北京的遠(yuǎn)郊延慶考察,每次回來都疲憊不堪。
再搞模型論證。奔波大半年,趙家和告訴劉迅:從小學(xué)到初中有義務(wù)教育,上大學(xué)有國(guó)家助學(xué)貸款,要花,就花在窮孩子“最要?jiǎng)拧钡母咧校@是“邊際效用最大化”。
2006年,第一筆助學(xué)款從北京寄出,江西、湖北、吉林、甘肅……中國(guó)的版圖上,多少在困境中拼搏的貧寒學(xué)子在趙老師的助推中重燃希望。
2009年,由于資助學(xué)生過于分散,為避免“四處撒錢”,趙家和決定改變捐助方式,從白銀市實(shí)驗(yàn)中學(xué)整班學(xué)生資助開始,把捐助對(duì)象范圍從全國(guó)多地向西部聚攏。
助學(xué)走上正軌,趙家和卻在例行體檢中查出患了肺癌,已經(jīng)是晚期,癌細(xì)胞已經(jīng)向脊椎和腦部轉(zhuǎn)移。
晴天霹靂!“老天爺太不公平了,怎么能讓這么好的人得絕癥?!”驚悉消息,劉迅憤怒了,“我又突然慶幸,趙老師的賬戶上已經(jīng)過千萬(wàn)元了,可以保證最好的治療。”
可趙家和又作出了驚人決定:保守治療,捐出全部積蓄助學(xué),并醞釀成立基金會(huì),讓助學(xué)更加長(zhǎng)久和規(guī)范。
一場(chǎng)與生命的賽跑就此展開——2011年,趙家和找到了學(xué)生兼同事、清華經(jīng)管學(xué)院原黨委書記陳章武,委托他籌建基金會(huì)。2012年初,由趙家和捐資倡導(dǎo)建立的甘肅興華青少年助學(xué)基金會(huì)正式成立,華池一中、環(huán)縣一中、鎮(zhèn)原二中等甘肅省10所高中共1000名優(yōu)秀寒門學(xué)子成為資助對(duì)象。
整整六年,劉迅、陳章武一直為趙老師保守著秘密:捐資助學(xué)不留名。
誰(shuí)也沒想到,勤儉的趙老師有“1000多萬(wàn)元”,而且“全都捐了”。直到基金會(huì)成立的消息在清華校園傳開,常與趙家和嘮嗑的邵斌才“猜出來了”。
那時(shí)的趙家和已經(jīng)臥床不起。在陳章武赴蘭州出席基金會(huì)成立儀式前,趙家和反復(fù)叮囑,在基金會(huì)的名稱和章程中一定不要出現(xiàn)他的名字,他的家人今后也不在基金會(huì)擔(dān)任任何名譽(yù)或?qū)嵸|(zhì)性職務(wù)。基金會(huì)成立當(dāng)日,趙老師又從病榻上給陳章武打電話,“嚴(yán)肅強(qiáng)調(diào)”:不要向媒體透露他的姓名,不要帶回任何禮物。
“興華”助學(xué),“他鐘愛這兩個(gè)字:一是與眷戀了一輩子的‘清華音近;二是取‘振興中華之意。”劉迅這樣解釋。
生命垂危還為了省錢堅(jiān)持吃便宜藥的趙老師,讓劉迅這個(gè)每日與錢打交道的投資人領(lǐng)悟了“錢”的真諦:“他知道怎么賺錢,可他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怎么把錢花在最有價(jià)值的地方。他教給我們什么才是最好的投資。”
一團(tuán)炭火如此平凡,又如此高貴。一如他的歸宿,意蘊(yùn)深長(zhǎng)——在北京城郊的長(zhǎng)青園公墓,趙家和的名字與眾多遺體捐贈(zèng)者的姓名一起刻在一塊碑上,只有仔細(xì)看才能找到——他燃盡自己,了無(wú)遺憾;剩下那抹至純至凈的灰,仍滋養(yǎng)后人;而他的精神,燭照世界,永不熄滅。(摘自2016年7月4日《光明日?qǐng)?b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