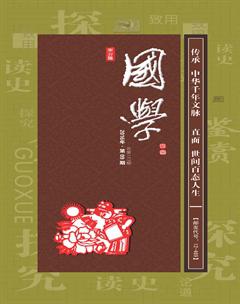晚清時代的人工智能
會寫字的機器人
對130多年前一個叫徐建寅的中國人來說,機器甚至能預測他未來的命運。1881年,年僅36歲的徐建寅,已經是當時虎虎生風的洋務運動中最得力的技術人才,三年前,他赴德國考察學習科學技術。他見識了無數西洋新式機器創造的奇跡,但仍然以這一年9月11日在柏林蠟像館里見到的那尊會寫字的機器人最讓他感到驚異。
這尊機器人是一尊蠟人,“面目衣履與生人無異,能據案疾書。足有輪,可任意推置何處”,但打開這個機器人的衣襟,就能看見胸膈里面“機輪甚繁,表里洞然”,只要打開開關,這尊機器人就可以“一手按紙,一手握管橫書”。若在機器人的掌心寫字,然后握緊拳頭問他,則機器人“口不能言,而能以筆答”。于是,徐建寅就在掌心寫了幾個中國字,然后問機器人“余幾時能返中國?”只見機器人右手執筆,寫下了“冬間”一詞。
這個答案當然讓當時的徐建寅感到啞然失笑,因為他其時并沒有回國的打算,但就在這一年的冬天,徐突然因為急事不得不回國,此時他又想起當時柏林機器人所作出的預言,不由得在這一天的日記后面用小字寫下了自己的感慨:
“其時余未有歸志,其后卒如其言,不知蠟人何以能先知也?此事若非目擊,出于他人之口,鮮有不河漢其言。在外洋數年,所見奇異,終以此事為第一。其神妙莫測,直覺言思擬議之俱窮矣!”
徐建寅所見到的機器人,不僅可以模仿人類寫字,并且還能先人一步預測出人類的下一步命運,確實如徐所言,令人感到“神秘莫測”,難以言喻。不過與現代人想法不同的是,徐建寅并沒有夸想出日后機器勝過人類,人類反而屈膝于人工智能之下的“歹托邦”未來。就在第一次參觀寫字機器人的12天后,也許是實在不能忘情于那尊能寫字預言未來的機器人,他又和當時寓居柏林的著名“中國通”、京師同文館的“洋教習”丁韙良再一次去了蠟像館,這一次連在海外見多識廣的丁韙良也感到震撼:“機器之妙能奪天工,此事曾見古書,不謂今日乃目睹之爾!”
“曾見古書”這種充滿了崇古氣息的說法,恐怕不是丁韙良這位“中國通”一人的所思所想,對站在身旁、生長于一個積淀著五千年歷史文明的老大帝國的徐建寅來說,這種發古之幽思的情緒也許更加強烈。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面對現代西洋科技時的思古幽情,乃是晚清時人的一種共同心態,他們需要從自己熟悉的歷史中尋找合適的部分,拿來安插在自己所不熟悉的文明上面,以彰顯中國人見多識廣,所以見怪不怪。畢竟,徐建寅見到的這個能寫字預言未來的機器人,并非晚清中國人見到的唯一一尊機器人。
西洋機器人來了
周圍的人都紛紛閃避,唯恐擋住了這個頭頂禮帽、叼著雪茄之人的前路。因為這個看似不異生人的西裝革履的家伙,竟然一邊疾步行走,一邊從禮帽上冒出了滾滾濃煙。
對打開這一天上海最時興的畫報《點石齋畫報》的晚清讀者來說,他們肯定會被眼前圖畫上的那幅奇景所吸引。這一景象確實令人驚駭,但是,讀過畫面上方那段介紹文字的讀者就會明白,這不是有哪個家伙引火燒身或是太過憤怒所以真的“七竅生煙”了,而是這個頭頂煙囪禮帽之人,乃是一架善于行走的機器人。
它是美國一位名叫佐芝模的博士的新發明,其行走的原理,是因為“腹中藏有機器爐鼎,以火燃之,其人即自能行走,迅捷異常,計一點鐘能走五英里之遠”,而他頭上戴的帽子,真的是一個煙囪,因為這尊機器人需要靠火力蒸汽驅動,所以才會從帽子里冒出煙來。在這段介紹的最后,作者就像徐建寅一樣發出慨嘆:“嗚呼!技至此,可謂神矣!”
不過,這則晚清機器人的獵奇報道,最有趣的部分并非僅僅關注于這尊具有后現代蒸汽朋克風格的機器人,而是在于報道前面論者所發的一通議論,在這段占據了一半篇幅的議論里,作者縷述了中國古代同類偶人的歷史,并且還在開頭附會上了國人諳熟的陰陽五行之說,“嘗考五行中,惟水火有形無質,余皆可以制成人形”,緊接著,作者追述了昔日“孔子曾見金人三緘其口,秦始皇鑄金人十二;越王慕范蠡,用金鑄其像”等長長的一段中國人形制作史,直到最后才進入正題,描述這個西洋的行走機器人。
玄機恰恰隱藏于這段看似冗余的敘述之中,它當然可能是評論者炫耀自己的博學多才,但更可能是為了從中國悠久的歷史中尋找相類的事物,以證明在這類奇技淫巧方面,中國古人并不輸給西洋列強。而這一點從某種意義上說確實有據可查。
譬如論者在文中提到的“秦始皇鑄金人十二”這個例子,并非僅僅指的是《史記》中那句簡短的“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鑄金人十二”的干澀記述,而是公元3世紀的一本偽托道教創始人葛洪之名的小說《西京雜記》中的內容。這個故事講述的是公元前206年,漢高祖劉邦在秦始皇的寶庫中發現的一套神奇的會自動演奏音樂的銅機器人:
“復鑄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繩花采,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后,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扭繩,則眾樂皆作,與真器不異焉。”
對將悠久的歷史視若拱璧的中國人來說,倘使要循著這一思路,在數千年的歷史中找出類似現代西洋人工智能科技的發明,可謂歷朝歷代,史不絕書。在比《西京雜記》稍早成書的另一本史學著作《三國志》中,也記載了一個其能力絕不下于發明行走機器人的美國博士的發明家馬鈞,他成功地通過改裝,讓一套不能動的傀儡木偶活動起來。
古代中國機器大師
制造自動機器人的大師代不乏人,即使是在六朝亂世,仍然有這種精思技巧之人,公元4世紀后,趙暴君石虎統治時期,就有一個叫解飛的人,為石虎制造了一輛檀木車,車上坐著一尊金佛像,只要車走起來,就有九條龍對佛像噴水,同時又有十余尊木制機器道人,其中一尊能“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間”,而另外十余尊木道人則“皆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輒揖禮佛,又以手撮香投爐中,與人無異”。而隋朝的另外一位暴君隋煬帝,也有他自己的機器人大師黃袞,在他奉命撰寫的機器百科全書《水飾圖經》中,記載了一種機器人的水上表演,在水中安置機器,用以操控水面上七艘載有機器木人的小船,船上的機器木人除了可以自動撐船、蕩槳,還可以給等在水邊的賓客斟酒。
這些機器大師中還包括一位皇帝,明末的倒數第二位皇帝熹宗朱由校就是一位狂熱的木制機器愛好者,根據《天啟宮詞》里的記載,這位皇帝發明了一種“水傀儡戲”:“用方銅池縱橫各三丈,貯水浮竹板,板承傀儡,池側設帳障之,習為此者,鐘鼓司官也。數人隱身帳內,引其機,輒應節轉動。左右宣題目、鳴鑼鼓者,代傀儡問答者,又數人。所演有東方朔偷桃、三寶太監下西洋諸事”。可以說這種靈怪機巧的程度,應該遠遠高于晚清時人透過圖畫想象一個禮帽冒煙的機器人行走時的模樣。
細心的人也許會發現一點,剛才所舉出的所有中國古代引以為豪的人工智能機器的例子,幾乎全都是玩物,這恐怕也是中國的機器大師們所能達到的極限了——他們所制造的只是一種可供玩賞的自動玩具,對他們的評價也僅止于“巧”,卻難以突破這種“巧”,來發展出像西洋那樣真正的實用機械制造學來。
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即使是西洋人攜帶這種技術來華,在中國人那里也往往被當成是一種玩具。18世紀來華的擅長機械技術的西洋傳教士,很快發現自己在皇帝面前只是一個宮廷玩具大師,用以滿足皇帝的西洋旨趣。1754年,身在宮廷中的傳教士錢德明在寄回歐洲的信中多少有些無奈地寫道:
“為了討好皇帝,為了聽從他的旨令,楊自新教士剛剛做成了一只自動的獅子,它能像一只普通獅子一樣走上百步。楊自新教士在它體內裝置了許多彈簧使它走動。這位教士把最先進的機械制造技術都用到了他的機器人上。”
而15年后,另一個來華的傳教士汪達洪則發現他自己干脆成了皇帝的機械師,他被要求負責維修楊自新為皇帝制造的機器人,并且奉命制造“兩個捧著花瓶會走路的機器人”。
這些來自西洋最天才的機械技師的頭腦,全部都傾注于滿足皇帝對西洋玩具的好奇心上了。但與之相比,這些西洋機械師還是很幸運的,他們的中國同行卻在這個老大帝國的暮年遭遇了自己的受難曲。我們能夠查到的最后一個中國土生土長的機器人大師名叫石甘四,他的名字只在一本鮮為人知的地方志《湘潭縣志》里出現過一次。
根據方志上簡短的記述,這位18世紀默默無聞的機器大師,受到《三國志》里諸葛亮“木牛流馬”的啟發,制造出兩個木頭機器人給他當仆役。如果他的這一發明真實可信并且得到推廣的話,那么,也許中國的人工智能時代會來得更早一些,或者至少不會讓晚清的讀者為一個腦袋冒煙的美國機器人嘖嘖稱奇,但他的下場卻是險些被鄰里當成乾隆末年興起的白蓮教匪,他的那些精巧的發明,也被說成是某種邪惡的巫術被控訴告官。無奈之下,石甘四只得親手毀掉他制作的機器人。
對這個老大帝國的臣民來說,巫術比科學更容易解釋他們難以理解的現象。畢竟,就像《點石齋畫報》上所描繪的那些從行走鐵人身邊四處逃散的人一樣,這一情景當然是出自中國繪畫者自己的想象,因為對于他和他的同胞來說,逃避比好奇更符合中國人的天性。但對于晚清的公共知識分子來說,這種逃避的天性亟需改變。
——《鳳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