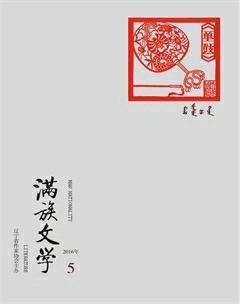以怎樣的愿力書寫
劉恩波
曉峰一共送過我四本書,即《看法——王曉峰文學筆記》《當下小小說》《生活里的文學和藝術》,最后是《喜歡玉一定喜歡陽光》。
曉峰突然走了。聽到消息,心下一片茫然混沌。怎么都難以接受這個事實。朋友去矣,長歌當哭。
所幸還有記憶,會讓自己想起從前的好時光,當初的緣。
最早讀到曉峰的文字,是在1995年第四期的《藝術廣角》雜志上。其中有“評論家特輯”欄目,那一期上了我和曉峰。照片上的他顯得很斯文,在臨水的欄桿前站著,身著筆挺的西服,看上去一副謹慎謙恭的樣子。那會兒他的文字也不野,不大講究文采格調,是修辭立其誠的君子之言。不過盡管如此,從他那略顯平實質樸的口吻里,我還是聽到了生命本真的喧嘩與騷動,因此,格外喜歡閱讀他的個人自述——在那里,他寫到童年難忘的往事——“我有四個弟弟,我為老大,因此小時候常常領著弟弟們玩得昏天黑地。一次,在瓦房店站前的小廣場上(比現在的要好看多了),為了玩開飛機,老三鉆進了已廢棄而放倒在地的水泥郵筒里。鉆進去就出不來了。嚇得我和老二都哭了。四周圍滿了人,都沒有什么辦法。后來來了兩個大人,拿著鐵錘,跪在地上,用手掌墊著郵筒內側(怕砸壞郵筒里的我弟弟),揮著鐵錘小心地一塊一塊地砸水泥郵筒,直到我家老三能從郵筒里爬出來……”
上面這段文字完全是工筆和素描,未見裝飾和渲染,在我的記憶里卻宛如一道光束,照亮了心靈某個塵封的角落,如今讀起來,更加感念物是人非,生命的不由自主和飄如轉蓬。
好在文學本來就是夢的集結和儀式般的相逢或是重逢,這樣重溫曉峰的書寫,就是對朋友最好的紀念和話別。
1
《看法——王曉峰文學筆記》是他送給我的第一本書(以下簡稱《看法》)。當初讀曉峰的《看法》,覺得他的變化是令人吃驚的,他開始將評論的目光從傳統的精英文學領地拓展到更加寬闊蕪雜的市民文化圈兒,尤其值得注意的還在于,此際他談說的姿態有些遠離主流文學批評的過于概念化理念化,而變得非常輕松、自如、瀟灑。其中,我為之傾倒的是一篇題為《讓我們現在來談情說愛吧》的文章,在那里,曉峰游走在理論和詩意之間,歷史和當下現實之間,還有命運和靈魂的奧秘之間,用眩暈的近乎萬花筒般的筆法,交織勾勒了新世紀的愛情魔方的不可思議、迷離莫測與恍兮惚兮。
我知道,按照曉峰的固執想法,評論本身就是一種創作,雖然它借雞生蛋,可那蛋依舊是充滿了可愛的顏色,美麗的光暈和可人的觸感的。
為此,曉峰的許多評論都寫得那么有靈氣,有體溫,有光澤,是帶著心意、心愿和心音的觸摸和顫抖完成的,從而讓我們分享到他對人生和世界充滿變幻多姿的色調情趣的內在貼靠和咂摸。更關鍵的還在于,他的漂亮的文字里面總是承載著個體對當下現狀的反思、究詰與剖析。
他寫《讓我們現在來談情說愛吧》并非心血來潮的沒話找話,而是對于那個年代盛行開來的愛情即時性商業性速遞速配現象的洞燭幽微的揭示、闡發和把脈。那個時候正是衛慧的《上海寶貝》大行其道之際,解構古典愛情的趨向正以風高浪急不可遏制的勢頭在文壇流行蔓延開來。“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如果若干年前出現的《廊橋遺夢》中的男女之愛還萌發于“為了古老的夜晚和遠方的音樂”的浪漫口實,那么在衛慧筆下,人們已經不再背負傳統道德的十字架,而是隨意隨性地交接合歡,只要他愿意,而她也想要。
對于“生猛無忌,一路殺去”的衛慧式寫作,曉峰一方面抱以理解和局部地認同,指出《上海寶貝》表現了另類的生活,“它樸素、率真、坦誠,膽子也不小,有平民底層情懷”。而另一方面,他不無憂慮地對愛欲失控的精神癥結,給予了必要的有力的質疑、辯駁和糾正。那會兒,他在讀福柯的書,尤其是《性史》里面的觀點,帶給他“理性上的清醒。”他甚至在行文里用略帶玩笑的口氣,說學習福柯精神,“我力爭做到不走樣,請同志們監督。”
曉峰當年的質疑和追問即便今天讀起來依舊振聾發聵,觸目驚心,因為他以自己敏銳的觸覺撞到了新生代愛情敏感部位的痛癢,因為他看到了當下社會現實的病灶——“當下小說的愛情敘事走得似乎遠了一些,有許多相悖于人類應有的文明精神和道德情操。愛情話語,已經不是戀人絮語,喃喃自語,而是一種大眾話語,像集貿市場里買賣雙方公開而無恥地討價還價一樣。”對此,曉峰以近于心靈告白式的質問,對解構和調侃愛情的作品提出了嚴峻的對質和懷疑,我們是不是在放縱自我、放縱自我欲望?我們是不是忘記了什么叫體面、優雅、尊嚴和高尚?我們是不是置理性、法理于不顧?
看到此處,我有點擔心曉峰是否會走火入魔,變成保守派的禮教衛道士?變成捍衛人類傳統道德觀念的清道夫?
然而,讀曉峰的文字,我最欣慰的還是,他剛剛要把審美的游戲搞成道德裁判的法庭,盡管后者有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理正義墊底和支撐,所幸他及時地懸崖勒馬,這表現在曉峰的措辭后來明顯軟了下來的語調,讓我懂得,文學的可愛和自在無為的妙哉。他寫道:“2000年的7月13日,我家所在的白云新村的一戶人家放了大半下午的流行音樂——我聽不出來是誰唱的,唱的是愛情,愛的興奮,愛的失意……問題是,這聲音的分貝太高了,讓正在寫此篇文章的我,心神不寧,焦慮不安……”
正是在此處,我們找到了曉峰的性情。那道貌岸然劍拔弩張背后的松弛和拿不準、不確定、左右為難的不甘心的樣子,才是藝術評論家的真正應該擁有的范兒。
《看法》讓我走近了曉峰,就像曉峰自己在一個細雨蒙蒙的晚上,走近汪國真。那是1991年5月里發生的故事。此刻,我讀著曉峰《汪國真的秘密》,仿佛逆著流轉的時光隧道回到了從前的青澀季節。
當然,在大學讀書期間我就疏離汪國真包括同時期走紅的席慕容,但我覺得他們在讀者群體中還是弄出了不小的響動,值得關注,起碼不應該輕蔑或者予以徹底抹殺。曉峰之所以專程去北京拜訪汪國真,其實是沖著他感興趣的文學雅俗之爭這個宏大的命題去的,汪國真的走紅恰恰讓他發現了在那個特殊的歷史節點上俗文學的魅力所在。他公正地指出,在青少年之間流傳的汪國真詩作和“哲思短語”的手抄本,實際上就是把汪國真的作品看成了一種普及的藝術。endprint
《汪國真的秘密》顯示了曉峰緊密跟蹤和積極體察文學熱點現象并給予及時反饋和認真解讀評判的踏實作風。其實,文學說到底是一種交流,心靈彼此的敞開、叩問和尋找。哪怕歷史翻過了新的一頁,最初的渴求變成了過往煙云,然而,文字依舊會為這不老的情懷和生命深處蕩起的漣漪般的印跡作證。
“那個夜半的時候,我走出了汪國真小小的居室……夜的春雨還在淅淅瀝瀝。”
曉峰的筆下,常常充滿一種難得的屬于他自己的詩意和溫情。
在文章的結尾,他引用惠特洛亞的詩句點出,閱讀的美好在于,“書是時代的見證,是旅人返鄉的航船和駿騎;書是忙碌者最好的娛樂。是解除疲乏的安神丸,它是心靈最好的教堂,也是大自然永恒的花園和苗圃。”如今曉峰和他的訪談者都安息在那里了。
2
斷斷續續地傾聽閱讀和走近曉峰,無論在生活的某個場所和角落,還是在精神交流參與的某個瞬間片刻,我都獲得了不小的收獲,有一種知己之感,同道默契的因緣。記得那次他把《當下小小說》還有《生活里的文學和藝術》一并寄給了我,并囑咐我寫一篇評論,我欣然應諾。《生活里的文學和藝術》應該說是曉峰的代表作,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書做得干凈漂亮。如果說從前的曉峰還有爭論辯駁譏諷,這個時候的他,卻是沉浸于心緒的散淡梳理、體察和點染,不再是嚴謹的工筆,而是潑墨的寫意,不再流連于大主題大話題的深度聚焦,而是游走在細節、情緒、心境的邊緣地帶,臥看斜陽山外山的明麗舒朗。
當然,閱其書、知其人或者知其人、閱其書,我們看到的書充其量是生命的片斷見證,人也是一鱗半爪地揣摩理會,很難通透全面地讀懂那個人。
2000年之后,跟曉峰見面的機會多了,我們參與了省作家協會特邀評論家論壇活動還有省文聯的中青年理論骨干讀書班,一年之中總會見上那么一兩回。曉峰話少,我就更是默默寡言。記得在承德外八廟景點,跟他合影留念了,但現在那照片也早已不知去向。酒桌上喝酒,不見他暢飲,我同樣喝得溫吞。但我們兩個有共同的價值取向,那就是愛惜文字,看重文學本身的澄澈美好,而不太在乎功利名聲等身外之物的羈絆和束縛。曉峰跟我幾乎沒談過生活方面的苦楚和惶惑,我也沒跟他說起過自己的坎坷磨難,兩個人聊的最多的還是評論,還是文學。
再后來,聽曉峰說的最多的就是玉了,而不再是小說散文甚至評論。他轉向了,走向對玉的收藏、鑒賞和品味,實際上,他寫玉的那些文字構成他一生文學生涯的最后輝煌,那么美麗、晶瑩、明凈、璀璨。
3
2014年10月里的一天,曉峰把他的寫玉的那本書《喜歡玉一定喜歡陽光》送給了我,我知道在那里有一種“與我們情思往還的藝術境地”。
其實,古往今來的讀書人不就想在茫茫人世浩瀚宇宙間為自己的心靈找到一個詩意棲居的“場”嗎。用曉峰的話說,就是在世俗生活里以器物和想象建立自己的“獨立的小天地”。
難得曉峰擁有那片癡心,那份癡情,不然何以會有《喜歡玉一定喜歡陽光》里的那些精金美玉一樣的文字分享?
在他眼里,“石頭是活著的生命。玉又是美的石頭,是石頭的精華,是動態生命中美的天使。”他又說,“和玉在一起,只能是對話,交流。用眼睛,用心靈。”
因為真正的分享都出自愛。
有一次某位學生問克里希那穆提,我們為什么游戲的時候快樂,讀書的時候不快樂?
克氏回答,理由很簡單。你的老師不知道如何教你們。如果一個老師愛數學、愛歷史或愛任何他所教的科目,那么你也會愛這項科目,因為“愛”自己會溝通。
在我看來,曉峰生命中最后歲月里留下的文字,都是充滿了愛的愿力,因而輻射出飽滿結實渾厚豐盈的內力質感。這是一種大境界大情懷。也是一種大愜意大自在。
很可惜,曉峰生前我沒有把自己的閱讀感想及時反饋給他。如今才知道,這該是多么地遺憾!
也許,《喜歡玉一定喜歡陽光》是曉峰本人最為得意滿足的收獲。那是將器物和內心融為一體,將外在和內在打成一片的“心中的惋嘆”。這“心中的惋嘆”是曉峰靈魂世界的低語、傾述、沉思、挽留、告別……
只可惜現在的人和現在的文學,還沒看到什么發現什么,就興奮地大喊大叫起來,張揚著滿世界都知道(《敘述縫隙的深處》)。對比之下,曉峰的書寫,就有點在語言和敘述的縫隙深處打撈精神光影的默默者存的況味。就像他喜歡的玉,無聲息地擺放在那里。只有愛它的人懂它的人才會停下來,守望流連欣賞那靜謐紋理之中集聚沉淀下來的歷史刻痕。
讀曉峰的書,我想到虛云大師的話,“一切處都是用功。”某種程度上,《喜歡玉一定喜歡陽光》字里行間無不是作者內在情懷的承接、起舞和流動,他是那么渴望而近于虔誠地把玉的豐富的色彩、獨特的造型,甚至形態器物所凝固下來的美,都一點一滴告訴給我們聽。
曉峰談玉,別開生面,別有匠心,別具幽情。在他那里,玉是一種文化,一份情致,一脈氣息,一縷精魂。好的玉制品,都寄寓著人工與天道自然的絕美契合、共生和再造。而中國古典美學中又有象以立德之說,如此看來,玉之所以能進入人的精神審美層次,大概是因為它負載濃縮象征了生命的諸多內涵、底蘊、格調及靈性。
在曉峰筆下,玉實際上已經獲得了人格化、藝術化的匯聚和提升,體現出心意的寫照,歲月的磨礪,歷史的變遷和悟性的沉潛。你看,他從那青玉素壺的純凈本色里,尋找到知己般的安慰,“和架上的玉壺在陽光里無語地交流,心里洋溢著暖暖的潮水。”而在對黃白老玉圓雕《不一樣的童年》的梳理玩味咂摸之際,曉峰沉醉于鄉土少年走在上學的路上唱歌、手提鐮刀、扌匯 著水桶的生命造型之美,在那其中,他認定了藝術的本質和生活真相的難以切斷的扭結的魅力所在。所謂的歷史感,其實已經濃縮雕鑿于幾個孩子或是歌唱或是微喘或是微笑的復雜神態里,成為那個年月和時代的蘊含豐富的表情。玉之美當然有一種溫潤祥和圣潔的氣息,甚至在美麗壯闊的大自然里,都會發現玉之美的無所不在。曉峰有一篇《白玉之歌》,寫他到新疆訪玉的見聞,里面說“烏魯木齊藍天下的云和雪,讓我想到了白玉。”讀此,令人不覺心向往之。玉的故鄉,也是藝術發生涌動的現場,也是心靈流通天地造化的洗禮之處——當曉峰把朋友送給他的和田白玉扣帶到它的源頭,在天池冰涼的水里,在吐魯番的坎兒井中,在喀什噶爾河邊,他都把這白玉扣,放在它出生的雪水里,感覺手里溫潤和心里溫暖,那一刻,他有福了!endprint
《金剛經》用“深解義趣,涕淚悲泣”來寫照人進入悟道進境后的自然狀態,我讀曉峰寫玉的文字,盡管沒有涕淚悲泣,可還是動了感情,只因為曉峰寫玉的癡迷和深情。如今寫美之石者美之壺的人不在了,那文字里卻有熱的愿力,水的漣漪,生之喜悅和禪意一般的靜。
含而不露的謙謙君子,這是我交往中最為欣賞的曉峰的秉性所在。文如其人,成就了他的美之玉,詩之玉。
4
“好東西是慢慢品出來的”,“好多時候,突然看到了一幅畫,一本書,一個玉器……只覺得好,但給不出理由”“言說永遠存在著局限”……盡管如此,那些沉默的玉,那些沉默的文字,畢竟見證了一個人入骨的體察和貼靠,撫愛和滋養,那眼神,那心跳,不約而同給了我們與藝術精神相往還的契機和緣分。現在想來,有十年的光景曉峰在寫玉,依偎著玉,就像用無限的渴望和熱切擁抱著歲月的冰冷和人生的虛脫。
也許,寫玉,總比寫人好些吧。贊美玉,玉依舊沉穩安妥,不會有任何驕傲之心。人呢,很難說,很難把握,對于寫評論,我的感覺是曉峰后來厭倦了,一點兒也不喜歡。當然這是我的主觀猜想。
我看到的曉峰的最后的文字是給《藝品》寫的,取名“最幸福的時刻”。那次我約曉峰為我們的刊物寫稿,他爽快地答應了。重讀茨威格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用回憶的口吻講述1979年前后在《世界文學》雜志上看到該作品時的怦然心動以及對青春的啟蒙,他寫道:“那時的閱讀給我留下了永遠的印記,讓我知道了什么是最好的小說,和什么是可歌可泣的愛情。那時我還是一個大學生,對小說藝術以及愛情,有著難以遏制的愿景和沖動。”兩年前我就非常珍視曉峰的這篇小文章,現在則更加珍視。它寫得漂亮雋永,充滿了人生閱歷的回味和莫名的感慨乃至憂傷,隱隱的,淡淡的,如味道回甘的佳釀。其中有段話,值得抄寫下來,作為永遠的記憶吧——“我重讀這不朽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是在一本書《斯·茨威格小說選》,1982年1月由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這書應該是我在當時的復縣(多好的名字啊)逛新華書店時買到的。那時我對復縣新華書店熟悉到文學柜臺什么位置有些許變化都能馬上感應。昨天在微信的朋友圈里我看到遼寧省文聯的于雙說她在逛書店,還是‘外文原版區,比我那時要高級多了,都能看外文原版了。我非常喜歡逛書店的逛。我要是有錢了,就重獎逛書店。這是閑筆,好玩,一般人看不出深刻來。恩波不要刪這句話啊……”
斯人已逝,文字猶存,隔著時空,隔著歲月,依舊閃現著夢境般的呼吸和光澤。
茨威格的小說刻畫了一個女人燈蛾撲火一樣的愛情,書信體的傾述,蕩氣回腸,果真是字字看來皆有淚,“一寸相思一寸灰”。曉峰的解讀伴隨著人生遭際和故事本身的兩個聲部的配合呼應,讀起來意味深長,風韻滿紙。
這是以怎樣的愿力書寫而成的呢!
巴金說,他是把愛留在了溫暖的腳印里。
我相信曉峰的文字跋涉中也曾有過這溫暖的腳印。
為此,他可以告慰自己和文學。
〔責任編輯 叢黎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