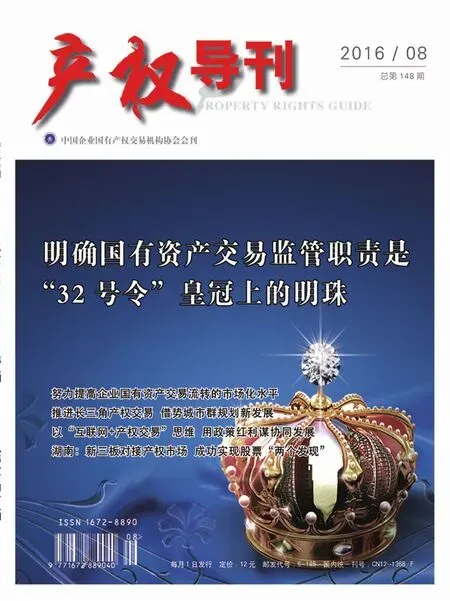觀點集萃
觀點集萃
經濟運行的杠桿風險加大
經濟學家連平7月18日在《經濟參考報》發文——
外部經濟環境仍存在不確定性。全球經濟正在經歷結構調整,除美國以外的主要發達經濟體、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脆弱性在增強,不確定因素依然較多。在初級產品及低端加工產品需求走弱和價格下跌的影響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失衡問題依然嚴重,整體經濟增速有可能放緩。同時,經濟運行的杠桿風險加大。去杠桿作為今年經濟工作中重要一環,對于穩定經濟增長、降低風險具有重大意義。而貨幣投放擴大和房市政策放寬帶來的“溢出”效應引起關注,有必要警惕實際信貸增速過快、企業債務和房地產市場杠桿“不降反升”的風險隱患。

未來互聯網金融創新發展將呈現出五大趨勢
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7月9日在的首屆紫金峰會上表示——
未來,互聯網金融創新發展將呈現出五大趨勢。第一,從參與的主體來看,大型傳統企業開始不斷加入,成為行業的新鮮血液;第二,智能投顧被視為互聯網金融新的風口;第三,區塊鏈技術在重構整個互聯網金融的底層架構;第四,大數據運用在互聯網金融領域向縱深展開;第五,互聯網金融發展已呈現兩個非常典型的兩個方向的演變,一是生態化,一是專業化。所謂生態化,就是支付基金、保險、銀行、證券、信托、征信等多種金融業務進行整合,形成一個生態價值服務的產品鏈條。所謂專業化,就是專注于某一個細分領域,比如創投的眾籌、P2P、征信、消費的分期領域這些方面。
三方面推動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確立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胡祖才7月7日表示——
下一步,將從三方面推動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的確立。一是要推進反壟斷執法的常態化,有效地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的發生。同時也要不斷完善《反壟斷法》的法律法規,特別是通過制定相關指南和細則來增強法律的操作性;二是組織實施好公平競爭審查制度。使政府相關部門政策的制定者,也包括制定產業政策的相關部門,增強對競爭政策的理解。在制定相關政策時,自覺開展公平競爭審查工作,使兩者能夠很好地協調和融合;三是要培育全社會競爭文化。最重要的是加強競爭的倡導,營造全社會公平競爭的氛圍。
亞投行未來會更注重項目風險評估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行長金立群7月5日在香港表示——
亞投行與其他國際開發銀行并非競爭對手,而是合作關系。即將有3個項目由亞投行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共同提供融資。目前市場有12萬億美元的債券處于負回報狀態,這反映出市場避險情緒高漲。因此,在未來投資基建項目時,亞投行會更注重成本效益及風險評估。
中國經濟體量大,韌性強
中金公司原董事長李劍閣于7月5日在香港金管局與博鰲亞洲論壇合辦的金融合作會議上表示——
中國經濟不僅體量大,而且韌性強、回旋余地大,不會出現外界所擔心的災難性前景。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進入到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增長率下降了幾個百分點。但由于中國經濟體量已今非昔比,即使5%的增長率,所帶來的GDP增長絕對值也是可觀的,不亞于之前的高速乃至雙位數增長。同時,由于中國人口近年來緩慢增長,目前的中高速增長基本能夠滿足新增就業需求。中國正在進行的“去產能”,可能會帶來一部分人的失業,但最高估計也沒超過300萬。從就業的角度,中國經濟壓力并不大。中國政府已明確不搞超強的經濟刺激和大水漫灌,而是將重點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這有利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性和發展后勁。
去杠桿要打破剛性兌付
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管清友近日在對接受采訪時表示——
去杠桿,主要是降低非金融企業杠桿率、降低國企杠桿率,現在對于上市公司的融資監管已經有所加強。債務需要慢慢消化,逐漸降低債務風險,關鍵是要有序打破剛性兌付。剛性支付打破了之后,想讓債務消失是不可能的,未來肯定要向市場傳遞改革信號。當然可通過資產證券化、債務重組等方式去杠桿,但是有些債務“滾雪球”似的,利息都覆蓋不了,更別提償債,這時該破產的就要破產。從政府角度來說,政府沒法兜住所有企業的債務,那不現實,也不合適。一些企業破產,部分債權人需要承受相應后果。
運用市場的方法是解決中國金融業發展癥結的重要途徑
著名經濟學家樊綱7月5日出席“‘問道’濟南區域金融中心2016論壇”時表示——
中國金融體系目前存在三大癥結。第一,中國市場的直接融資比例太小,還不到10%,直接融資太低的重要后果就是杠桿率過高。第二,產能、庫存過剩。第三,剛性兌付問題。如何解決中國金融業面臨的三大癥結?樊綱認為,政府要少參與金融業,要使用市場的力量,民間的力量,讓當事人承擔風險,而不是政府承擔風險。通過市場方法,在當事人承擔風險的基本制度下,由他們之間相互交易,相互議價,找出一個大家能夠接受的交易方法、交易方式。政府只發揮監管、制定規則,提供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作用。
存量資產機會:資產證券化+并購重組雙輪驅動
招商銀行資產管理部總經理周松7月5日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表示——
對于存量資產的發掘,應從深化供給側改革大局出發,從符合國內經濟和金融轉型方向的各類資產重點著手:一是資產證券化。特別是企業資產證券化和非傳統金融機構的資產證券化。因為資產證券化有利于實體部門去杠桿以及促進金融服務的多樣化轉型;二是并購重組。資產證券化是存量企業債權資產的優化,并購重組則是存量企業權益資產的優化。前者對應去杠桿和推動直接融資,后者對應去產能和推動供給側改革。銀行資產出表對應的是實體加杠桿,企業資產出表對應的是實體去杠桿,非傳統金融機構資產出表代表的是經濟轉型和金融深化。后兩者更符合經濟和金融轉型的訴求。

地產行業呈現五化發展趨勢
全聯房地產商會常務副秘書長趙正挺7月5日在第八屆中國產業地產發展論壇上指出——
房地產行業經過十年高速發展后,面臨宏觀經濟增速放緩、人口結構調整、投資增長速度下降、行業集中度上升、市場分化加劇、產品模式升級等挑戰,加上受大數據、云計算、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等沖擊,地產行業朝著產業化、金融化、綠碳化、信息化、國際化“五化”發展的趨勢愈加明顯。為此,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平臺,產業地產及產業園區面臨轉型升級的內在需求。
經濟到底部的時間不會太長
中央財經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所長賀強6月25日在“中國宏觀經濟與證券市場發展高峰論壇”上表示——
從空間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增速從14.2%已下滑到6.9%,增幅跌了一半多,說明經濟下跌的幅度已很深;從時間上看,中國經濟增速到去年為止已下降了8年,超過了九十年代經濟連續下滑7年,這說明經濟下滑時間已很長了。但經濟是否已到底,還需要觀察。比如物價的反彈是豬價推起來的,而固定資產投資對應的反彈是被房地產爆炒拉動起來的,能不能持續存在疑問。中國經過長期的經濟增速下探,探底的過程可能會緩慢出現,不會是一個V型的反轉。但經濟到底部的時間也不會太長了,經濟一旦見底將會給市場帶來一系列的希望。
人民幣國際化有機遇但不可操之過急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6月25日在“國際貨幣體系之占優貨幣問題研究論壇”上表示——
人民幣國際化不可操之過急。目前我國貨幣存量達20萬億美元,實際是個“堰塞湖”。如果按照傳統模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對金融穩定極其不利,因此人民幣國際化要走一條與眾不同、漸進的道路,各種政策需要建立在精心務實的研究基礎之上。同時,英國脫歐將導致歐元相對地位下降,國際貿易、國際金融交易需要新的貨幣來平衡美元獨大格局,因此客觀上全球需要人民幣。另外,對于英國而言,脫歐之后對中國的依賴可能更大。在這些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可能有機遇。
新經濟將產生更加重要推動作用
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許憲春日前在第十屆“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論壇”上指出——
工業中的新經濟持續快速成長,對我國傳統經濟的下滑發揮重要對沖作用,減輕經濟下行壓力。但新經濟體量目前還比較小,還不能完全抵消傳統經濟下滑的影響。一
旦新經濟體量大到可以抵消傳統經濟下行的影響,那么中國經濟可能就穩住了。可以預期,新經濟對未來我國經濟發展必然產生更加重要的推動作用。同時,新經濟的成長也造成了GDP總量的漏統和增速上的低估。目前國際上對新經濟的基本概念、內涵特征以及口徑范圍還未形成共識。新經濟在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也給政府統計帶來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