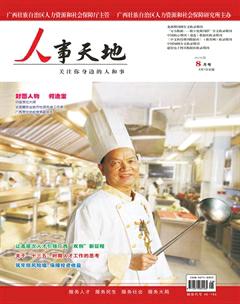關于“十三五”時期人才工作的思考
董志超
2016年對于中國來說是一個重要節(jié)點。作為“十三五”規(guī)劃的開局之年,3月16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三個五年規(guī)劃綱要的決議》。面對經(jīng)濟進入新常態(tài),結(jié)構(gòu)性矛盾凸顯,世界經(jīng)濟整體下滑,中國經(jīng)濟轉(zhuǎn)型升級,從要素驅(qū)動向創(chuàng)新驅(qū)動轉(zhuǎn)換,國家制定了針對結(jié)構(gòu)優(yōu)化、供給側(cè)改革為主線的五年發(fā)展規(guī)劃。規(guī)劃在創(chuàng)新驅(qū)動發(fā)展戰(zhàn)略中提出要實施人才優(yōu)先發(fā)展戰(zhàn)略:“把人才作為支撐發(fā)展的第一資源,加快推進人才發(fā)展體制和政策創(chuàng)新,構(gòu)建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制度優(yōu)勢,提高人才質(zhì)量,優(yōu)化人才結(jié)構(gòu),加快建設人才強國。”
緊接著,2016年3月21日 中共中央印發(fā)了《關于深化人才發(fā)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提出:“充分發(fā)揮市場在人才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加快轉(zhuǎn)變政府人才管理職能。保障和落實用人主體自主權,提高人才橫向和縱向流動性,健全人才評價、流動、激勵機制,最大限度激發(fā)和釋放人才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創(chuàng)業(yè)活力,使人才各盡其能、各展其長、各得其所,讓人才價值得到充分尊重和實現(xiàn)。不唯地域引進人才,不求所有開發(fā)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確保人才引得進、留得住、流得動、用得好。”
可以說,有關人才的話題、有關人才的專項規(guī)劃、課題研究非常多。美好的話語和嚴峻的現(xiàn)實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也正是“十三五”期間不能回避的。究竟出路何在,“十三五”這五年中又可能有哪些突破?
一定不能就人才談人才。戰(zhàn)略定位是第一要務。在制定一些地方“十三五”人才發(fā)展規(guī)劃中明顯看到“部門主義”的影響沒有根本破除,地方發(fā)展戰(zhàn)略不清晰甚至存在重大錯誤。“多規(guī)合一”“一張藍圖干到底”“功成不必在我”應當成為地方、行業(yè)制定“十三五”規(guī)劃的重要理念。定位不準確、不正確就不可能成功。企業(yè)如此、國家、地方、區(qū)域發(fā)展也如此。當然,作為業(yè)務或者綜合管理部門,有一個五年規(guī)劃也是需要的,但這個規(guī)劃毫無疑問是建立在大規(guī)劃之下的。但是很多地方的規(guī)劃是發(fā)改委做發(fā)改委的,行業(yè)主管部門做行業(yè)主管部門的,綜合管理部門做綜合管理部門的。他們之間的業(yè)務交叉部分,由于涉及其他部門的業(yè)務和工作,往往這些部分也就比較模糊,或者直接采用“有關部門”的數(shù)據(jù)。現(xiàn)在明顯可以看到各地區(qū)之間的同質(zhì)化競爭現(xiàn)象,體現(xiàn)在人才政策上也是“大同小異”。言必稱“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言必稱“各種優(yōu)惠條件引進人才”。但究竟你那個地方的戰(zhàn)略定位是什么沒有搞清楚。“要么最好”“要么唯一”“涉及區(qū)域資源配置的則通過區(qū)域性行政組織加以協(xié)調(diào)”是國外地區(qū)發(fā)展的重要經(jīng)驗。“人才圍著項目轉(zhuǎn)、項目圍著資金轉(zhuǎn)、資金圍著市場轉(zhuǎn)”。這需要首先解決地方發(fā)展戰(zhàn)略問題。
環(huán)境和機制是根本。俗語說:“家有梧桐樹,不愁招不來金鳳凰。”要“通過制度建設、市場環(huán)境建設、事業(yè)發(fā)展環(huán)境建設、服務環(huán)境建設、人文環(huán)境建設等‘五大建設,到2020年形成一批生活環(huán)境方便、宜人,市場繁榮有序,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活躍,服務設施完備,服務質(zhì)量優(yōu)良,產(chǎn)業(yè)比較優(yōu)勢明顯,文化、教育、衛(wèi)生等公共服務優(yōu)良,獨具區(qū)域文化特色的宜居宜業(yè)示范區(qū)。形成國內(nèi)一流、國際知名的‘宜居宜業(yè)品牌效應”。你那個地方有機會,你那個地方環(huán)境美,自然就會吸引很多人才。而機制則帶有更加重要的作用,這一點在美國區(qū)域發(fā)展中表現(xiàn)得非常突出。無論自然條件還是生活條件,拉斯維加斯、鳳凰城都絕對比不了底特律,但是底特律破產(chǎn)了。而“不宜人類生存的不毛之地——沙漠”里卻發(fā)展得如此繁榮。
前以色列總統(tǒng)西蒙·佩雷斯在為《創(chuàng)業(yè)的國度》作序中寫道:“我們穿越了茫茫荒沙,回到了沙漠之中的家。我們必須從頭再來。作為一個貧困的民族來到這片貧瘠的土地,我們必須在貧瘠中發(fā)現(xiàn)財富。我們唯一能夠自由支配的資本就是人。這片不毛之地不會折服于金融發(fā)展,而只會折服于所求甚少、勇于開拓的人們。這是一個有理想、有知識的民族,然而,他們寧愿用自己的雙手耕耘這片土地。當發(fā)現(xiàn)土地貧瘠、水源不足時,他們轉(zhuǎn)向了科技與創(chuàng)造。以色列所孕育的創(chuàng)造力與我們的國土面積不成比例,卻與我們面臨的危險相當。國防安全方面的創(chuàng)造力為民用工業(yè)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2008年,以色列的人均風險資本投資是美國的2.5倍,歐洲國家的30余倍,中國的80倍,印度的350倍。與絕對數(shù)相比較,以色列這個只有710萬人口的國家吸引了近20億美元的風險資本,相當于英國6100萬人口所吸引的風險資本和法國合計1.45億人口所引入的風險資本總額。谷歌、思科、微軟、英特爾、eBay……這樣的公司還有很多。一個很少有人知道的秘密就是,這些公司的生死在我們以色列團隊的工作上……中國的深圳、華為也正在展示什么叫環(huán)境和機制建設。華為創(chuàng)立之初就寫下的《華為基本法》,可以說正是這部滲透著創(chuàng)新文化價值觀的管理大綱讓華為成為中國人的驕傲,而他們之所以讓中國人驕傲更是因為他們不是靠壟斷地位的優(yōu)勢獲得的成就。
在環(huán)境和機制建設上,一些誤區(qū)值得注意。首先就是“事業(yè)單位保留公職容許科技人員創(chuàng)業(yè)”的做法要慎重。這不是“康莊大道”,真正的康莊大道是讓那些還存在妨礙人才發(fā)展體制機制障礙的“官辦機構(gòu)”要么破產(chǎn)、要么徹底進入市場,置之死地而后生;要么徹底成為依法運營、規(guī)范管理、透明監(jiān)督的公共組織。其次,就是“官本位不破,創(chuàng)新型國家建設就很難”。官僚體制是客觀存在,也不可能完全消滅,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存在。問題是,不能讓這種“官文化”滲透到社會所有組織中去,滲透到人們的骨子里面。第三,就是各種“人才工程”需要整合,甚至也要“去產(chǎn)能、去庫存”。名目繁多的人才評價、人才工程“把人才的心搞亂了”。“關鍵的不是你是誰,關鍵的是你做過什么,在做什么”。要引導人才關注做事而不是關注“標簽”。按事給資源配置,按能力和實際貢獻給報酬,權利義務平衡。我們現(xiàn)在選任干部就存在權利義務脫節(jié)的現(xiàn)象。“榮譽性,錦上添花性”的項目盡可能少一些,有也盡可能民間性一些。時間會證明和改變一切。老子講:“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還是有些道理的。
最后,領軍人才是關鍵。這種領軍人才屬于資源配置型人才,也是“非常稀缺”的人才,他們決定著市場,決定著地方的繁榮安康。問題在于這種稀缺人才哪里來?如何發(fā)現(xiàn)?如何獲取?什么標準?中國人講:“得人才者得天下”。毫無疑問,地方行政首長,那個說話算數(shù)的首長,如果不是領軍人才,那個地方就發(fā)展不好。尤其是在中國國情下。“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這句話非常深刻!企業(yè)家也是領軍人才!“一百個人里找出一兩個專家不易,但一千個人里找出善經(jīng)營的好專家很難”!這樣的領軍人才,我們更關注的不應是他的“名頭”而是他的精神,作為企業(yè)家,是否具有企業(yè)家精神?作為科學家,是否有科學精神?作為政治家,是否有政治家的偉大抱負和情懷?這些都不僅僅是“哈佛博士”“院士”“局長”這些“名頭”可以衡量的。你也可以說這樣的人很少,是稀缺資源,你也可以說這樣的人很多。“這個世界缺少的不是美,而是發(fā)現(xiàn)美的眼睛”。人才學有個規(guī)律就是人才的群體效應。你會發(fā)現(xiàn),那些發(fā)展很快,人才集聚的地方往往是“人杰地靈”“人才輩出”的地方,而那些閃耀的“明星”,其實,看起來跟普通人也沒有什么“太大的差別”——他們也是“人”,天時、地利、人和而已。好的時代就是造就群星燦爛的時代,好的地方就是人才輩出的地方。
(作者系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企業(yè)人事管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廣西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