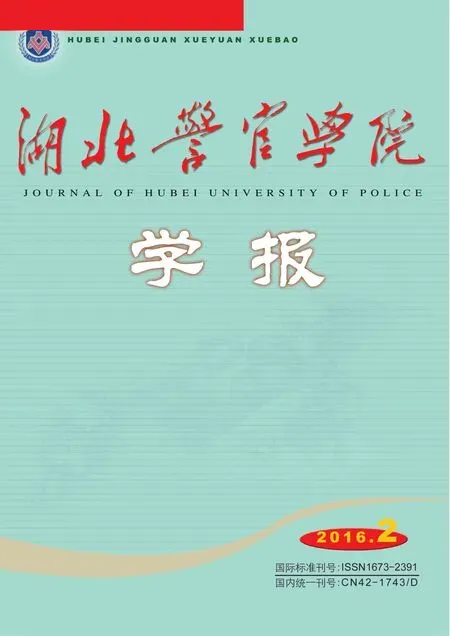試論集群犯罪的條件控制
董士曇
(山東警察學院,山東 濟南250014)
試論集群犯罪的條件控制
董士曇
(山東警察學院,山東 濟南250014)
集群犯罪與集群行為或群體性事件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并非等同。雖然集群行為中包含著集群犯罪形態,合法集群行為亦具有很大的潛在危險性,常常因為失控而轉化為集群犯罪,但這僅僅是一種可能性而非必然性。集群犯罪的發生不是簡單的感應式因果關系,在集群犯罪的因果鏈條上,還有一個重要變量因素——犯罪條件。從某種意義上說,控制了犯罪條件,犯罪結果就不會發生。在當前社會沖突加劇、集群犯罪的成因難以短期根除的背景下,將防控集群犯罪的視角由犯罪原因轉向犯罪條件,從“群體情緒”、謠言傳播、“重點人物”、“受害人”、突發因素以及“處置因素”等這些關鍵條件因素入手,打破集群犯罪的結構,阻斷集群犯罪的成因與犯罪結果之間的聯系,對于控制集群行為的惡性轉化、遏制集群犯罪的發生和維護社會穩定等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集群行為;群體性事件;集群犯罪;犯罪條件;犯罪控制
經過多年探討,學界和實務界對我國社會近20年來多發的集群行為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對其形成、發生、演變的機理以及處置措施亦達成了一定的共識。但隨著我國社會改革的逐步深入、各種利益關系的重新調整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變化等,導致社會沖突加劇的客觀原因在短期內難以消除。因社會矛盾、群體沖突引發的集群犯罪在今后一個較長時期內仍會在高位運行,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在這種情況下,轉變思維方式,另辟蹊徑,嘗試從控制犯罪條件入手,解構集群行為惡性發展的方法,或許是當下減少集群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的一條有效路徑,其作用和現實意義顯而易見。需要強調的是,犯罪學中的犯罪條件理論不是從消除犯罪原因方面解決犯罪問題,而是著眼于犯罪的情景因素,通過控制犯罪發生的條件,切斷犯罪原因與犯罪結果之間的聯系,遏制犯罪的發生。因此,本文研究的重點不是研究集群犯罪的成因,而是在解析集群犯罪結構的基礎上,通過控制犯罪條件來解構集群犯罪的生成機制。
一、集群行為、群體性事件以及集群犯罪概念之界分
鑒于目前學界和實務部門對集群行為、群體性事件、集群犯罪等概念存在的認識偏差,并由此導致在實踐中出現的一些非理性行為,因此有必要對有關概念的內涵及其性質作出科學的界定。
集群行為或“集聚行為”、“集體行動”是一個域外概念,西方學者往往從社會學或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對其特征進行描述或現象分析,強調參與集群的“群體心理”、“集體意識”、“集體認同”,強調集群行為的自發性、無組織性、不穩定性等;認為它是“自發產生的,相對來說是沒有組織的,甚至是不可預測的,它有賴于參與者的相互刺激”。[1]可見,在西方語境中,集群行為不是一個完全否定性詞語,而是一個中性詞。目前,類似的行為在我國學界特別是實務部門被稱之為“群體性事件”,其實這兩個概念應當具有大致相同的內涵與外延。但從“群體性事件”這一概念的演變過程 和我國學者給出的定義[2][3][4]以及政府文件關于處置群體性事件的規定 中皆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都突出強調了群體性事件的破壞性和對社會的不良影響,隱含著群體性事件的違法性。[5]盡管經過多年的研究與處置實踐,人們對群體性事件的認識不斷深化,處置方式和手段也越來越趨于人性化和規范化,但在社會維穩壓力和人們的慣性思維影響下,不論學界還是實務部門,對群體性事件仍有不少人不加區分地持有明顯的否定性評價。這里有必要予以澄清。
現代漢語詞典中的“事件”是一個中性詞,“是指歷史上或社會上發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6]而在之前加入“群體性”限定詞后,“群體性事件”被賦予了特定的內涵,其行為可區分為:符合法律規定的游行、集會、靜坐、請愿、示威等合法集群行為;可容忍的越軌行為;為法律所否定的打、砸、搶、燒等集群犯罪行為。可見,集群犯罪作為集群行為或群體性事件的下位概念,其外延只包含上述打、砸、搶、燒等違法犯罪行為,系指“參與人數眾多、違反社會法律規范、由眾多人的狂熱行為而導致的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7]雖然不可否認群體性事件中包含著集群犯罪的形態,合法的集群行為或群體性事件亦具有很大的潛在危險性,常常因為失控而轉化為集群犯罪,但這僅僅是一種可能性而非現實性,二者是不能畫等號的。合法的群體性事件能否最終演化為集群犯罪,不僅取決于群體沖突的烈度,還取決于政府及其執法部門應對危機的能力等多種催化因素。其實,大多數群體性事件皆起因于弱勢群體基于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這種群體性抗爭對推動政府改革不合理的社會政策,提高管理水平,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或許是有益的,它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推動了社會的改革與進步。比如“漢源事件”就促成了我國不合理征地補償問題的解決,“烏坎事件”促進了土地使用和選舉的規范化。[8]
因此,將任何形式的群體性事件都貼上“不良”或“違法”的標簽,甚至將其等同于集群犯罪而一概予以否定是非常錯誤和十分有害的。對群體性事件的這種“標簽化”偏見,一方面會嚴重誤導政府及其執法者對群體性事件性質的正確評價,進而不分青紅皂白地動用國家權力一味采取打壓等非理性的處置方式,加劇矛盾沖突,將一些合法性集群行為激化為集群犯罪;另一方面,將嚴重影響我們對群體性事件發生發展和變化的規律性認識,進而影響到有針對性地防控集群犯罪。
二、犯罪條件應用于集群犯罪的意義
犯罪原因系統論認為,犯罪原因是由相互作用的若干致罪因素所構成的具有引發、促成犯罪產生、存在和發展變化的有機聯系的體系。犯罪系統內部存在的若干相互聯系的因素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有的起原因作用,有的起條件作用,有的起相關作用,但其中的任何一個單項因素都不能獨立地引發犯罪,這些因素只有有機結合在一起時才能導致犯罪的發生。其中,犯罪原因(直接原因或狹義犯罪原因)是犯罪得以發生的直接動因和根據,在犯罪原因系統中處于核心地位;任何犯罪的發生都離不開具體的犯罪原因,沒有具體的犯罪原因,犯罪就不可能發生。犯罪原因包括犯罪產生的社會原因和犯罪產生的個體原因,前者是指對犯罪產生有重要影響的各種社會因素,主要包括誘發犯罪產生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法制、人口、社會管理和人文自然環境因素等;后者是指犯罪人本身存在的足以引起、促成和影響犯罪結果出現的各種因素,主要包括犯罪人的意識因素、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等。犯罪原因的形成是主客觀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犯罪條件是犯罪動機外化為犯罪行為所借以利用或必須利用的外在因素,它雖然不能直接引發犯罪,但卻能對犯罪的發生起著促進、加速、保證和便利的作用,是犯罪原因系統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在犯罪動機、犯罪意識沒有外化為犯罪行為之前,如果缺少一定的外部條件,犯罪原因就只能停留在動因狀態,無法轉化為犯罪行為,成為犯罪事實;而有了犯罪條件,犯罪動因便會借助它造成犯罪事實,鑄成犯罪結果。犯罪的相關因素是指對犯罪結果的產生具有一定聯系和直接作用的因素,如與犯罪結果相關的時空因素、地理環境因素、季節氣候的變換因素等。這些因素雖然只是造成犯罪的一種可能性,在犯罪原因系統中的作用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必要的,有它,犯罪發生更便利,無它,犯罪也會照樣發生,但它作為犯罪的外部環境因素,與犯罪條件一樣都與犯罪結果相聯系,皆有助于犯罪的實施。
將犯罪條件應用于集群犯罪研究,是基于“犯罪系統論”立場揭示集群犯罪發生的過程并加以控制的一種方法,對于解構集群犯罪的結構,切斷集群犯罪的成因與犯罪結果之間的聯系,控制集群行為的惡性轉化和減少集群犯罪的發生皆具有極大的作用和應用前景。[9]
首先,從犯罪的因果關系看,犯罪作為一種社會失范行為不同于自然界中一定的原因必然出現一定的結果。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都是一些自發的、盲目的和難以控制的自然力量,因果聯系的必然性表現得十分充分;而社會中所發生的一切現象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人的主觀意識、目的性的制約與影響。正是人的這種高度自覺性、能動性決定了即使具備了犯罪的所有成因,犯罪行為也未必就會發生。在犯罪原因結構體系中,犯罪原因和犯罪結果之間還交織著一些復雜的中介因素,我們將這些因素稱之為犯罪條件。控制了犯罪條件,犯罪就難以發生,甚至可以按照我們的意志促使即將爆發的犯罪向著良性方向轉化,從而達到控制犯罪的目的。
其次,從犯罪發生、發展的規律看,社會的復雜性決定了人類所追求的價值目標之間存在著一些難以克服的矛盾與沖突。比如,為了社會的進步,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經濟,而商品經濟的發展無疑會刺激人們對金錢的欲望,從而成為一些財產犯罪或經濟犯罪的誘發因素;同時,發展商品經濟又會帶來社會人、財、物的大流動,這又增加了犯罪控制的難度。正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存在的這種悖論,決定了消除犯罪的社會原因的長期性與艱巨性。此外,變革社會,消除社會矛盾,改變落后的生產方式和管理方式,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充滿了各種風險和變數,搞不好還可能引起社會的動蕩與混亂,制造出更多的犯罪。比較而言,從犯罪條件方面控制犯罪的發生,不需要從根本上變革社會關系,實施起來要簡單得多,盡管它不是治本之策,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犯罪的原因,但卻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應然性選擇。
再次,從當前的犯罪形勢看,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矛盾、社會沖突多發的社會轉型期,這一時期恐怕還要持續較長一段時間,因而誘發集群犯罪的各種社會因素短期內難以消除,控制集群犯罪的心理因素更不具有可行性。為了維護社會穩定,防止出現大的社會動蕩,保持經濟社會發展所必要的治安秩序,實施以消除集群犯罪條件為策略的治標措施不失為一種明智選擇。其最大價值就在于,它能夠最大限度地控制大量可防性犯罪——遏制集群行為的惡性轉化,減輕目前嚴峻的社會治安局勢所帶來的巨大政治壓力,保障社會基本穩定。
三、集群犯罪的結構
集群犯罪結構復雜,并非簡單的“原因→結果”關系。在集群犯罪的因果鏈條上,既有集群犯罪的上位因素——集群行為,又有集群行為轉化為集群犯罪的變量因素——犯罪條件;既有合法的集群行為,又有一般違法行為和嚴重暴力犯罪行為;參與者中既有眾多的利益相關人,又有大量的不明真相者,還有混跡其中的違法犯罪分子;而且犯罪現場混亂復雜,群情亢奮,充斥著各種流言和暴力,場面極難控制。面對體系內如此盤根錯節的復雜關系,實難做到全面分析,這里僅擇其要點述之,盡可能勾勒出一個大致的面貌。
(一)致罪因素
所謂致罪因素主要是指促使個體形成群體及其犯罪心理的外在社會因素。就我國目前來看,導致集群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很多,但其根本原因是經濟利益分配的不平等,這從我國集群行為多起因于經濟利益沖突的事實可以得到充分的說明。馬克思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無不同他們的利益有關。”[10]誠然,中國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并沒有達到每個人的心理預期,期望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使人們產生了強烈的相對剝奪感;長期的利益分配不均衡導致的失業、貧困等問題,加劇了人們的挫敗感;現行政策、體制的弊端致使貧富懸殊不斷拉大,社會不斷分化,一些社會邊緣群體逐漸被固化,處境艱難,近乎絕望;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激烈競爭所帶來的巨大心理壓力,引發了社會下層人員普遍的緊張狀態;嚴重的權力腐敗給社會帶來的負面情緒,削弱了公眾對政治體系的心理認同……這些淤積的挫敗感和利益沖突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而導致的過多積怨,是導致集群犯罪頻發的重要社會根源。從眾多集群犯罪的案例中也可以看到,參與者中有的是對下崗、失業、生活水準降低心存芥蒂,有的是因為看病難、高房價、環境污染而郁郁寡歡,有的對拆遷、征地、貧富懸殊忿忿不平,也有的“仇官”、“仇富”、痛恨不公,當然也有少數人因為被抓、被罰、被處分而懷恨在心……諸如這些怨恨與不滿情緒,累積疊加到一定程度,在沒有適當的管道發泄時,就可能在一定的共同心理認知驅使下,遵循“挫折-攻擊”的理論假說釋放出來。這就不難理解,那些非利益相關人員為何要冒著風險參與集群犯罪以及近年來多發的沒有具體犯罪指向的針對社會犯罪的原因了。
(二)群體
一定數量人員的群體形成是集群犯罪發生的主體因素和必要條件。集群犯罪既不同于個體犯罪,也有別于有意識地結成團伙所實施的共同犯罪形態。集群犯罪沒有明確的犯罪目的性、組織性和預謀性,其起因多被解釋為“利益訴求”、“集體抗爭”、“官民沖突”、“公共事件”等。但在大致相同的社會環境條件下,為什么只有極少數人參與到集群行為之中?這些“烏合之眾”又是如何聚合成群體的?社會認同理論認為,群體現象與社會認同密切相關。因為個體會自動地將人進行分類,明確自己所屬的群體,并以所屬群體身份定義自我。個體對群體的覺知、對群體的心理歸屬感及對群體共享價值信念的肯定都是群體認同的構成要素。[11]一般而言,個體對內群體的認同度越高,就越顧忌來自群體的壓力,更加傾向于以群體成員的身份行動,并排斥異己群體,從而將群體整合為高效的行動統一體。當然,高群體認同與集群行為并非絕對正相關,個體對群體身份的認同隨著情景的變化而變化,參與的程度還受到“得失損益計算”和“群體效能”的影響。
但是,個體一旦參與到群體之中,在匿名、模仿、感染、暗示、順從等心理機制的作用下,就會失去理性和責任感,[12]不明真相的群眾也極易受到群體沖動情緒的感染而加入其中,整個群體由此演變為躍躍欲試的危險群體。此時,如果稍有不慎或處置失當,在突發因素的刺激下,場面就會失控,集群犯罪一觸即發。
(三)犯罪條件
這里所謂的犯罪條件,是指集群犯罪發生所借以利用或必須利用的由合法集群行為轉化為集群犯罪的外在因素。同其他犯罪一樣,集群犯罪絕非空穴來風,毫無征兆,其明顯經歷了一個情緒積累、發酵、爆發的過程,[13]一般情況下會沿著“集群→集群行為(合法)→集群犯罪”的軌跡演變。犯罪條件就是合法集群行為達至集群犯罪的橋梁和中介,是合法集群行為向集群犯罪惡性轉化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些因素主要包括:
1.群體情緒。群體情緒是指參與集群的無數個體基于群體成員的身份而產生的情緒反應氛圍。極端的群體情緒營造了集群犯罪的“情景”,是爆發集群犯罪不可或缺的重要變量因素。
2.謠言。謠言是人群中傳播的不符合事實或沒有根據的傳聞。在集群情景中,謠言的傳播不僅使原本松散的集群變得更具凝聚力,還可能成為集群行為發生惡逆變的助推劑。
3.處置失當。在集群行為的萌生、醞釀、發展還未激化為集群犯罪的階段,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的適時回應、及時應對和規范化處置是化解集群沖突、避免集群犯罪爆發的關鍵。面對群體訴求和處于激情狀態下的群體人員,當地政府部門反應遲鈍、有意回避、辦事拖沓或一味地強硬打壓;執法人員的疏忽大意、戒備不足、草率敷衍、違規用法、濫施暴力等,都會成為激化矛盾、釀成集群犯罪的誘發因素。如果仔細梳理近20年來我國發生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便不難發現,每起集群犯罪事件的發生無不與政府及其執法部門的處置失當有關。在這里,犯罪條件與犯罪原因之間的相互轉換關系表現得十分明顯,即作為處置集群行為外在條件因素的方法與手段,因為運用不當而轉化為集群犯罪的原因。
4.突發性因素。集群犯罪中的突發性因素多種多樣而且非常直觀,往往是一些偶然的“戲劇性事件”,一句謠言、一句粗話、一個推搡性動作、一件不起眼的小事等都可能成為引發集群犯罪的導火索。如足球比賽中球員的一個烏龍球,就可能引起暴力性騷亂事件;群體中“領袖”的一個眼神或手勢,也可能成為集群犯罪的引擎,點燃圍攻、毆打執法人員的集群犯罪事件。可見,控制這類條件因素盡管難度很大,但卻有著重要的實踐意義。
(四)相關因素
集群犯罪的相關因素與條件因素一樣都是集群犯罪的外在因素,對集群犯罪的發生皆有促進和影響作用。因此,我們也可以將犯罪的相關因素看作是廣義的犯罪條件,了解其性質和特征對控制集群犯罪有重要幫助。研究表明,不同的季節、時間、氣候以及地理環境條件等,與犯罪的種類、數量、性質有極大的關聯性。性犯罪、暴力犯罪之所以多發生在夏季,就是因為其深受季節因素的影響。而集群犯罪的暴力性特征,決定了它與季節因素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如,集群犯罪中的“群體情緒”、“突發性因素”、“暴力”等都容易被夏日炎炎的氣溫所點燃。
綜上所述,在社會因素(外因)和個體因素(內因)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一定規模的群體。集群犯罪的原因形成,犯罪結果未必就會發生,此時,犯罪成因與犯罪結果之間只是具備了高度的蓋然性而非必然性。犯罪成因只有與犯罪條件這個中間變量相結合,發生“化學式”反應,才能轉化為犯罪結果,導致集群犯罪的發生。
四、控制集群犯罪條件的基本策略
集群犯罪是一種復雜的犯罪形態,其發生發展直至終結涉及眾多的部門和人員。在該類犯罪多發的情勢下,地方各級政府應當高度重視,切實加強對本地維穩辦的實體領導,結合本地區的實際,加強研究和人員培訓,掌握集群犯罪的規律特征,形成一套切實可行的維穩處突工作模式,這是控制集群犯罪條件的組織保障。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建立輿情監測系統,消解“群體情緒”
實踐證明,在集群犯罪處于臨界點時,“去個性化”加劇,個體處于一種非理性狀態,在傳染、模仿機制的作用下,“群體情緒”被點燃,表現為亢奮、過激狀態,此時再試圖進行控制幾無可能。因此,要有效控制“群體情緒”,必須建立社會輿情監測系統,收集集群行為的相關信息,進行早期疏導與控制。
一是建立基層民情社情跟蹤測量常規化機制。應設立以村、社區、街道為單位的基層民情社情測驗機構,并由該單位的一把手擔任機構負責人,采取有償服務的方式,規定其工作職責,明確民情、社情和各種矛盾信息的收集范圍,落實責任制,對民情社情動態實時進行跟蹤調查;對收集到的各種相關信息要及時處理上報,不得拖延、遺漏;對因為工作失誤造成嚴重后果的要追究負責人的責任。各地維穩辦對基層反饋的民情社情檢測信息,應及時進行研判,一旦發現有不穩定因素或出現集群行為的苗頭,要及時會同基層直管部門作出應對之策,將“群體情緒”消解在萌芽狀態。
二是建立關于“重要事項”的評估工作機制。這里所謂的“重要事項”是指涉及諸如土地征用、房屋拆遷、涉法涉訴、企業改制、生態環境、生產安全、食品安全等與廣大人民群眾的權益密切相關的、極易引起糾紛沖突的情況與項目。對這些敏感事項如果決策不當、考慮不周,極易激起民怨,引發集群犯罪事件。典型的如廈門“PX事件”、上海“磁懸浮事件”、廣東番禺“垃圾焚燒廠選址事件”、浙江“海寧事件”、四川“什邡事件”等都經歷了一個較長的輿情發酵過程。這些事件之所以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而發生惡逆變,主要原因是政府有關部門對事件缺乏應有的重視,從中也暴露出了輿情、情報收集及預警、處置機制的缺失。[14]因此,對涉及公民切身權益的“重要事項”的決策,政府應當高度重視并吸納民眾參與;必須充分論證,體察民意關切,制定關于“重要事項”的評估機制和民意收集、研判機制,以防控“群體情緒”的積聚和發展。
三是關注網上輿情。互聯網時代,網絡成為了民眾不滿情緒宣泄的重要平臺,網絡的匿名性特征,使得“群體情緒”在網絡上表現得淋漓盡致。這為我們了解、掌控和消解“群體情緒”提供了可行性手段。在“什邡事件”中,有關對項目污染的質疑、反對項目建設的呼聲在2012年3月起網上就有所反映,之后逐步傳播,形成熱點。隨著項目開工典禮的舉行,網上情緒宣泄、語言攻擊短期內達到了高潮,網上串聯活動、組織聚集上訪已成公開之勢,但直至7月2日事件爆發,當地政府部門仍未給予重視,錯失了消解“群體情緒”爆發的最佳時機。因此,必須將網絡輿情納入輿情收集監管范圍,建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網絡輿情監控體系,切實提高網絡輿情收集能力,第一時間把握社情、民情動態。[15]
(二)及時揭露真相,控制謠言傳播
在集群犯罪事件中,通常都伴隨著謠言的傳播,如無權威機構及時予以澄清,謠言就會迅速擴散,激化輿論,加劇集群犯罪的爆發。謠言是一種神秘的力量,它具有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能量。特別是在不確定的集群情景中,不論是造謠者還是傳謠者,都會根據自己的需要理解它、加工它、傳播它。在謠言的蠱惑下,參與者的焦慮感降低,形成共同利益,本來松散的群體因此變得更具凝聚力。在集群犯罪中,謠言傳播的客觀原因是政府公信力下降,直接原因則是政府信息公開機制缺位。[16]因此,要有效控制謠言的傳播,必須建立政府信息公開機制,使政府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不僅需要政治智慧,還需要下大力氣轉變政府的工作作風,扭轉時下盛行的“說空話、說假話,臺上一套、臺下一套”的不良官場風氣,這是提高政府公信力、防止謠言出現和傳播的根本措施。同時,在謠言出現時,應及時揭露真相,占領輿論制高點,以權威的聲音戳穿謠言的本質,避免因謠言的傳播而形成輿論危機。因為沒有真相,謠言就成了真相;有了真相,謠言就會自動消失。
(三)提高自身素質,加強“自我控制”
所謂“自我控制”即是政府及執法人員在應對集群行為時對自身言行與處置方式、方法的自覺約束。現實中發生的集群犯罪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為處置不當導致沖突加劇釀成的。經過多年的摸索和總結,雖然目前處置集群犯罪的水平有了較大提高,地方各級政府及執法部門逐漸形成了一套應急處置模式,但由于集群犯罪的復雜性、現場情勢的多變性以及執法人員素質的差異性,使得任何一起看似平常的集群事件都充滿了極大的風險與變數。要有效規避這些風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首先,應加強對有關人員特別是領導、指揮者的業務培訓,防止走過場,使其真正掌握應對集群犯罪時必備的把握政策的能力、談判溝通能力以及具體的業務知識能力等。
其次,應堅持依法處置原則、有錯必改原則、慎用警力及合理用警原則。依法處置集群行為是法治化國家的應有之義,應區分不同情況,在集群行為的不同階段、針對不同人員采取不同的措施。對一般參與人員應主要采取說服疏導的方式;對觸犯法律或別有用心、渾水摸魚、以犯罪為目的的不法分子,應給予嚴厲制裁,決不姑息,以維護法律的尊嚴;對因為政府決策不當或有一定過錯損害了公眾的利益所導致的集群事件,政府及有關部門應適時予以糾正,以化解矛盾、消弭沖突,變被動為主動,促使問題妥善解決。集群行為多屬于人民內部矛盾,能不用警力最好不用警力,以規避因“自我標簽效應”而產生的逆反對抗心理;在不得已使用警力的情況下,也要把握好分寸,避免濫施暴力,激化矛盾,釀成悲劇。
再次,執法人員應按照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行事,做到言語文明規范、行為謙抑節制、執法有理有據。總之,一切應有利于問題的解決,必要時還要忍辱負重。
(四)仔細篩選,強化對重點人物的監控
這里所說的重點人物主要是指在集群犯罪中發揮“領袖”作用的骨干人員,主要包括:曾經串聯、煽動、組織策劃過群體性事件的骨干人員;不穩定群體中被視為能代表其利益的帶頭人員;在曾經發生過的群體性事件中書寫傳單、張貼標語、懸掛條幅、散布謠言的人員;極力插手群體性事件別有用心的人員;揚言報復企業和社會的人員;組織建立或參與所謂代表不穩定群體、非法組織的人員;有可能參與策劃、幕后指揮、插手群體性事件制造事端的危險人員等。[17]盡管集群犯罪的群體是一幫“烏合之眾”,沒有明確的組織性,但幾乎從所有的集群犯罪案例中都可以看到這類重點人物的影子。這些重點人物在集群事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一個動作甚至一個眼神都可能成為群體瘋狂模仿的風向標,從而將其意志輕而易舉地轉化為群體的意志,并外化為群體的一致行動。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控制住重點人物就等于拔掉了集群犯罪的引信,對降低集群犯罪的幾率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雖然在群情激憤、混亂不堪的集群事件中,及時分辨和發現這類重點人物非常困難,但只要科學分析,運用方法得當,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下面就如何發現重點人物進行分類論述。
一是根據其社會關系的密疏程度進行篩選。一般來說,擁有廣泛社會關系的人在群體內部具有較強的交際能力,其所發出的暗示能夠在群體中迅速加以傳播,其言行也是群體成員模仿的主要對象,其意志也最容易轉化發展為群體的意志。所以,篩選重點人物應重點分析群體內部是否形成利益團體,以及該團體成員中誰的人脈關系最為廣泛。
二是根據社會聲望進行分辨。權威、聲望高的人在集群行為中具有一般人所不具有的影響力、號召力和動員力,是群體成員心目中的自然領袖和主心骨。分辨這類重點人物,應將那些交往能力強、經歷豐富、為人義氣、愛打抱不平、學識淵博、經濟條件較好的人作為重點考察對象。
三是根據言行舉止確認。法國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群體心理學的創始人古斯塔夫·勒龐認為,“只有最極端的人,才能成為領袖。”[18]這里的領袖,就是集群犯罪中的重點人物。實際情況正是如此,在我國所發生的集群犯罪中,多數都有黑惡勢力或極端分子不同程度的參與。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只有具備了極端意識、形成反社會人格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機會,伺機而動,制造事端;而集群情景無疑為極端分子提供了天賜良機。根據言行舉止確認重點人物,可重點監視和控制以下幾類人員:謠言制造者及惡意傳播者,煽風點火者,思想激進、反動者,上躥下跳、積極串聯者,行為詭異、情緒反常者等。
此外,識別、發現和確認重點人物,應充分發揮輿情監測系統的作用,將監測到的重點人物的信息與上述識別方法有機結合起來,進行綜合分析和判斷,并根據重點人物的具體情況采取相應的管控措施。
(五)做好“受害人”的疏導、善后工作
這里所說的“受害人”系指與集群行為的發生有直接利害關系且權益受到損害的自然人。該類受害人,可能是實際受害人,也可能是潛在受害人,還有可能是虛擬受害人。目前我國發生的一些集群行為,不少是由于個體與政府執法部門或強勢利益集團的沖突激化所致,而作為弱勢群體的受害人,通常會受到公眾和本群體成員的同情與支持。在受害人不理智的行為和情緒感染下,往往會引發集群行為,如果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還可能激化為集群犯罪。例如,2008年6月發生在貴州省的“甕安事件”,起因是一名女學生溺水身亡,甕安縣公安局調查后作出鑒定,排除了他殺的可能性。但死者家屬 不肯接受鑒定結論,之后由于家屬的憤怒所導致的不滿情緒迅速在當地彌漫、擴散,事態急劇惡化,最終演變成打、砸、搶、燒政府機關的集群犯罪事件。因此,在有具體受害人的集群事件中,應高度重視受害人的致害作用。政府等有關部門應認真做好對受害人及其家屬的疏導工作,積極回應受害人的“關切”,善后工作要及時到位,以防止被害人因情緒過激做出失去理智的行為,從而成為點燃集群犯罪的導火索。
【注釋】
50-70年代),之后被表述為“治安案件”、“群眾性治安案件”(20世紀80年代)、“突發事件”、“治安突發事件”、“治安緊急事件”、“突發性治安事件”、“緊急治安事件”、“群體性治安事件”(20世紀80年代末至21世紀初),2004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關于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理群體性事件的工作意見》中使用了“群體性事件”。該概念一直沿用至今。群體性事件概念的演化反應了對群體性事件認識的不斷深化,即由原來的對其定位于“群眾鬧事”而予以堅決打擊和取締,發展到后來認為其由各種社會矛盾糾紛引發應依法妥善處置。但實踐中,有些地方政府仍將集群行為或群體性事件與集群犯罪混為一談,或出于維穩需要,或為了其他目的,簡單、粗暴地對待群體性事件,甚至予以打壓。
[1][5][12][15]王慶功,張宗亮.社會沖突與集群行為[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5:31,44,138-139,189.
[2]馮琳.淺析當前群體性事件的誘發因素及預防處置對策[J].上海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3).
[3]周寶鋼.社會轉型期群體性事件預防、處置工作方略[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37.
[4]中國管理學會課題組.我國轉型期群體性突發事件主要特點、原因及政府對策研究[J].中國行政管理,2002:950.
[6]現代漢語詞典[C].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115.
[7][17]趙輝,江帆.集群犯罪形成機制初探[J].河北法學,2015(2).
[8][16]陳聞高.群體性事件的輿論危機及其引導[J].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15(4).
[9]徐大慰.國外城市犯罪空間理論綜述[J].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15 (5).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2.
[11]殷融,張菲菲.群體認同在集群行為中的作用機制[J].心理科學進展,2015(9)..
[13][14]繆金祥.環境群體性事件治理研究[J].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14(6).
[18][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M].戴光年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8.
【責任編校:譚明華】
Discussion on Conditional Control of Colony Crime

(Shandong Police College,Jinan 250014,China)
There are rela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a colony crime,a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a group incident.Although collective behaviors contain the form of colony crimes and legal collective behaviors also have huge potential risks to be transformed into colony crimes without control,yet it is only possible instead of inevitable.The emergence of colony crimes ia not a simple inductive causality.There is an important variable factor,the crime condition,in the causal chain of colony crimes.In some sense,the criminal consequence would not occur as long as crime conditions have been controll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nsifying social conflicts and irrevocable reasons of colony crime in a short time,it has undoubted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ontrolling vicious transformation of collective behaviors,containing the emergence of colony crimes and safeguarding the social stability that we turn our perspective of colony crim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rom criminal causes to crime conditions,startwith some keyelements such as"the groupemotion","the rumor spread","the key figure","the victim",the unexpected factor and"the disposal factor",break the structure of colony crimes and block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easons and results of colony crimes.
collective behavior;group incident;colony crime;crime condition;crime control
D631
A
1673―2391(2016)02―0049―07
2016-03-12
董士曇(1962—),男,山東定陶人,山東警察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犯罪學。
2015年山東省法學會重點課題“創新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的理論與實踐”(SLS[2015]E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