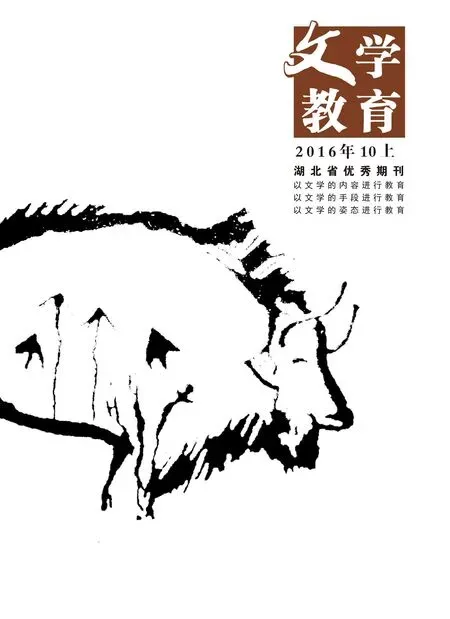新聞一束
新聞一束

●郝景芳憑科幻小說《北京折疊》獲雨果獎
郝景芳《北京折疊》日前獲得2016年雨果獎最佳中短篇小說獎,這一獎項頒給7500字至1.75萬字間的作品。據介紹,郝景芳在《北京折疊》中構建了一個不同空間、不同階層的北京,可像“變形金剛般折疊起來的城市”,卻又“具有更為冷峻的現實感”。故事多源自她自己的生活日常,記敘現實的人情悲暖。《北京折疊》的英文版譯者是科幻作家兼翻譯劉宇昆,他也是《三體》英文版譯者,這是他翻譯的作品第二次獲得雨果獎。中國第一位雨果獎得主、科幻作家劉慈欣此前曾對媒體表示“中國科幻仍處于不太成熟的階段”,不過值得安慰的是,近年來一批“后新生代”科幻作家異軍突起,他們不斷地在想象力、實驗性、思想性上進行突破,努力嘗試并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為紀念20世紀世界著名科幻作家雨果·根斯巴克,世界科幻協會設立了雨果獎。在世界科幻界,雨果獎和美國科幻奇幻作家協會設立的星云獎被認為是最具權威性和影響力的兩項世界性科幻大獎。
●張愛玲遺稿《愛憎表》曲折講述自己過往
據臺灣旺報報道,張愛玲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指出,最新近公開的張愛玲“遺作”,要屬她自己剖析學生時代想法的《愛憎表》。此文的重構過程,日前在“張愛玲誕辰95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上首次發表,全文并于臺灣《印刻文學生活志》率先刊登,為兩岸三地首見。張愛玲身后,其實每隔一段時間,就有所謂的張愛玲“遺作”問世。作為張愛玲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很感慨,自己是統計學背景出身,要不是父母宋淇、鄺文美,他自己從沒想過有天要成為她的遺產守護者,而他所能做的,就是在不違背張愛玲意愿的前題下,整理她所留下的一切,還原更真實的張愛玲。原本宋以朗并不打算讓《愛憎表》發表,“手稿字跡模糊難辨且雜亂難以整理”,坦言自己也不怎么懂得欣賞張愛玲,實難單憑一己之力進行;而后在香港文學評論者馮晞干的協助下,從眾多支離零碎的手稿中重構其貌。而其中最費時的工作在于將張愛玲的字跡逐一辨讀后,一字一句搬入計算機。張愛玲最早提及《愛憎表》是1990年寫給宋淇夫婦的信上,提到1937年高中畢業時在校刊填過一個調查,其中她填下“最怕:死;最恨:有天才的女人太早結婚;最喜歡:愛德華八世;最喜歡吃:叉燒炒飯”故而她名為“愛憎表”。但即使是她自己,“隔了半世紀看來,十分突兀”甚至完全陌生,需要解釋,于是她花了約2個月的時間寫〈愛憎表〉但陸續擱下,始終沒有寫完。馮晞干指出,張愛玲《愛憎表》如《小團圓》,迂回曲折地講自己的過去,除張氏回環往復式寫法的文學性值得一探,另有其傳記價值;相較于自傳性小說,此文更為直述,可借以理解張愛玲的小說及其切身經歷的關連。
●第四次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在長春舉行
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吉林省作家協會承辦的第四次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日前在吉林省長春拉開帷幕。鐵凝在致辭中說,中國作家協會舉辦的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開始于2010年,近年來,中國作家的國際影響力逐步提升,這無疑是多方共同努力的結果。在持續的對話和交流中,漢學家和翻譯家們加深并擴展了對中國文學、中國文化乃至中國社會的認知與了解,讓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得以分享當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莫言在致辭中談了自己對中國文學翻譯的看法:“中國文學創作和翻譯都應在快速發展的社會節奏中慢下來。”他認為除了借助工具書解決語言問題之外,翻譯家還需要對翻譯對象也就是中國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有深刻的理解和體察,并與原著作者保持密切聯系。莫言強調,翻譯要忠實于原著和翻譯是創造性工作這兩種說法并不矛盾,經過作者本人同意,譯者可以對原作章節作適當調整。此次研討會的主題為:“與中國文學攜手同行”,國際漢學家和中國作家將圍繞“翻譯的權利與邊界”、“當代漢語的擴展變化及翻譯的新挑戰”、“可譯與不可譯——語際書寫的困惑”三個議題展開討論和交流,拓展文學翻譯的視野,提出有助于推動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翻譯和推介的新觀念。
●第二屆河南杜甫文學獎頒獎
第二屆河南杜甫文學獎(2012-2015)頒獎典禮日前在鄭州舉行。與首屆不同的是,本屆增加了小小說、網絡文學兩個單項獎。河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省文學院院長何弘表示,小小說和網絡文學是一種新型的文學體,作者群龐大,影響也非常大,文學界呼聲很高,所以作為單項列出。河南作為全國小小說的創作中心,推動了河南整體文學水平的提高,對擴大河南文學影響產生了積極作用。這次獲獎者以年輕作家為主,顯示了河南小說創作后繼有人的趨勢。劉峰暉(庚新)的作品《宋時行》獲得了網絡文學獎。他的小說大多都是以洛陽、開封為背景,他說:“這次得獎很意外但更多的是驚喜,是老師們對我們新增文學系列的作家們的認可,激勵我繼續用心寫作,更多地傳播河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