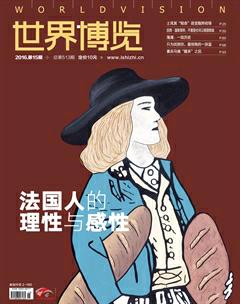“網紅醫生”都在做什么?
常芳菲
導語:7月19日,南京兒童醫院的一名護士在給3歲患兒做靜脈穿刺時,因為沒有一次成功,被患兒母親用Ipad砸中額頭,造成了長達1.5公分的傷口。事后患兒的母親因涉嫌尋釁滋事,被警方行政拘留。而這只是錯綜復雜的醫患矛盾中一個微小縮影。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最新發布的 《第3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數據,截至2015年底,我國互聯網醫療用戶規模為1.52億,占網民的22.1%。相比起其他類型的應用,互聯網醫療仍處于用戶習慣培養的階段。
隨著互聯網浪潮的興起和國家相關政策的,醫生多點執業已經成為趨勢。針對看病難、醫患間信息不對稱等行業痛點,涌現了一批民營醫院與醫生集團,比如優和維爾、美中宜和、于鶯醫療、張強醫生集團等等。然而在這個賽道中,所有選手似乎都還在試跑的階段,并沒有人占據絕對領先的優勢。
可以確定的是,醫生集團以其超輕的模式和專業化的團隊迅速打開了市場。而全科的門診和醫療平臺則是將目標客戶定位為中產階級的一次重要嘗試。在醫療改革的大背景下,曾經體制內的醫生們,開始實踐自己對醫療的理想。

移動醫療的前景和它的可操作性一樣,充滿了不確定的未知,這也正是這個行業最誘人的魅力所在。
“體制內”,留和走都是艱難的決定
2013年,擁有310萬粉絲的于鶯在微博上瀟灑地宣布:不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評判體系玩了。然后離開了供職十余年的協和醫院急診科。現在,她的身份是美中宜和門診中心的CEO,本月拿到聯想之星的投資后,將成立全科醫生集團“于鶯醫療”。
“醫生應該是服務行業。”女超人于鶯說。但現實非常骨感。每天早晨七點,各個三甲醫院的走廊上就擠滿了人。隨便推開任何一個診室的門,患者和家屬都里三層外三層的圍著醫生。醫生偶爾抬頭,不耐煩地催促他們出去,但大家完全沒有要離開的意思。好像守著醫生,自己被先看到的幾率就能更大些。
“門診醫生平均一個上午就要看40個病人。這時候你跟他們說,醫生其實是服務業,他怎么可能不拍著桌子罵娘呢。”于鶯說。除了工作強度大,三甲醫院負擔了許多基礎病、慢性病的治療工作,逐漸變成一臺負擔沉重,但必須高速運轉的機器。而醫生也疲于奔命,難以實現自己的臨床理想。
作為曾經的急診科主治醫生,于鶯坦陳,大家對急診醫生的想象是《實習醫生格蕾》,但長期住在急診室的,基本是癌癥晚期或者慢性病病人。“急診應該是搶救重大外傷患者或者心肌梗塞病人,總之是靠搶時間就能挽救生命的疾病。但協和急診住著的基本是老年肺炎這種慢性病。”作為住院總,于鶯不得不扮演“轟病人”的角色。“我也知道過不了幾天,病人還得回來,因為家里的護理條件不行,但我沒辦法。”
而如果徹底離開體制內自由執業,首先,患者都是認廟不認人。醫生難以憑借個人的品牌迅速獲取患者信任。顯然,患者在醫生個人與三甲醫院之間,還是更認可后者。“任何一個人看病都會說,我要掛三甲醫院的專家號。至于具體大夫是誰,到底對哪個領域更擅長,患者不care。”于鶯說。而正呈井噴之勢的分答、值乎給醫生提供了一個直接靠專業知識變現的機會。既讓醫生能夠直接接觸到潛在用戶,有可以將這部分用戶倒流到其他平臺。
但于鶯似乎并不滿意:“很多醫生分答定價(高)是不合理的。一分鐘的時間太短,不夠說清楚任何事情。”于鶯進一步解釋道,“而且分答不具備相同問題檢索功能,大部分人都提了同樣的問題,花了冤枉錢,所以現在我都去免費追問那里回答。”優和維爾聯合創始人桂瑤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醫患之間一定是要見面的,專家10分鐘都嫌沒有聊夠,1分鐘并不能解決任何實質性的問題。”
全科醫療平臺推“爆款”引流,但舉步維艱
既然走和留都不容易,多點執業作為一個折衷的方案,成為醫生的首選。基于這樣的需求,醫療平臺應運而生,他們與三甲醫院及專科醫生合作,開辦綜合性全科診所。優和維爾和南加醫療平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多點執業,俗稱“開飛刀”。醫生在公立醫院允許的前提下,與其他醫療機構簽訂協議,同時受聘于兩個及以上醫療單位的行為。目前,中央也在大力推廣多點執業的概念,希望以此來分流集中在三甲醫院的病人。為了快速獲取顧客,醫療平臺需要打造爆款。“跟開淘寶店一樣,你要推出一個利潤很低,甚至倒貼利潤的‘爆款來吸引顧客,然后再靠其他項目賺錢。”于鶯說。
而由于醫保無法覆蓋,全部項目都需要自費,所以醫療平臺的定位仍是中高端人群。優和維爾的全身體檢分為不同檔次,幾千元到上萬元不等。而南加醫療曾經的主推項目就是為中高端客戶提供私人醫生。
對于優和維爾來說,“爆款”是付費會員咨詢項目。他們利用自己專業的醫療知識和大醫院的資源,向會員推出付費咨詢業務,年費會員的定價將控制在1000元以下。“私人教練的價格都在200-300元,找健康咨詢師一年才這么多錢,對普通人來說也根本不算什么。”桂瑤判斷。她隨后又對我講了一個故事:一個顧客的父親一直覺得胸口疼,以為是老年心臟病,掛不上阜外醫院的專家號,就向優和維爾的專家咨詢。經過判斷,結論是腸梗阻。“我們就立刻安排他們住進協和醫院的國際部接受治療。”桂瑤說,“花這么點錢,治病就能少走很多彎路。”
而南加醫療平臺打造的“爆款”是企業員工健康咨詢項目。剛開始,南加力推的業務是為高端客戶提供私人醫生,但在推動的過程中,他們遭遇了重重困難。總經理李煉對我說:“我們認為一些實現了財務自由的人士確實有這種需求,但天花板確實太低了。”于是,南加開始了to B的服務。針對企業員工提供健康指導,開設企業診療室,無疑是可以快速打開市場的服務項目。“亞健康狀態在城市人群里非常普遍。”李煉說,“企業診療室不僅可以治療員工感冒發燒這類日常疾病,還有專業醫師對減肥、運動一些領域提供專業指導。”
即便優和維爾和南加醫療都在致力于推“爆款”吸引客戶,但全科診所的模式顯然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場地、儀器、專家每筆都是不小的支出。今年3月份剛剛拿到天使輪投資的優和維爾,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我們希望模式能輕一點,先把一部分護理的服務外包出去。”桂瑤說,“這筆投資起碼要帶來24個月的生存期。” 但24個月之后,資本市場能否轉暖仍是未知數。
基于這樣的現實,全科醫療離盈利還很遙遠。與美中宜和合作近三年的于鶯坦陳自己的診所剛好實現收支平衡,而普通民營醫院想要達到不賠錢的狀態基本需要5年。這似乎是一個需要慢慢來的行當,但“資本是嗜血的,是要增長的”。目前來看,它僅僅為白領階層沒時間看病的問題提供了一個性價比較高的解決方案。
醫生集團離錢更近,引進商業保險是必由之路
專科比全科賺錢,是目前行業內部的共識。“一個血管手術就可以定價38888,整個手術過程幾小時,從患者住院到出院也就3-4天。效率非常高”于鶯笑著說:“我干不了專科,我總不能說,你需要氣管插管兒嗎,我給你插一個。”比起于鶯,在專科領域里最具代表性的應該是張強醫生集團。張強創業2年,旗下擁有9個團隊,包括脊椎外科、血管外科、疝外科、整形外科、小兒外科、泌尿外科外科、頜面外科、肛腸外科。并且開創了醫生與醫院合作的模式,醫生團隊不拿醫院的工資,而是靠整個診療過程中的提成,實現收入的透明和合法化。團隊中的醫生全部自由執業,離開體制內。
盈利對張強來說不是問題。公開資料顯示,2015年,血管外科醫生集團的手術量超過1000臺,去年的收入已經達到千萬級別。其次,醫生集團的優勢在于模式“輕”,能夠實現標準化,并快速復制。拿到5000萬的首輪融資之后,張強沒有按照原先的設想那樣去建立一個大型的手術中心,而是選擇與其他線下醫院合作。張強認為,應該讓專業的人去做專業的事情。醫生的強項在于治病救人,而不是管理一個手術中心。
但同時,醫生集團也有風險點。首先,有意愿自由執業的醫生只是小部分,大部分的醫生仍然在觀望。比起大型的醫院,自由執業的前景不明朗。最早探索自由執業,并創立醫療團隊的萬峰,最終的選擇仍然時回到體制內。“為什么很多專家退休后都選擇被三甲醫院返聘呢,因為離開這個體制,你就不會有那種前呼后擁的感覺了。”于鶯說,“你可以看到那些已經成功的醫生所獲得的東西,所以真的走出去不容易。”
其次,病人數量的問題。于鶯認為,自由執業的醫生把自己經營成一個IP是必要的。“還是要下笨功夫,靠口碑讓患者產生信任感。這并不是能夠一蹴而就的。”于鶯說。而由于醫保無法分擔手術費用,只向中高端用戶提供服務是遠遠不夠的。那么,引進商業保險就成為了醫生集團做大的必由之路。獨角獸工作室創始人劉謙就曾判斷:商保占醫療開支5%以上,是互聯網醫療迎來春天的必備條件。張強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7月22日,他在朋友圈表示,張強醫生集團已與商業保險平臺達成了戰略合作。
而除掉全科醫療平臺和醫生集團之外,盡管國家也出臺了各類政策力推家庭醫生的概念,但從現狀來看,只會是少數人的選擇。“一個家庭醫生處理20個家庭已經工作量飽和了。” 桂瑤分析,“中國人口的基數決定了家庭醫生很難全部覆蓋。”而張強則認為,目前,優質的醫療資源仍然集中在三甲醫院里,無法下沉,同時沒有配套的讓優秀醫生下沉至家庭的鼓勵機制,所以家庭醫生的水平很難保證。
對醫療創業者而言,春天尚未開始,一切都還在處于概念很好的階段。但這些創業者仍然義無反顧地投身其中。除了順勢而為之外,他們提到最多的詞是理想。于鶯說:“協和畢業的人,都想靠臨床技術、循證醫學,幫助病人解決問題。如果要說理想,這是我的理想。”
我能從他們的眼睛里看到希望,他們是除了均衡收支外,心里還抱有理想主義的那些人,盡管他們不太提起。采訪開頭,于鶯急急忙忙趕來:我女兒放暑假,跟她交代一些事所以來遲了。現在,她已經把家都搬到診所上面,為了方便工作,同時照顧女兒。“都說創業的女性不顧家,我偏不,我得成為一個家庭事業都兼顧好的人。”于鶯還是一股不服輸的勁兒,“回過頭想,沒有什么困難是過不去的。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要隨便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