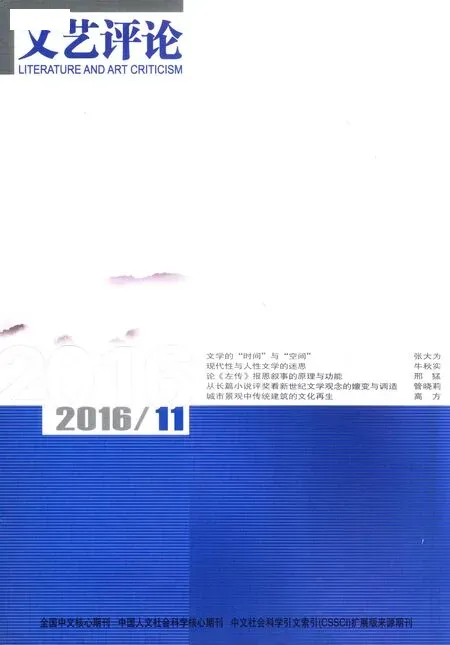二元結構的設置與個人立場的懸擱——對賈平凹長篇小說《極花》的一種解讀
○楊有楠
二元結構的設置與個人立場的懸擱——對賈平凹長篇小說《極花》的一種解讀
○楊有楠
賈平凹的《極花》甫一發表就招致駁雜的批評之聲,一些讀者指出它隱含著為拐賣婦女辯護的傾向,一些讀者認為它顯示出作者對鄉村的固執情懷已是一種荒誕的行為,甚或更有女權主義者直陳它暴露了作者的“菲勒斯中心主義”立場,其功用是“用對過時悲劇假裝深情的鋪陳,刺激讀者,以求關注和治療作者長期抱有的男性失敗的焦慮”①……針對種種爭議,賈平凹試圖給出自己的解釋,然而他所提供的一些“辯詞”似乎反而成為批評者可據其作進一步聲討的“證詞”。比如,賈平凹認為:“這個人販子,黑亮這個人物,從法律角度是不對的,但是如果他不買媳婦,就永遠沒有媳婦,如果這個村子永遠不買媳婦,這個村子就消亡了。”②如果斷章取義地僅從這一句出發,我們似乎可以從容地站在道德的高地為《極花》的批評者們搖旗吶喊。然而如果我們耐心地進入文本就會發現,《極花》所引起的爭議或許恰好來自作者所作的一種可貴努力,即突破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竭力“寫這生活的黑白之間,人心里極難說出來的東西”③。小說中的“極花”是一種冬天是蟲夏天開花的奇特生物,除了所被賦予的象征意義外,筆者認為它還以非此卻不即彼的身份特性隱喻了作者所追求的懸擱立場。
受害者與施害者之間
作為與新時期及其轉型一起拓路的作家,賈平凹對介入現實抱持著極大的熱忱,他的作品幾乎都或多或少地與當代中國的社會問題相關聯:《懷念狼》反思人與自然的復雜關系,《秦腔》哀悼傳統文化的隳敗,《高興》關注城市拾荒人的命運,《帶燈》審視鄉鎮基層的政治倫理困境……而在《極花》中,賈平凹則試圖對拐賣婦女這一社會議題作更深層次的探討。這一問題自然不是新近出現的,而以其為表現主題的文藝作品也已經不在少數,小說《喊山》(2004年),電影《盲山》(2007年)、《嫁給大山的女人》(2009年)等都是據此鋪展而成的。如果對它們作比較閱讀就會發現,無論是在主要人物的設置上,還是在細小情節的營構上,《極花》實際上并沒有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之前的敘述模式。在《盲山》中,導演李楊對白雪梅遭強暴,以及村民阻擋警察帶走白雪梅等場面做了粗糙的、甚至不加節制的光影表現。而在《極花》中,村民幫助黑亮強暴胡蝶,暴力野蠻地破壞解救行動的場景在賈平凹不吝筆墨的“絮叨”中同樣得以再現。然而,《極花》當然不同于《盲山》,其最大的區別在于賈平凹試圖突破施害者形象的扁形塑造方式,并盡力挖掘施害行動背后的深層原因。應該說,盡管李楊也試圖在緊張的敘事間隙對鄉村人情、人性作更飽滿的展現(比如拐賣者黃德貴的母親就是一個相對矛盾、立體的形象),但或許是受電影時長所限,又或許是出于明確傳達主旨的需要,《盲山》里的受害者與施害者之間的界限基本是分明的,而結尾處白雪梅用菜刀砍向黃德貴的情節設置不僅更凸顯了兩者之間的尖銳對立,而且意味著矛盾緩和的不可能性。④與之相比,《極花》則力圖在施害者與受害者之間搭建出更具復雜性、流動性的關系,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是對黑亮們施害者與受害者雙重身份的著力凸顯(尤其是后者)。幾十年來,即使社會文明已明顯提高,打擊力度已逐年增強,拐賣婦女為何頻仍發生?這或許是賈平凹讓發生在十年前的真實故事重新浮出歷史地表的重要動因之一。因之,他竭力規避了“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的中介因素和表層邏輯,而集中于對直接原因的尋找和分析。作為拐賣婦女的直接需求方,農村男性就成為作者審視的主要對象,繼而他們的婚姻難題以及性苦悶現狀就被挖掘出來。在此之前,梁鴻的紀實文本《中國在梁莊》、韓少功的散文《山南水北》、曹乃謙的小說《到黑夜想你沒辦法》以及郝杰的電影《光棍兒》等都對農村男性的性苦悶做過酷烈、赤裸的呈現。而《極花》的特別之處在于不只是呈現,而是力圖將這一問題向前、后兩個方向推演開去,即向前尋索其產生的深層原因,向后思考其帶來的連鎖問題和可預見的走向。《極花》開頭,在進城打工的順子的媳婦跟著收購極花的村外人私奔后,順子爹因痛恨自己不能為兒子留住媳婦而自殺,同村的男人也因女人不愿留下備感羞辱和憤恨。接著,作者便通過美女像上的深刻刀痕表現了黑亮們的性苦悶。可以看到,作者指出癥結的欲望如此急切,以致不惜直接借黑亮之口傳達出來:“現在國家發展城市哩,城市就成了個血盆大口,吸農村的錢,吸農村的物,把農村的姑娘全吸走了!”盡管賈平凹旋即就站在胡蝶的立場上對拐賣行為提出質疑,但這很快便湮沒甚至消解在欲言又止的語氣和對農村男性性苦悶的渲染中。與其他作家相似,賈平凹走的也是“往狠里寫”的路子,于是我們看到,喪妻后瘋癲的金鎖的哭墳聲貫穿全篇,女人訾米像財物般在立春、臘八兩兄弟間完成轉手,光棍們只能從石頭女人,甚至動物那里獲得慰藉……除此之外,借助家家戶戶前立著的像石祖一般的門窗,以及血蔥的繁盛和極花的日漸稀少之對比,作者不但暗示了性苦悶在農村的普泛性、焦慮感,更牽涉出女性缺席給農村男性帶來的傳宗接代的壓力,以及由此造成的更大焦慮。“那些男人在殘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層開著的不結瓜的荒花。或許,他們就是中國最后的農村,或許,他們就是最后的光棍。”⑤可以說,在賈平凹看來,這是社會轉型期的中國加諸于傳統農村(尤其是農村男性)的傷痛,這傷痛不僅劇烈而且很難通過正常的方式獲得療愈,久而久之它更是熬成無奈的苦衷,繼而為本是受害者的黑亮們疊加上施害者的身份。這兩種對立身份的糾纏無疑使得黑亮們成為一個矛盾的主體,作者一方面想給予他們同情的理解,另一方面又無法也不能輕易原諒他們的暴力行為,因而只能延宕審判的到來。但不得不說,必要的批判性的缺席也是一種寫作遺憾。
其次,是一種類似于“斯德哥爾摩效應”的情節設置。一般而言,“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指的是一種反常的心理學現象,即受害者在與施害者共同生活期間,對其產生一定的認同感或正面情感。表面看來,被拐賣者胡蝶對拐賣者黑亮及其“幫兇”(幾乎是整個圪梁村)所表現出的情感變化與此效應十分相似。一開始,被囚禁的胡蝶對黑亮、黑亮爹甚或整個圪梁村村民都只有滿腔的仇恨。她以每天在窯洞壁上刻道兒的方式計劃逃離,勾勒活下去的希望。然而隨著故事的推進,經歷了被強暴、被迫生子等厄運的胡蝶反而能以平和的心境與黑亮們相處了。她開始視自己為家庭中的一員,主動承擔家務,稱呼黑亮的父親“爹”,甚至最終接受黑亮做自己的丈夫(無論身體上還是心靈上)……不能否認,這種情感上的轉換或許出于無奈地認命,但是細究文本就會發現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胡蝶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作出的主動情感選擇。與《盲山》中粗魯、兇悍、暴躁的丈夫黃德貴不同,《極花》中的黑亮在拐賣、囚禁、強暴胡蝶之外,不僅竭力為胡蝶提供更好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小心翼翼地給她一定的尊重和包容。賈平凹用一個個有溫度、有分寸的細節將黑亮塑造為一個雖有污點,卻也老實孝順、好求上進,甚至不乏溫柔,有些膽怯的農村男人。除此之外,以黑亮爹為代表的圪梁村村民其實都是摻雜著善惡因子的傳統農民,他們雖蒙昧、野蠻、暴力、貪婪,卻也不乏樸素的人情溫暖,比如,他們自發地幫外出打工的順子料理爹的后事,也盡量在立春、臘八兄弟喪生之后伸出援手等等。由于《極花》是用第一人稱視角敘述而成的,因而以上圖景基本是經胡蝶摻雜著仇恨的眼睛過濾后的結果。因此和“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病態扭曲不同,胡蝶的情感轉向在賈平凹不急不緩的鋪墊下折射出的或許正是真實的人性,它如此復雜而莫測,以致黑白分明的價值判斷在它面前顯得無力甚至幾近失效。
可以說,盡管同樣是關注人口拐賣問題,相較于《盲山》等更著重于展現人道主義悲憫和現實批判精神,《極花》則意在借其勾勒出如惡之花般、異化了的人性的復雜圖景。為此,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懸擱了個人的價值判斷,而只是呈現了兩難現狀的事實存在。
城市和農村之間
雖然《極花》是從胡蝶被拐賣說起的,但賈平凹卻直言:“我實在是不想把它寫成一個純粹的拐賣婦女兒童的故事。”“我關注的是城市在怎樣地肥大著而農村在怎樣地凋敝著,我老鄉的女兒被拐賣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樣,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還活著的一群人是懦弱還是強狠,是可憐還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樣常年駐雪的冰冷,還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⑥可以說,關注鄉村于現代化進程中的真實境遇已成為賈平凹揮之不去的書寫情結。而在《極花》中,作者則希冀借助主人公胡蝶的空間流浪探討當下時代語境中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復雜關系,并進而考察個人在中國大轉型年代的生存境況。
縱觀全篇,胡蝶先后完成了農村-城市-農村-城市-農村的空間流浪,而鄉村的全面衰敗不僅激發了她最初的流浪沖動,而且還使其在很長時間內延續著對城市的美好憧憬。與《古爐》不同,《極花》中的鄉村不再被描繪成“文化烏托邦式”的存在,而逐漸裸露出其真實面相。首先,物質的貧乏仍是難以擺脫的生存焦慮。借助胡蝶的喋喋不休,賈平凹呈現了連基本的生存需求都無法保障的農村現狀:飲食單調乏味且只夠溫飽,學費難以籌集,衣著、住所破舊不堪,醫療技術古老落后,村莊偏遠封閉,環境破敗險惡……不只黑亮的家鄉圪梁村如此,胡蝶的家鄉營盤村也是如此,借此,《極花》試圖表明這樣與主流意識形態描繪的新農村藍圖相去甚遠的圖景絕不會只是個案。其次,鄉村傳統倫理趨于崩塌。作為圪梁村的主要經濟來源,極花和血蔥在商品市場的風行所借助的是過度包裝、炒作等商業手段,而那種“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民間營銷理念則慢慢被淘汰了。與此同時,經濟利潤刺激了欲望的膨脹和貪婪的滋長,遂而極花在瘋狂的采挖中幾近消失,血蔥則日益稀釋、離間著村民之間,甚至兄弟之間的感情。即是說,沒能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農村非但不是獨立于商品經濟大潮之外的桃花源,反而還在逐浪的過程中或主動或被動地丟失了傳統鄉村文明的精神內核。小說尾聲,作為德孝仁愛等傳統道德象征的葫蘆的枯死更是顯示了作者對這一問題的憂慮和悲觀思考。最后,鄉村權力結構的暗瘡再次被披露出來。《極花》中的村長長期霸占著村里的多個寡婦,主觀把控著村里的資源分配,參與人口拐賣并從中謀取高額抽成……不要說為農民謀福祉,村長甚至成為借權力之刀殘忍屠宰農民利益的劊子手。應該說,在當代鄉土小說中,這類村長的形象已基本構成了鄉土中國權力網上的符號化存在,比如《耙耬山脈》(閻連科)、《蛙》(莫言)中的村干部即屬于這一類型。盡管這在某種程度上暴露了作家塑造人物的類型化傾向,但也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這類村干部不只出現在圪梁村,也在耙耬山區、高密東北鄉等農村事實存在著。綜而觀之,胡蝶所要逃離的農村即是如上所述的面目,它的土地上生長著的已非希望,而滿是凄苦。因之,在被拐回農村之后,胡蝶仍不能放下對城市身份象征——高跟鞋的迷戀,她所心心念念的是“我要回去……我要回城市去”,而不是“我要回營盤村去”。
然而,被寄予無限希望的城市真的可以成為胡蝶們理想中的棲息地嗎?賈平凹對此持明顯的懷疑態度。于是我們看到,初到城市的胡蝶與媽媽不僅仍生活在局促破陋的出租房里,小心翼翼地省吃儉用,還要額外承受著城里人的鄙夷、俯瞰甚至侮辱……但胡蝶們堅信如是現狀主要導源于農村身份與城市空間的格格不入,一旦取得了城市人的身份標簽,她們也能順理成章地分享城市的馨香與甘甜。為此,以各式各樣的都市符號(普通話、小西裝、染發、高跟鞋等)包裝自己,繼而遵循城市生存法則(努力掙錢)就成為她們自以為的獲取城市身份的重要路徑。然而,當胡蝶們懷揣期待地搭上通往美好幻夢的客運車時,她們卻被以一種狡黠又諷刺的方式遣返回農村。就此,裹挾著商品經濟屬性和暴力色彩的“拐賣”成了作者透視城鄉關系的重要管道。可以說,農村的事實寙敗已基本成為一種顯證:在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農村無疑是掉隊者,是被犧牲者,它們甚至以自己的衰敗喂養了城市的肥大。在這里,城市與農村呈現出不可調和的對立矛盾,而“拐賣”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這一矛盾激化的產物之一。胡蝶們被物化作一種可供販賣和爭奪的資源,先是城市以異于農村的表相吸引她們主動地完成空間轉移,隨后又將她們包裝成可供出售的商品,最后農村以購買的方式將她們搶奪回來。于農村而言,這既出于實際需要,也近乎于一種絕望且無效的反抗。當黑亮們憤恨又無奈地將全部積蓄作為跟城市爭奪女性資源的籌碼時,城市實際上又一次完成了對農村的剝奪。而在拐賣因其非法性受到嚴厲打擊的同時,隨之而來的或許還有某種遮蔽。即是說,當解救者(警察等)以正義、合法之名重新把胡蝶們帶回城市,并將審判的矛頭導向罪惡的人販子,農村男性甚至整個農村的苦悶與焦慮復又很快地淡化出公眾的視野。不惜以流血的方式野蠻地阻擋解救行動,這或許是農村所能做出的最無奈、最原始的反抗,也是它在這場社會悲劇中最后的、蒼涼的退場姿勢。它的兒子繼續如荒花般等待著命運的終結,而它的女兒——胡蝶們即使在重新回到夢寐以求的城市后也終究尋不到一朵可供棲居的花,最終只能如夢似幻地飄蕩于城鄉之間。
有評論者指出,在《秦腔》中,賈平凹“建構起一種新的敘事倫理”,即在面對鄉村急劇現代化的現狀和未來趨向時,作者以“我不知道”的含混態度替換了早前相對明晰的價值判斷。⑦在《極花》的后記中,賈平凹講述了自己到一些偏遠村莊進行田野調查的經歷,面對光棍的哭訴:我家在我手里要絕種了,我們村在我們這一輩就消亡了,他無言以對。筆者認為,賈平凹的“無言以對”不但是因為他深知在如此巨大的悲愴面前言語安慰將是多么蒼白無力,或許更基于對不可逆轉的歷史發展趨向的理性認知:現代化的最終結果可能就是農村以及農民的徹底消失。于是,《極花》里,盡管哀傷的挽歌情調無處不在,盡管控訴的欲念甚至有些急不可耐,但是糾葛于現代理性與個人感性之間的賈平凹顯然不是要在熱情擁抱城市化和退回傳統鄉村之間作出簡單明了的選擇,他更關心的是人,尤其是飽經風霜的農村人,如何在處于轉型陣痛期的中國安身立命的問題。透過胡蝶于城鄉之間或主動或被動的輾轉流離,賈平凹將一個田園將蕪、都市未臻成熟的當代中國推至前景,其中游蕩著的是不知何處是吾鄉的苦命人,抑或無論是何處,都無甚差別?于是,當自認已是城里人的胡蝶喊叫著農村不是自己該呆的地方,黑亮回答道,“待在哪兒還不都是中國”;當胡蝶認為自己的星星只有在城市里才能看到,老老爺反問道,“在哪里還不都是在星下啊”;而于城鄉之間完成數度空間流轉的胡蝶最終也意識到“在中國哪兒都一樣”……在這里,中國已然是一個混沌一體的生存場域,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都無法成為胡蝶們、黑亮們棲身的安全地帶。故事結尾,賈平凹駕輕就熟地以亦虛亦實的寫作技法安排了胡蝶的歸宿——在似夢非夢中回到了都市,又如剪紙般地粘在了農村的窯壁上,其所傳達的不只是許多中國人的迷惘心境,還有同樣“不知道”的作者的懸擱立場。
實與虛之間
承上所述,一個恍兮惚兮的情節被用來為《極花》作結,除承擔著傳達主旨意蘊的功能外,它還彰顯了賈平凹一直以來的審美追求,即突破嚴格的寫實框架,竭力將清明與神秘熔于一爐。這不單是受西方文學創作思潮影響的結果,更是因為“賈平凹在古老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中長久修煉已經‘得道成仙’,因此構成了他自己獨特的感知世界的方式”⑧。從上世紀80年代末的《太白山記》《煙》,到上世紀90年代《廢都》《白夜》《高老莊》,再到新世紀以來的《懷念狼》《秦腔》《古爐》等,虛實相生、亦幻亦真可謂是這些作品共有的審美面相之一。不得不指出的是,隨著創作時間的推演,賈平凹處理虛與實的方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例如,《太白山記》基本可看作中國傳統志怪小說的當代延伸,《廢都》《白夜》在借“哲學牛”、再生人的鑰匙等局部意象傳達神秘感的同時,也透過“廢都”“白夜”這樣的核心意象生發多義性,《懷念狼》意在“直接將情節處理成意象”⑨,《秦腔》之后的作品不僅以密實的流年式敘述呈現生活“混沌又鮮活”的自我流程,還大多擇取了頗富神秘色彩的敘述人(如,引生、狗尿苔、唱師等)……而《極花》則試圖一面極盡寫實之能事,一面借有意構建的意象群營造虛幻的意境,進而在實與虛之間覓得一種風格上的平衡。
可以說,賈平凹摹寫日常經驗,雕刻生活細節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比如,《白夜》中,糾葛于欲望與理性之間的市井細民的百態生活就得到了如同影像般的呈現,《秦腔》更是事無巨細地將鄉土世界中的雞零狗碎都轉化成文字。而《極花》盡管被作者稱為“最短的一個長篇”,但它反而以更密實的文字構筑起愈顯實在,甚至可觸的日常空間。言稱小說是不需要技巧的“說話”的賈平凹以一個被拐賣女人的“嘮叨”結構起《極花》的故事,于是胡蝶的說話,包括控訴、對話、自言自語、所思所感所想等,無一不是《極花》鋪展開去的重要憑借。與此同時,作者試圖賦予胡蝶充分的話語權,即將部分掌控小說走向的權力讓渡給敘述者,進而讓講述以近乎原生態的方式流淌出來。因而,日子不再被一筆帶過或服膺于理念的拆分重組,而是還原成無數隨時間自然流淌的瑣屑細事:三時三餐中一蔬一飯的滋味,村民之間狡黠也溫情的交際日常,總是披著大衣的村長在村里的來來回回……尤其讓人印象深刻的是胡蝶以“我學會了……”的句式開啟的多段自陳自述,在這里,賈平凹不吝筆墨地將飼弄雞、做攪團、做蕎面饸饹、做土豆、騎毛驢、采茵陳、做草鞋等農村生存技能細致地刻寫出來,這不但部分地返還了日常生活所內含的文學審美意義,也在對細節的鋪排中折射了胡蝶不無矛盾的情感態度,而如此真實生動的細節描寫自然是以作者豐富的農村生活經驗作為支撐的。即使在入城多年之后,賈平凹也沒有完全褪去農村的烙印,甚至依舊以農民自居,這并不是一種簡單的身份認同,其提供給作者的也不單是上述寫作素材,還有一種部分疏離于現代理性的原始思維方式。因而,《極花》還將一些被傳統現實主義小說排除在外的質素呈現出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其自足的存在意義。例如,鬼魅精怪的幻影,預示風水、吉兇的白皮松和烏鴉,麻子嬸的離奇經歷(在槐樹下懷孕、“死”而復生等),帶有神秘色彩的民間禁忌、傳說和習俗等等。對此,賈平凹曾指出自己并不是像馬爾克斯那樣硬在作品中來些魔幻,出現在他作品中的神秘現象都是他“現實生活中接觸過,都是社會中存在的東西”⑩。應該說,當賈平凹以一種“確信其有”的心態記錄“鮮活又混沌”的日常生活時,其已為讀者帶來了一種虛實難辨的閱讀感受。
當然,《極花》之虛更多地來自于那些作者有意遴選、創造的意象,例如紅狐貍、極花、血蔥、星野、老老爺、離魂和夢境等,它們并不是散金碎玉般的存在于文本之中,而是基本都暗合于作者想要傳達的隱含意蘊,進而被組織進一個系統的意象群。如果說包括紅狐貍在內的諸多已然消失的野物在文本中的復又出現、極花與血蔥的功能與消長顯示了鄉土中國原始性、神秘性的一面,那么對老老爺和星野的濃墨涂抹則象征著古老化中國的當代遺存。即是說,雖然現代文明已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對鄉土世界的滲透,但是農村以及農村傳統仍未徹底走入歷史。《極花》中的老老爺無疑是類似于傅山(《懷念狼》)和寬哥(《白夜》)那樣的人物意象,其象征著的是一種將逝未逝的生活和思維方式:他承續傳統,斥責“忘八談”現象,每年的二月二都堅持給村民拴彩花繩兒;他相信宿命,認為分星和分野的對照關系決定了人生活的地域,墳里呼出的氣則決定了人最終的歸宿;他懼鬼敬神,當村子里連連發生怪事時,他主張通過搭臺唱戲祈求神的保佑……應該說,自五四以來,現代理性就一直將改變上述情狀視作啟蒙的重要任務之一,然而在將近百年之后,它們仍脆弱又頑強地遺存在中國的大地上。因之,現代文明的駛入與其說是實現了中國的現代化,不如說是撕裂了當下的中國:中國儼然成為一個對立物的遭遇之地,極落后與極先進、極古老與極現代生長在同一塊土地上。遂而,離魂和夢境兩個意象的設置就更多地出于審視撕裂之中國的需要,作者不僅借此獲得了更恰切便利的敘述視角,也能更有效地抵達虛實相生的美學境界。《極花》多次敘述了胡蝶的魂魄離開身體的經歷,通過細讀可以發現,這基本都發生在胡蝶罹難之際:逃跑被抓、被強暴、難產……每當暴力靠近,胡蝶就會分裂成兩個人——處于暴力中心的胡蝶(身體)旋即失去話語權,處于暴力外圍的“我”(魂魄)隨之承擔起敘事的職責。后者在某種程度上就成了引生(《秦腔》)式的敘述人,講述由此不再受限于第一人稱的限制性視角。比如,在胡蝶難產之際,作者就借離魂的“眼睛”呈現了依然流行于民間的古老落后的接生方法。而當村民們極其粗暴地抓回逃跑的胡蝶,野蠻甚至亢奮地扯掉胡蝶的衣服并將其捆綁在條凳上以幫助黑亮完成強暴,作為敘述者的離魂不只看到了女性受難的身體和毫無尊嚴可言的存在境遇,更披露了鄉村世界粗鄙、非理性的一面。不論這是人性中蟄伏已久的惡魔性的迸發,還是矛盾激化的惡果,其在當下中國的事實存在才是作者所要著重凸顯的方面。與之類似,夢境意象的設置同樣帶來了更加自由的敘述視閾,借此,被囚禁的胡蝶講述了更駁雜、開闊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故事結尾處,那個以亦幻亦真的方式呈現而出的解救與阻擋解救的暴力場面同樣是撕裂之中國的重要表征。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不管設置了怎樣虛幻的意象,作者都竭力以實筆,以豐滿的細節描寫之,其意圖在于以實寫虛,而如此虛虛實實的筆法或許也可視作當下曖昧、混沌之中國的一種隱喻。
綜而觀之,《極花》可謂較為鮮明地顯示了賈平凹的懸擱立場:在受害者與施害者之間,他在一定程度上延宕了道德審判的到來,著力剖析人性的動蕩與駁雜;在城市與農村之間,他既不遺余力地披露前者的惡,又毫不避諱地撕下后者的畫皮,進而凸顯出無處安身立命的人的苦痛;在實與虛之間,他一方面以密實、豐滿的細節鋪述生活固有的自我流程,另一方面借相對系統的意象群營造虛幻的意境,以求通過兩者之間的平衡互動,生發深層意蘊。筆者認為,正是這一立場的擇取使《極花》在很大程度上跳脫出相關題材的既有敘事框架,并拓展出相對新鮮、深度的表現空間。當然,《極花》并不完美,必要的批判性、反思性的闕如,以及過于絮叨、不加節制的語言等都是其不能被忽視的寫作遺憾。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
①呂頻《賈平凹為拐賣媳婦辯護,何其荒唐》[N],《新京報》,2016年5月9日。
②張知依《賈平凹:我想寫最偏遠的農村與最隱秘的心態》[N],《北京青年報》,2016年4月16日。
③毛亞楠《賈平凹:〈極花〉不僅僅是拐賣與解救的故事》[J],《方圓》,2016年第6期。
④這是《盲山》海外版本的結局。而在內地公映版中,這一情節被刪掉了,故事以警察對白雪梅的成功解救畫上句點。
⑤⑥賈平凹《〈極花〉后記》[J],《東吳學術》,2016年第1期。
⑦謝有順《尊靈魂,嘆生命——賈平凹〈秦腔〉及其寫作倫理》[J],《當代作家評論》,2005年第5期。
⑧曠新年《從〈廢都〉到〈白夜〉》[J],《小說評論》,1996年第1期。
⑨賈平凹《懷念狼·后記》[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頁。
⑩賈平凹、張英《地域文化與創作:繼承與創新——關于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談話》[J],《作家》,199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