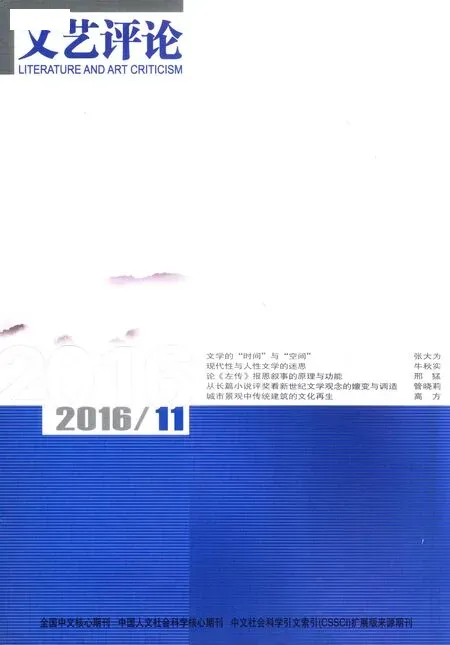“醉”:宋代蜀學之審美境界
○譚玉龍
“醉”:宋代蜀學之審美境界
○譚玉龍
中華酒文化的歷史源遠流長,我國先民在五千多年以前就已掌握了釀酒的技術,并且,酒還滲透于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朱肱《酒經》云:“大哉,酒之于世也。禮天地,事鬼神,鄉射之飲,鹿鳴之歌,賓主百拜,左右秩秩。上至縉紳,下逮閭里,詩人墨客,漁夫樵婦,無可以缺也。”①個中緣由乃是酒不僅具有實用價值,它還具有精神價值。對于“詩人墨客”來說,酒的精神價值集中體現為“醉”,酒讓人“醉”,“醉”讓人消愁解脫、自然適意。而以“三蘇”為首的宋代蜀學正注意到了這一點,引“醉”入藝術與人生,將“醉”提升為一種即工夫即本體的蜀學美學范疇,并以此區別于荊公新學和二程洛學,成為宋代美學中一個獨特的美學流派。
一、醉筆得天全,宛宛天投蜺
對于藝術創作、審美鑒賞等活動來說,情感總是貫穿于始終的,所以,“美是情感變成有形”②。可見,“情”在藝術、審美活動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儒家美學也承認并且重視“情”在人們生活和藝術創作中的作用,但是,毫無節制的“情”就會導致“過”“淫”,故儒家美學倡導“發乎情,止乎禮義”(《毛詩序》)③,以對“情”進行限制而使之歸于“正”。宋代荊公新學和二程洛學則沿此路徑發展了儒家美學的情感理論。新學與洛學美學較為一致地認為“情”是“性”的一種狀態,所以不必完全禁止和取消“情”,如“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性情》)④;“只性為本,情是性之動處”(《河南程氏遺書》)⑤。從本體論上講,“性情一也”(《性情》)⑥。但同時,荊公新學認為:“求性于君子,求情于小人。”“動則當于理,則圣也,賢也;不當于理,則小人也。”(《性情》)⑦二程洛學也認為:“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答橫渠張子后先生書》)⑧“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顏子所好何學論》)⑨。因此,雖然“情”在新學、洛學中具有存在的空間,但是他們與傳統儒家一樣,更多地注意到了“情”的負面影響而倡導“性其情”(《顏子所好何學論》)⑩。
三蘇蜀學卻與荊公新學、二程洛學明顯不同。蘇軾云:“情者,性之動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無非性者。性之與情,非有善惡之別也。方其散而有為,則謂之情耳。”(《蘇氏易傳》)?所以,“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惡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情”,在蜀學美學中,并不是“惡”,而是“性”的一種狀態,它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并且“極歡極戚而不違于道”(《欒城集·上兩制諸公書》)?。也正由于此,蜀學美學才認為,藝術創作必須要重視“情”、運用“情”,如:“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而非勉強所為之文也。”(《南行前集敘》)?所謂“不能不為”就是情感充沛到了不得不進行創作的程度。在這種狀態下,藝術創作不是“勉強所為”而是純任性靈而發,藝術作品就是情感的外化。與新學、洛學限制“情”相反,蜀學美學尊情、尚情,這就為“醉”的藝術創作論奠定了堅實基礎。
我們知道,“醉”是一種過度飲酒而產生的由生理到心理的一種變化和狀態,它往往使人情感奮發、精神活躍。這一點正被蜀學美學所注意而將其引入了藝術創作領域。蘇軾曰:“仆醉后,乘興輒作草書十數行,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也。”(《跋草書后》)?可見,“醉”在藝術創作過程中,就是一種情感的抒泄。蘇軾還說:“成都人蒲永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書蒲永升畫后》)?醉酒使人放浪形骸,從而在自由的狀態下,自我之“性”與繪畫融合為一,讓藝術作品達到“活”的境界。可以說,蜀學美學因“情”而重視、倡導“醉”,因為“醉”激發“情”,讓人在“不能不為”的狀態中進行藝術創作。因此,蘇轍云:“醉書大軸作歌詩,頃刻揮毫千萬字。”(《飲餞王鞏》)?
“醉”觸發充沛的情感,從而使藝術家在亢奮的狀態下瞬間地、毫不粘滯地進行藝術創作。而這種瞬間而成的藝術創作必然要超越技法。蘇轍詩曰:“醉吟揮弄清潮水,誰信從前戒律人。”?“戒律”就是規則、技法,“戒律人”就是恪守法則、墨守成規之人。在蘇轍看來,“醉”正是對“戒律”的否定,對藝術創作技法的超越。有學者認為:“洛黨、蜀黨是舊黨豪貴內部依地域勢力結合而相互傾軋的集團。”而“洛學與蜀學之爭是洛蜀黨爭的反映”?,因此,蜀學自然烙上了地域文化(即巴蜀文化)的印跡。巴蜀文化,自漢代以降,就不斷受到道家哲學的影響,蜀中學人大多重視吸收老莊哲學。《老子》所謂的“道法自然”?、《莊子》中的“庖丁解牛”?等等,無不蘊含著“無法之法”的美學思想。三蘇蜀學美學也正是在吸收老莊“無法之法”論的基礎上,倡導藝術創作應沖破技法的束縛。蘇洵曾對何謂“天下之至文”的問題進行了論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雜文·仲兄字文甫說》)?可見,“天下之至文”不是刻意創作而成的“文”,而是猶如風與水相接觸而自然形成的“文”,這是一種“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之“文”。此“文”不待技法、規則而通向老莊之“自然”“大道”。
“醉”正滿足了這種“無意相求”“不期相遭”的要求。蘇軾《題醉草》曰:“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為不及。”?日本學者平山觀月曾用“蜿蜒跌宕似無意而為”來評論王羲之的草書。?而“蜿蜒跌宕似無意而為”正說明了草書的創作需要超越有限的技法而“無意”為之。蘇軾所謂“醉”能作大草,而“醒”卻不及。可見,蜀學美學之“醉”與“醒”正對應著無法與有法,“醉”就是對技法的超越,是一種無意為之的無法之法。三蘇鐘情于“醉筆”?“醉墨”?的原因正在于此。要言之,三蘇蜀學美學不像荊公新學、二程洛學那樣倡導“去情卻欲”(《禮樂論》)?、“性其情”(《顏子所好何學論》)?,而是以“醉”觸“情”進行超越技法的自由創作,讓藝術創作真正成為解放自我、彰顯個性的活動。因此,在蜀學美學中,“醉筆”可以“得天全”?、“醉語”可以“出天真”?。
二、醉中身已忘,萬事隨亦毀
蜀學是一種儒學,但它是融合了佛道等思想的儒學,所以我們認為,蜀學具有“融合三教、融貫博通、重經學、積極進取不因循守舊等鮮明特色”?。而蜀學美學同樣具有“融合三教”的鮮明特色,不過在政治人生道路上,“三蘇”以儒家思想為主,在藝術審美方面,佛老思想的影響則是主要的。?道家以出世的態度面對世間的人事,認為世間事物遮蔽人的真性、限制人的自由,所以他們欲超越當下、回復到原生性的社會中。佛教則以遁世的態度觀照塵世,它認為塵世的一切皆虛幻不實、遷流變動,所以佛教在“空”萬法的基礎上,實現解脫、證得涅槃。佛道二教雖然有所差異,但他們較為一致地否定或超越當下的塵世而進入他們自己設想的自由之境。蜀學美學中的“醉”正是這樣一種否定或超越。在藝術美學中,“醉”是對技法的超越,而在人生美學中,“醉”成為對世間憂愁煩惱的超越,如“我醉歌時君和,醉倒須君扶我,惟酒可忘憂”(《水調歌頭》)?;“醉后胸中百無有,偃然嘯傲傾朋曹”(《欒城集·次韻趙至節推首夏》)?。可見,蜀學美學之“醉”不只是一種藝術創作方法,還是一種人生的修為。
對于占據北宋思想主導地位的荊公新學來說,人生的修為主要是“思”。王安石《洪范傳》曰:“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五事,以思為主……思者,事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圣也。”?這就是荊公新學“以思為主”的修為之法。雖然,貌言視聽要以“思”為主、由“思”來統攝,但其中最為根本的乃是人的思想言行要符合“禮”。所謂“以思為主”是讓人發自內心的遵從“禮”,讓人自愿地按“禮”行事。而“三蘇”蜀學卻與此大異其趣。蘇轍云:“醉中身已忘,萬事隨亦毀。此心不應然,外物妄使爾。”(《次韻子瞻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可見,“醉”讓人忘卻自“身”。而“身”都已經忘卻了,身之視聽言貌符不符合“禮”就更加無意義了。蘇軾也說:“得酒未舉杯,喪我固忘爾。”(《和陶飲酒二十首》)?莊子美學中有“吾喪我”?的理論。“吾”與“我”是兩種不同的生存方式,“我”是對待之我、欲望之我,“吾”是真我、道之我。“吾喪我”就是要消除對待分別和欲望之心。蜀學美學認為,“醉”可助“喪我”,其實是說,“醉”讓人消除思想中的分別、蕩去心靈中的欲望,從而實現自我的本真存在方式。蘇軾《記焦山長老答問》十分形象地講述了這種本真之“醉”:“東坡居士醉后單衫游招隱,既醒,著衫而歸,問大眾云:‘適來醉漢向甚處去?’眾無答。明日舉以問焦山。焦山叉手而立。”?不知向哪里去了的“醉漢”就是“我”,“醉”中的蘇軾喪去了“我”,從而實現了本真之“吾”。
如果說荊公新學以“思”為主是強調修身應符合“禮”的話,那么,二程洛學以“敬”為工夫則是強調修身應主于“理”,即“涵養須用敬”?、“入道以敬為本”?。二程曰:“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河南程氏遺書》)?“敬”就是“主一”,“一”則是“理”。所以,二程洛學以“敬”為工夫的理論其實是讓人順應、遵從天理。這是一種道德形而上學的要求,是一種“自我約束的方法”?。而蜀學美學卻以“醉”沖破這種約束與束縛。蘇軾詩云:“醉中相與棄拘束,顧勸二子解帶圍。”?“棄拘束”“解帶圍”就是莊子美學中“真畫者”之“解衣般礴”?,即解開了功名利祿、仁義禮智的束縛。蜀學美學之“醉”正與此相通,它讓人解脫后、進入“法天貴真,不拘于俗”?的境界。蘇軾《論淳于髠》云:“淳于髠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于州閭之間,男女雜坐,幾于勸矣,何諷之有?”?在蘇軾看來,淳于髠之“醉”超越了一切倫理道德的束縛而自由地“于州閭之間,男女雜坐”。男女之間的隔閡已被“醉”所消解,他因“醉”而進入了一種混沌未開的大道之境。
總之,荊公新學、二程洛學分別以“思”“敬”為工夫實現成圣入道的人生美學理想,而“三蘇”蜀學美學卻以“醉”為工夫沖破禮法、天理的束縛。所以,蜀學美學所謂的“醉時萬慮一掃空,醒后紛紛如宿草”?“哀歌妙舞奉清觴,白日一醉萬事忘”?等皆說明,“醉”是一種人生修為之法,它讓人去除功利欲望的束縛,最終實現人生美學意義上的“曠然天真”(《與言上人》)?。
三、天地一醉,萬物同歸
人是時間性的存在,在時間之中,人的生命總是有限、暫時的。但人并不滿足于此,總是在沖破有限、追求無限。這也體現在中國古典美學之中:“中國古代藝術家都在審美活動中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把個體生命投入宇宙的大生命(‘道’、‘氣’、‘太和’)之中,從而超越個體生命存在的有限性和暫時性。”而蜀學美學之“醉”正反映了這一“超越性”。蜀學美學中的“醉筆得天全”“醉中身已忘”分別代表了藝術創作和個人修為之“醉”,但蜀學美學并未就此止步,它還追求一種“天人合一”的超越之“醉”,即天地之醉。前兩者是工夫,后者為本體。
在蜀學中,形上之道與形下之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如“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道德真經注·道常無名》);“蓋道無所不在,其于人為性”(《道德真經注·載營魄》。包括人在內的萬物皆以“道”為宗,是“道”的一種存在方式,它們并不彼此分離。所以,蘇軾云:“天人有相通之道。”(《周書·洪范》)但是,“天人相通”僅具有可然性而非必然,即并非所有人都能與天相通。那么,什么人才能與天相通呢?蜀學認為:“惟達者為能默然而心通也。”(《周書·洪范》)“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后可以涉世而無累矣”(《道德真經注·寵辱》)。所以,只有“達人”才能與天相通,只有修煉到了“達”的境界才能天人合一。
東晉葛洪曰:“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抱樸子外篇·行品》)“達人”就是不為世累、自然逍遙、淡然無為之人,“達”的境界就是莊子中的“神全”之境。《莊子·達生》曰:“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逆物而不懾。彼得全于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于天乎!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傷也。”“神全”乃其神“全于天”也,即人復歸于“道”。而“醉”讓人無欲無求、忘卻生死、讓人復歸于天,這與“道”相通,所以“醉者”即“神全”者,他可以超越有限、進入無限,“墜車”而“不死”。申言之,“達人”即“神全”之人,“神全”之人即“醉者”,“醉”就是一種“達”、一種天人合一之境界。蘇軾吸收了這種莊學思想而認為:“有如醉且墜,幸未傷即醒。”(《穎州初別子由二首》)另外,他還進一步說:“醉眠草棘間,蟲虺莫予毒。”(《和王晉卿》)“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書孟德傳后》)。可見,蜀學美學之“醉”不僅能讓人像《莊子》中的“神全”之人那樣“墜而不死”,還可讓蟲蛇虎豹不能來加害。
“醉”可讓人“神全”而“達”,防止肉體生命受到傷害,此外,它還可以讓人的精神超越有限進入無限,在精神境界上獲得自由。《老子》曰:“我愚人之心,純純。”“愚”相對于聰明、知識,“純純”即“沌沌”,象征著道之混沌狀態。所以,“愚”就是對知識、聰明的超越而獲得那“大制不割”的混全之道。蘇轍曰:“頹然一醉,終日如愚。”(《自寫真贊》)“醉”即“愚”,它超越了功名利祿、善惡美丑的無分別狀態。蘇軾曰:“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書李伯時山莊圖后》)“醉”是一種無區分的心境,既然沒有了區分,那么萬物齊一、貴賤不存,自然不會“留于一物”。在這種狀態下,人才能見出自我與萬物之本真,達到“神與萬物交”“智與百工通”“與佛合”的境界,讓人的精神進入了永恒。
“醉”讓人身心皆“全”,使“人之天”復歸“天之天”,在“成己”與“成物”之間消除物我間的隔閡、彰顯生命的本真,正如蘇軾在《醉白棠記》中云:“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游。”此時,萬物不是與我分離、對待的客體,不是為認識、功利而存在的對象,而是與我生命息息相關的另一“主體”,物我之間是一種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即主體間性。蘇洵曰:“開樽自獻酬,竟日成野醉。青莎可為席,白石可為幾。”(《藤樽》)蘇軾亦云:“醉中走上黃茅岡,滿岡亂石如群羊。岡頭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登云龍山》)在“醉”之中,天地成為人的屋宇、萬物成為人的衣裳。這也就是莊子美學所追求的那種“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要言之,蜀學美學中的“醉”不只是工夫,它本身還是一種境界,是一種“神全”“通達”的本體之境。蘇軾引《祭曼卿文》曰:“天地一醉,萬物同歸。”(《書石曼卿詩筆后》)“醉”讓萬物歸于“道”,這種天地之“醉”就是人與萬物融合為一的天地境界。
結語
有學者認為,唐型文化是一種相對開放、相對外傾、色調熱烈的文化類型,宋型文化則是一種相對封閉、相對內傾、色調淡雅的文化類型,中唐以后,中國文化正出現了一個由唐型文化轉向宋型文化的大流轉。此說大體正確。以美學觀之,荊公新學、二程洛學美學的以“性”為重的性情論以及以“思”“敬”為主的工夫論等都能說明一種宋型文化的相對“封閉”“內傾”特色。但當我們將宋代蜀學美學納入其中加以考察時,卻還有繼續探討的空間。一方面,蜀學美學以“醉”為藝術創作方法,倡導藝術創作應該沖破技法、自然而然、任性而發,從而彰顯出“天全”“天真”的審美風格;另一方面,蜀學美學以“醉”為人生的修為方法,強調它能使人“忘”的功效,在忘卻煩惱、焦慮之中,使人達到“曠然天真”的審美境界。雖然,前者屬于藝術創作論,后者屬于人生修為論,但兩者都是工夫論。而蜀學美學之“醉”不僅是工夫,它還是本體,通向了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大道之境、存在之域。這種即工夫即本體的蜀學美學之“醉”并非是在禮教束縛下的創作、修為,它指向的也不是去人欲而窮天理的道德形而上學,而是在否定、超越現實中種種束縛的真正自由的天人合一境界。它彰顯出了狂放、濃烈、自由的特色。所以,雖然“三蘇”蜀學不像荊公新學、二程洛學(或理學)先后成為兩宋思想界的主流,但在美學領域中,“三蘇”蜀學則發揮著更為重要和獨特的作用與影響,如后世逐步興起的文人畫及其審美旨趣和明代以“醉”作草書的理論與實踐都不能說沒有受到“三蘇”蜀學美學的影響、啟發與刺激。總之,自由、狂放、濃烈而非封閉、內傾、色調淡雅的蜀學美學不僅是巴蜀美學發展史上的重要一環,還是宋代美學乃至整個中國美學中的一個獨特流派。
(作者單位:重慶郵電大學傳媒藝術學院)
①朱肱《酒經》[A],載《中國古代酒文獻輯錄》(第三冊)[M],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4年版,第1-2頁。
②鮑山葵《美學三講》[M],周煦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頁。
③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A],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72頁。
④⑥⑦??《王安石文集》[A],載《王安石全集》(上冊)[M],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版,第134頁,第134頁,第134頁,第123頁,第110頁。
⑤??《二程集》(第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3頁,第188頁,第169頁。
⑧⑨⑩?《二程集》(第二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60頁,第577頁,第577頁,第577頁。
?《蘇氏易傳》[A],曾棗莊、舒大剛主編《三蘇全書》(第一冊)[M],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143頁。
??《東坡志林》[M],曾棗莊、舒大剛主編《三蘇全書》(第五冊),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208頁,第237頁。
?《蘇轍集》(第二冊)[M],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87頁。
?蘇軾《南行前集序》[A],《蘇軾全集》(中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57頁。
?《蘇東坡全集》(上冊)[M],上海:世界書局,1936年版,第303頁。
?????《蘇轍集》(第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34頁,第207頁,第47頁,第94頁,第127頁。
?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史綱》(上冊)[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第294-295頁。
?平山觀月《書法藝術學》[M],喻建十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頁。
???《蘇軾詩集》(四)[A],曾棗莊、舒大剛主編《三蘇全書》(第九冊)[M],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頁,第48頁,第468-469頁。
?蔡方鹿《北宋蜀學三教融合的思想傾向》[J],《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王世德《儒道佛美學的融合——蘇軾文藝美學思想研究》[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8頁。
?《蘇軾詞集》[A],曾棗莊、舒大剛主編《三蘇全書》(第十冊)[M],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頁。
?《蘇軾文集》(五)[M],曾棗莊、舒大剛主編《三蘇全書》(第十五冊)[M],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頁。
?《二程集》(第四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183頁。
?蒙培元《理學范疇系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5頁。
?郭慶藩《莊子集釋》(下冊)[M],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032頁。
?蘇軾《仇池筆記》[A],曾棗莊、舒大剛主編《三蘇全書》(第五冊)[M],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頁。
2016年四川省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規劃項目“宋代蜀學與美學研究”]